朱朱(以下简称朱):我们从绘画的物质性说起。和当代的其他画家不同,你的绘画材料不是油画、装置、影像之类,而是用了最传统的宣纸。当然,这纸又不属于一般的中国画范畴。这其中的理由是什么?
徐累(以下简称徐):可能是因为我的懒惰吧。我学习的专业是中国画,和纸打交道业已经年,对伟大的中国传统绘画通过纸表达得那么出神入化,实在只有叹服。中国人对纸的敏感性和独造性无与伦比,我觉得它应该还有新的作为。当然,我的愿望不是继续做一些“枯藤老树昏鸦”的事情,我还没有如此昏庸。总的来说,我是一个与人群相背的人。一方面我还坚持用熟宣作现在的画,没有选择当代艺术的油画或者影像什么的,我是想在这件事上我的工作可以改变对传统纸的认识,它原来也可以做得这么有层次,这么不一样。另一方面,虽然我是在熟宣上作画,但又不是人们习惯的中国画的样子,纸,对我而言,是表达上的特殊材料,和中国画的固有模式没有表面的关系。所以。它是双重背离的,似是而非,有些冒险。
朱:为什么说是冒险呢?
徐:很简单,我是一个“四不像”。没有人把我当成同类,我无法归入任何一个现有的圈子。从材料看,意图不正确;从意图看,材料又是守旧的。既不是“前卫”,又不是“传统”,既不是“意识形态”,又不是“反意识形态”,不入流,不应景,所以我说自己“笔墨不随时代”。
朱:我反而觉得像你这样固执己见的艺术家应该更多一些,现在的人过于随波逐流,他们害怕被人群抛弃,而历史往往是逆流者为大流。比如林风眠,他将中国传统水墨的人文情致与那时的立体派绘画、莫迪里阿尼的风格糅合在一起,开创了一代画风,在当时,他也是一个异类。
徐:林风眠的艺术实践除了他的坚定难能可贵外,他的好处更在于,其变奏是恰如其分的,绘画上的现代性没有超出中国美学的边界,没有变成系统之外的事情,但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只有你去做了才能知道这件事有多难。
朱:你的作品似乎也是如此。如现代“观念”命题,它看上去既符合传统艺术的精致样式,又完全具有当代意义,所以有人评价你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贡献,就是使传统工笔画真正转型为当代艺术,是不是这样?
徐:当代只是过去所有艺术最顶端的浮面。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艺术实在太多了,这并不能证明我们的眼界如何开阔,而是我们的眼光如何狭窄,和前人相比如何没有锐度。我们的知识是支离破碎的,有企图心又力不从心。怎么办呢?事情总是要做的,“缝缝补补又三年”。通过那些概念、那些表达,不同的元素,庞杂的、似乎没有关联的东西,可以变成个体的幻象。
朱:我知道你早年是前卫艺术的活跃分子,而后才转变成现在的模式,是怎样开始的呢?
徐:1989年以前,那时我还是年轻的艺术激进分子,参加了“八五新潮”美术运动。当时创作了一些纸上丙烯作品,受超现实主义和概念艺术的影响。譬如《心肺正常》,想告诉别人,越是美丽的东西越接近死亡,现象与本质之间是有距离的,这样的观点到今天仍然是有延伸的。19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以后,我突然厌烦了那种以“前卫”为名义的斗争,我认为那只是姿态,不是本质,不是自我怀疑,现象很繁闹,内在很虚弱,我们摩拳擦掌的只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反面。我好像感觉到,艺术的所谓“前卫”“后场”完全是自欺欺人的,所谓创造的自由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默许的主见。在节制的前提下,在美学的基线上,自己拥有最大程度的优先权,不必向任何势力讨好,不必向任何势力献宠。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就抽身而退,开始了一个人的游荡,我相信有一种“辽阔”是大于现实的,我认为那种黑夜的辽阔是创作上的恩德,既不妨碍别人,又和周围的事情没有什么瓜葛。
朱:现实与你的绘画构成一种怎样的关系?
徐:与形制更大的似水流年相比,现实只是偶然的风雨,是活在当下的借口。这并不是说我对现实麻木不仁,我有另外的方式来应对它。但艺术和现实的关系之于我来说,不是依附的,不是“物质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的,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校正和抵抗这样的关系。艺术和现实是两个并行的世界,这一点,中国古代的绘画艺术已经廓清了这两个世界的不同存在形式,我更同意它们之间是互为借口的。从更宽泛的角度来说,人的内心景象,也许是更为复杂的现实。相比而言,我更迷恋这样的“内界”,它是现实世界的反转,这是毫无疑问的。我的一些画不是没有现实,而是将现实改头换面,它是如影随行的。1997年,我做了一幅《虚归》,画中的屏风结构仿照了贝聿铭设计的香港中银大厦,谁都知道这个建筑是香港的标志。我并没有有意通过这个符号来纪念香港回归的事件,事后想想,为什么在这样的时间创作了这样的作品呢?冥冥之中也好,潜移默化也好,现实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偷袭过来,真是很有意思。
朱:现实在你的绘画中相当于—种心理暗示或潜意识,它是一个非主题性的东西?
徐:可能是吧。现实,包括我生活中的现实际遇,可能是我的画的底色。一幅画也许有好多层底色,现实是最下面的一层,被其他东西覆盖,你几乎看不到它。当我作完一幅画时,我会试图撩开看看,究竟底下有什么,有没有特别的危险或者艳遇躲在某个拐角处。这也是一件有意思的工作,给自己做做心理诊断,进行美学上的自疗,这对生存本身和接下来的事情都是有益的。
朱:也许不以现实来对应与你作品的关系,而以世界来对应与你作品的关系,可能更切合一些。就像你刚刚提到的那样,世界是“外界”,也是“内界”。
徐:你说得很对,“外界”和“内界”,这是一种修辞关系。就像维米尔的画一样,他没有表现市井的喧嚣,而是描绘午后的时光,某个室内,一个女人正在读信或者弹奏钢琴,那么庸常的生活。可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场景,往往会出现一幅地图,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女人是在世界之内隐藏着,世界呢,又是她内心的极限。这种虚实关系、大小关系,处理得荡气回肠,是何等美好啊!还有,凡·代克的《阿尔诺芬尼夫妇的婚礼》,画中那个远处的镜子反射的人物背影几乎是致命一击。委拉斯开兹的《宫中侍女》画面上的人物关系充满了修辞上的诡异,正面反面,里面外面,让人难以分辨虚实。这些作品带来的不仅是画面本身的美感,更重要的是思维上的闪烁不定,非常有智性。马格利特也一样,其实他对我的影响并不是所谓的非逻辑编排梦境,而是画面上的修辞游戏。说实话,我不是对绘画本身那么执著的人,真正吸引我的不是如何去画,而是如何去调弄图像之间的思维关系、修辞关系。这样说是不是又在自以为“意识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这件事情?
朱:在绘画这场不断展开的修辞游戏中,你最终想指涉什么?
徐:揭示事物的对应关系,为它提供新的理解。惊异的理解总是令人愉快的。你以自私的念头,恶作剧的念头,偷换或者指证某个概念,你会有一种快感,就像调情。你看我的地图,看上去和古地图没有什么差异,但里面的地名是另外一些内容,蝴蝶的名字,春药的名字、古琴的工谱,内容上偷梁换柱,这地图其实就是伪装的。地图是世界的平面微缩,它对人的存在有切实的安慰,但是,现在我想让它的归宿也成为虚无飘渺的东西,因为我也不知道,现实隐喻和文本隐喻哪个是更真实的,哪个是更可信赖的。《虚石》在屏风上描绘了一些逼真的假山石,我们知道,假山石是人造的,当它反映在屏风上的时候,那个源本立体的假山石就变成虚幻的平面影像。但它分明是清晰可辨、栩栩如生的。一个幻境,可是幻境又是实景,它们搅混在一起,莫衷一是。这种变化你也可以说它是修辞的方法,但我认为这其实还是中国美学界的惯用方法。像《红楼梦》、《聊斋志异》,虚虚实实、真真幻幻,现实和幻境是一个世界,两者相因相生,进退自如,不生造,不鲁莽,妄言也妄得那么妥帖,不像西方超现实主义的生硬嫁接,在对事物实施了暴力以后,才能实现所谓的超现实意象。我越来越觉得中国美学的诱人之处,实在是精妙、机巧,简直是造化的神奇。
朱:有一位美国诗人曾经这样来阐述诗歌的创作过程,意思是,—首诗的诞生从愉悦开始,经过一番旅程,最终以智慧终结。我觉得你也是这样,每幅作品自有一个意趣的开端。你的词汇表中的意象,譬如青花马、飘舞的帽子、以书遮面的人,一次又一次构造了奇境,总体上又汇成一个结论,有偏移,但不离心。
徐:一树千花才有意思嘛。我相信每个画家都能画出一两张好画。问题是你究竟是不是得心应手,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基本概念,有没有变奏的能力营造更多同样有价值的作品。就像形容一个女人好看,你可以用“美丽”形容她,接下来还可以说“漂亮”“标致”“如花似玉”,这些都是同义词。昆德拉说过,巴赫的原则就是,发明若干组音符的艺术,这些音符可以自己与自己相伴,再一个,从唯一的核心出发,去创造全部艺术。事情就是这样。只要活着,这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游戏,你要付出耐心,更重要的是有能力玩下去,玩得有意思。每一件作品都是前面作品的回声,你要有持续不断的招数,尽可能做出你能做出的。当然,词汇的丰富本身不代表任何价值,也许,词汇的准确才是至关重要的。
朱: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你如何知道某一个词——在你的作品中也可以理解为“意象”——恰好就是准确的,是你需要的,是你期待当中的呢?
徐:我有自己的方向感,知道自己美学意图的靶心在哪里,这个中心就是一个人的世界观和相关的趣味。经年累月,就像无法改变的血型,功能上有一种排异,自己以往完成的作品也一起先验般地制造了审美认识上的局限。这个局限是你的最大值。我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每天周围有这么多如过江之鲫的信息,能够滤下的东西一定不是说服了我,而是说服了我预期的美感。吻合意识的装置。这样的时刻往往连自己都觉得,老天爷又在照顾我了。
朱:我很喜欢法国批评家理查·皮埃尔的一句话:“观念不如顽念重要。”对于一个人而言,顽念可能是更重要的东西,甚至当一个人持续地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他也不完全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一种顽念的驱使,借用你的话来说,就是预期的美感、认识的装置。我觉得有那么一个顽念对你格外重要,那就是“虚无”。
徐:可不可以说,顽念是玩念的结石?你提到“虚无”的问题,我想我至少认同一种虚无的态度。虚无作为一个主张,它是什么呢?我以为,它是一杯水漫出来的那部分。虚无主义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共性问题。它首先是一个美学立场,但也不仅仅停留在美学问题上。我自己一直觉得,虚无是一种非常高尚的境界,在虚无这个“浴池”里浸泡,需要一个骄傲的心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人生就是一个残相,它在任何时候都是失去,或者准备失去,无法阻止。
朱:你的虚无主义从表象上看是缺失,是悬疑,是关于“躯壳”这样一个东西,它在你的意识里常驻,挥之不去。在你的画中,空衣服、空椅子、空房间,我们都可以称之为一种“躯壳”,它对应了一个主体。
中国古代有一种审美意识,叫做“人去楼空”,在你这儿,你的图像是对“楼空”的一种展现,但是它隐含和对应了“人去”。它有一种弃绝、不在场,以一种特别的意味感动着人;它是在唤起一个整体,或者说唤起一个完满的世界。那些物像,椅子和房子在这儿,证明了从前有人曾经逗留在这儿,“此曾在”,一种追忆性的语调,空间述说了时间。
徐:是的,“此曾在”是人性的无奈,心里有涌动,有算计,感慨在眼前的存在和失去之间来回踱步,可是作品却不动声色,自有其安详,按东方美学的说法,它是静观的。我们能看到些什么呢?来历、去处,都湮灭在背面的黑暗中,这唯一的光亮处只是过场和片断。虽然这些意象堂而皇之地待在这个地方,我们一样觉得它是一个“空无”,是“灵魂出窍”的残余。《小王子》里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最重要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这实际上肯定了可供看见的部分是一道难题。从艺术的样式来看,越是有怀疑精神,越会注意表面效果,所以,像颓废、寓言、魔术,洛可可,都是幻灭的绽放、虚无的面具,是有关迷失的另外的形式。
朱:从你说的这个角度看,绘画有可能是一种主动或自觉寻找迷失的过程,就像本雅明说的,“巴黎教会了我迷失”。迷失成了一种本领,需要通过训练才能进入的一种状态,我想一个人迷失在一座城市或者一幅画的创作过程中,他肯定既有心醉神迷的东西,同时也伴随着恐惧不安。
徐:总觉得在我身上有着多重的逃逸,一个是自己作为时代阵营里的逃逸者,有意放弃某种安全感,独自游荡。再一个,就是自己内部也有什么东西逃逸出来,就像达利的那件雕塑,身体上的抽屉不知何时滑了下来,唯有一个空洞。所以,我的画就是这样莫衷一是,自己设谜面,又根本找不到答案。这种感觉有点像看一部悬疑片,临到紧要关头,突然停止了,面对定格的画面只有一声叹息,但脑子里并没有停止猜测,这使人有长久的不安。我画帽子、衣服,它们就像悬疑片的现场那些有待考证的遗物;镜子、帘幕、地图,无非是藏匿的地点;我喜欢蝴蝶,它的生命形式代表善变的一生,那种欺骗、谎言和隐瞒体现得多么完美;我对天象台感兴趣,仅仅因为它的对应物是遥不可及的。我喜欢神秘的事情,在《绣履之往》中,鞋子隐藏在不可测的暗处,它是不是代表永远没法解答的秘密呢?
朱:“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或是引用罗兰·巴特的说法,“一个没有来源的复制品,一个没有原因的事件,一个没有主体的回忆”。对人在境遇中的无能有一种表达、怀疑的语气。但我觉得你在抱有悲观主义的同时,暗中怀有一种将真相最终翻转出来的梦想,当然你不肯定,似乎那是不可企及的。我觉得它有一个复调,或者是一种双重的调子,或者更多,因而它像是一种富有感染力和魔力的方式。
徐:我仍然觉得永远没有出口,好像被施了魔法。迟缓的、无聊的、使人麻痹的游荡是漫漫无期的。这样的梦游其实是很道德的。
朱:好像你的屏风也具有类似的功能,它的组成形式错综复杂,曲径通幽,我感觉你永远推着它在行走,不仅在做时间上的推延,也在故意设置某种障碍,使自闭更加蜿蜒。
徐:其实屏风的设置和原先的帷幔意思相近,我对遮蔽的事情一直都很感兴趣。后来发现,屏风还有助于我在视觉结构上完成一些事情,譬如形状大小、空间剪裁、节奏变化、平衡感,非常有趣。我在古代的戏本插图中找到这些空间的安排方式,后来,在画面具体操作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蒙德里安。年轻的时候我根本看不懂蒙德里安的作品,觉得他画的是一种图案,是设计。当然,现在知道他的纯粹是那么伟大,我从中明白了秩序是多么重要。
(摘自《艺术家·对话录》第三辑,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3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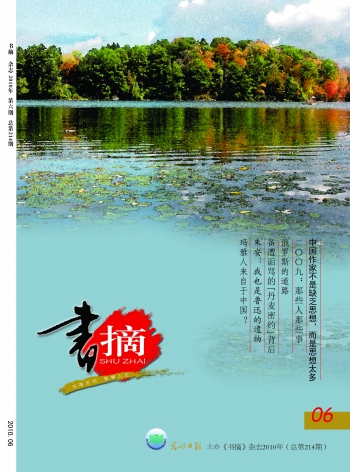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