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最兴奋的一件事”
成舍我大难不死,深知自己在京城随时仍有生命之虞,必须出去避避风头,韬光养晦一时,才是办法。于是把报馆的事托付给老友吴范寰管理,继续出刊,自己则在1927年春上去南京,寻找新的出路。
他要在南京创办新报的想法,与国民党大老李石曾不谋而合,于是遂由李出面张罗,合办一份四开小型报,命名为《民生报》。报纸首刊选在4月18日,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同一天。这一年,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通令党员必须重新登记,成舍我以“办报不应受到任何党派之约束”,“不往登记,自动放弃党籍”,这是他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作此选择,当然是出于对职业生涯的考虑和对新闻自由的尊重,他后来敢于和国民党进行抗争,这也是一个盾牌。
报馆房屋与成舍我的住宅联在一起,简陋局促。成舍我自任社长,请来了他在北大的同学周邦式任经理一职,编辑部骨干力量也多是《世界日报》的旧人。由于当时北伐军占领南京后,仍在同军阀孙传芳作战,孙的部队还一度夺取南京城,政局不稳,人心惶惶,成舍我对这份事业并没有多大信心:
《民生报》刚开始时,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因为几乎每天都在打仗,很危险。差点儿就办不下去,后来硬挺,总算撑住了。
报纸出刊后,因特立独行的风格,让人耳目一新。在报道新闻的理念上,成舍我也有自己的主见,认为小型报要与大报竞争,重要新闻不但不能比大报少,而且每天更要有一两条大报所无的消息或特讯,目的在于培养读者对本报的信心。为此,他花许多精力与达官贵人周旋,探求政界内幕,多次得到独家新闻,并引起轰动。加上《民生报》对时事的批评也十分精辟尖锐,因而深得读者欢迎。报纸初创时发行三千份,一年后就发行到一万五千份,几年后,更创下日发行达三万份的纪录,超过了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的销量。
此种蒸蒸日上势头,令成舍我信心大增。但到了1934年5月,一场意料不到的变故击碎了他的梦,《民生报》也遭到了灭顶之灾。
事情是由一篇报道引起的,当时的总编辑张友鸾还记得:“……有位记者采访到一条新闻:行政院盖大楼,建筑商贿买政务处长彭学沛,给他修了一座私人住宅小洋房;以致在主体建筑上偷工减料,而且屡次追加预算,超过原来计划一倍以上。我曾听说彭和成(舍我)是亲戚,有些踌躇,拿着稿子去问他,他却说:‘既然确有此事,为什么不刊登!’”此新闻发表后,《民生报》并没有罢休,围绕着这个线索顺藤摸瓜,连连报道,行政院屡次提出警告,徒然无效。成舍我行使“话语权”,竟连国府要人兼自己的亲戚都不放过,这种行为 ,令不少同行觉得其大节可仰,但也让当事人感到“不寒而栗”。很快,这个事件产生了边际效应,《民生报》又刊登了一篇“最有趣味性的特写报道”,惹到了行政院长汪精卫头上:
某日汪院长亲自主持一项重要会议,当与会人员到齐时,而院长不知去向,把秘书人员急得团团转,但遍找无着,正在无可奈何之际,有人发现院长被关在厕所里,因新厦所有门锁,按照规定均为外国进口的高级弹簧锁,而实际所用的,则均为赝品,使用效果甚差。汪因在会前入厕小解,厕门自动上锁,而事后就开不开门了,虽敲门呼救,并未被人发现,汪只有忍耐一时了。
汪精卫被困厕所的新闻,无形中证实了彭学沛贪污舞弊有据,很快成为谈资,为人们所乐道。汪为此发怒,立即召彭学沛责问,彭无言以对,遂提出辞呈。消息被《民生报》得知后,仍穷追不舍,在头条位置,以“某院、某处、彭某,因涉嫌贪污案请辞职”为标题,刊登出来,使得汪精卫更加光火,认为这是对他的重大冒犯,于是以《民生报》“肆意造谣、不服检查”为名,罚令停刊三天。但是成舍我不服,在《民生报》复刊时又登载社论,说明被罚经过,质问行政院,并声言将依法抗争。一场轩然大波由此引起。
在汪精卫授意下,彭学沛向首都地方法院提出诉状,控告成舍我及《民生报》诽谤罪。开庭那天,旁听者甚众,喝彩声不断,成舍我亲自上庭答辩,言辞滔滔,驳斥彭学沛的指控,南京各报也一哄而上,把这件案子炒得沸沸扬扬,成舍我的名字在宁沪一带叫得愈加响亮了。不久,《中央日报》程沧波、中央通讯社萧同兹等新闻同人从中调停,要《民生报》登一个更正声明,彭学沛亦愿撤回诉讼;但成舍我因事实俱在,为了报社信誉,坚决不干,彭为避免事态扩大,不得已撤回控诉,此案也就不了了之。成的精明加执著,于此可见一斑。
对于这次胜利,成舍我后来回忆起来,仍难掩心中得意,他对报人职业的体察,更令人钦佩感慨:
那时候年轻气盛,得理不饶人。并且要想把报办好,就得不怕事,对读者守信用,对自己尽职尽责。那次,也真出了个大风头,开庭那天,旁听的人把法院挤得水泄不通。……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一件事。
汪精卫以堂堂行政院长之尊与一家民营小报斗法,却落了下风,当然不甘就此了事。到7月下旬,汪便找到了报复机会。事起于铁道部从国外购买器材,因办事人员私饱中囊,引起监察院弹劾,汪精卫认为是院长于右任与他为难,乃向正在江西坐镇“剿共”的蒋介石控诉,蒋则从中调停,电文中有“勿走极端”等语。国民党CC派干将张道藩主持的民族通讯社据此发出通稿,南京各报均予转载,《民生报》也以“蒋电汪、于勿走极端”为题,在要闻位置刊登。汪精卫得属下报告后,不与别的报馆计较,独以“泄露军情,鼓动政潮”为罪名,向蒋介石申请“查封《民生报》,治罪成舍我”,蒋即从庐山电令南京卫戍区司令兼宪兵司令谷正伦查办此事。
谷正伦雷厉风行,立即派人查封《民生报》并逮捕成舍我,又通过追究新闻来源,依次把民族通讯社的采访记者陈云阁、总编辑钟贡勋、社长赵冰谷抓来讯问,与成舍我一道,关押在宪兵司令部的牢房里。当局虽然气势汹汹,但人们都明白,这一切都是汪精卫携私报复,借以泄愤而已,所以连监牢看守也不把他们当成犯人。成舍我多年后还感念当时的一个细节:
那次,使我最难忘的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时看守我的那个卫兵,和我开玩笑说,你不寂寞了,这回你们四个人,刚好可以打一桌麻将。
这一次,成舍我等被宪兵司令部关了四十天,同牢四人中,成的年龄并不是最大,但他的世故老练,却给牢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据陈云阁回忆,在抓捕成舍我时,派来的是便衣特务,以借口请他去谈话的方式进行的,“但他很敏感,把常用衣物和盥洗用具都带在一道,特务假装说何必那样,他还是坚持带去。他第二天早上穿上外衣,在天井刷牙,我们都很惊异。他见到我们三人毫无准备的样子,也暗暗发笑”。成舍我此举,虽是汲取了他在军阀时代的北京数次坐牢的经验,但这种敏感和内行里面,却掩藏着常人不具备的智慧以及洞察事物的能力,这是他能够做大事、成大业的重要条件。
至于上面“捏造电文”一案,经过成舍我通过家属暗中托人,取得汪精卫的亲信、外交部次长唐有壬等头面人物同情,出来说项,汪精卫终于同意从轻发落;当局又开具《民生报》永久停刊、成舍我不得以本名或其他笔名发表批评政府的文字,成本人今后无论到达任何城市,应向当地最高军警机关报告行止等若干条件,又叫每人各写一张悔过书,才准予保释,9月1日蒋介石的电令一到,众人便恢复了自由。
成舍我在获释后第三天,即去拜谢唐有壬,唐授意他写一封信向汪精卫示好,然后在汪接见时,不妨表示拥护之意,如此不仅可办报,还可做官,名利兼收,但被他断然拒绝。唐继而婉转劝告,晓以利害,说一个新闻记者要和一个行政院院长去碰,无疑是要头破血流的。成舍我当时的答复是:“我与汪精卫碰,最后胜利是属于我的。”“唐为之谔然不解,舍我先生对他说最后胜利的理由:第一汪的年龄比他大;第二汪不能一辈子做院长,而他能一辈子做新闻记者;第三做记者可以抱定主张,始终不变,搞政治则诱惑太多,不容易永保令名。”
果然,仅仅两个月后,1935年11月,汪精卫在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期间,被刺受伤,出国就医。
成、汪二人再次碰面,是在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首届国民参政会期间,当时汪精卫在汉口招待参会的参政员,见到成舍我,听说他在香港又创办了《立报》,创业阶段,举步维艰,不免要寒暄一番,表示慰问,但成舍我旧恨未消,并不买账,回答说:“在香港办报,诚然困难很多。所幸香港虽然还是殖民地,但在相当范围内,还能实行法治,好像还没有过不依法律手续,封报馆捕记者的事!”这一番充满挑战意味的话,刺激得汪精卫立刻站起身来,谈话也就不欢而散了。又过了多年后,成舍我关于“汪不能一辈子做院长”的话终被应验,他在《我们这一代报人》一文中记道:
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个月前,当我在南京挂出了《民生报》招牌的那一天,我从中山陵回来,经过所谓梅花山“汪墓”,只见许多人在他墓前排队撒尿。
回首当年,亲历了那一时代“不幸”的成舍我,是有理由出此刻薄感慨之语,并且自言“幸运”的。
成舍我的“吝啬”
重庆版《世界日报》于1945年5月1日发刊,然而开张伊始,就运交华盖,报纸出刊后一个多月,时值重庆多雨季节,一场暴雨袭来,报馆楼后的下水道堵塞,整个排印工厂全部被污水淹没,机器被水淹,有很多纸,因来不及往楼上搬,也都泡汤了,报纸被迫停刊十多天,损失严重。
据当时《世界日报》总编辑陈云阁回忆,为报馆被淹一事,成舍我向主管部门市政府公务局提出修整下水道申请,未得反应,以他的好斗性格,于是断然聘请江一平等著名律师公开登报,要求赔偿全部损失,这一威胁立即见效,重庆市市长贺耀祖见事情闹大,不得已两次亲临视察报馆下水道堵塞情况,严令公务局日夜抢修,报纸才得继续出版。嗣后,成舍我还在报上亲撰启事,宣布因此遭受拖累损失的订户读者,将得到补偿。“这些手法都对报纸声誉与发行增添了许多有利影响,所以当时就有不少同行说他在利害、是非问题上既能破除情面,毫不忍手,又善于迎合社会心理,争取读者同情,说得上一个报界狠人。”这个评价对于成舍我,是太确当了。
对于自己的记者,如在新闻竞争中没有尽到职责,成舍我更是毫不容情。抗战胜利后,南京中山陵园展出一只大玳瑁,《世界日报》驻南京毕群记者照抄一家小报的新闻,给北平拍发电讯,却错做“大乌龟成舍我便去电质问:“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何也?”文字诚然精练,且有魏晋六朝小品遗风,但不免让人难以接受,认为这位老板也太严厉且太“尖酸”了。
成舍我的“吝啬”在同行中也是十分有名的。他的一个老友说,这都是他小时候家里生活太苦,十四五岁外出谋生,在上海啃烧饼度日,在北京“逐水草而居”,养成的习惯。因而当报社里同事钱不够用,每每叫苦时,他大不以为然,总说人家太浪费了,自己当初如何如何刻苦,而且“大言不惭”地说:“如果这样过,每月都有富裕的。”还有一件被引为笑谈的事,抗战后期,《世界日报》在重庆恢复出版,成舍我一如既往对职工采取低待遇,甚至连食堂也只许吃糙米,做菜不放油,职工屡次要求改善伙食,成老板不允。适逢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成舍我午饭时到食堂传达消息,并说:“你们看,罗斯福是金元王国的总统,营养是很好的,可是他也死了,可见营养的关系不大。”他话音刚落,举室哗笑,可见人们对这位老板的吝啬既习以为常,也是无可奈何了。
毕群1945年在重庆加入《世界日报》时就深有体会:“成舍我办报素来有他一套‘精兵简政’的办法,用人不多,主观上想要报社职工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而两个人拿一个人的工资。旧新闻界都评价说:‘成舍我是刻薄起家。’这样的评价,过去只是听说,现在亲身尝到滋味了。那时我是光棍一条,生活上除抽点香烟之外,没有其他更大的浪费,但月薪只刚够维持一个人普通生活水平。其他有家室的同事更苦不堪言了。”
毕群的这一段似嘲笑似挖苦的介绍,确是为成舍我的“吝啬”画了一幅像。然而奇怪的是,成舍我在《世界日报》开的这道流水席却人来人往,不愁没人前来“赴宴”,而且这种艰苦环境“逼”出了一批颇具才干的编辑、记者,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要听说哪个人是从《世界日报》出来的,别的报社都乐于接纳。
毕群还感慨道:“我曾经听到一位新闻界前辈说:‘《世界日报》实际上是一所新闻从业人员训练班 。’这话含蓄着辛辣的讽刺意味,同时又是真实的写照。”
“我要说话”
1952年,成舍我举家从香港迁往台北。本拟在台北复刊《世界日报》,因国民党当局实施报禁,办报计划搁浅,于是创办了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声称要“培训一万名新闻干部回大陆”。几年之中,他断绝了办报念头,一面教书,一面写点评论或专栏之类的文章。
但这并不意味着成舍我就此改变了自己的“斗士”形象,1955年3月,在立法院第十五次会议上,他以“立法委员”身份,以《人权保障与言论自由》为题,向当时的行政院长俞鸿钧发难,为两位因言论罪被国民党长期关押的新闻界元老——失踪五年的龚德柏和被捕三年的马乘风鸣不平,追问何以“不审?不判?不杀?不放?”并质询:“新办报纸杂志何以不许登记?”他以如此凌厉猛烈的作风,挑战执政当局的“戒严”、“报禁”措施,让同人感到振奋,也令当局大为震惊。成舍我遂成为台湾舆论界“反对派”的一面旗帜。
此后十余年,成舍我“蛰伏”台岛,收起锋芒,潜心办他的新闻学校。但是人们并未因此忘掉他,l967年他七十寿辰时,台湾新闻界以公宴方式予以祝贺;又过了十年,他迎来八秩大庆,为了避免故旧门生过度铺张,筹办盛大的庆祝,乃提前携夫人离台赴美避寿宴,作为期一月的考察,一时传为佳话。
1988年,台湾开放长达三十七年的报禁时,成舍我已九十一岁高龄,他再酬壮志,创办了《台湾立报》,在发刊辞中表明办报的目的:“第一,为供应世新校友及在校同学,实现其所学的新闻理论及增进其技术。第二,开放报禁证明台湾确已有新闻自由。”这是他一生中创办的最后一个出版物,此时,当年和他一起在烽火岁月的报坛上冲锋陷阵的老友,都已驾鹤西去,只留下他,为这时代作最后的见证。
1991年4月1目,成舍我病逝于台北三军总医院,终年九十四岁。临终前两个月,肠梗阻、肺炎等症并发时,他无法发声,每日挣扎用颤抖的右手书写“我要说话”几个字,令周围亲友百感交集——成舍我一生都在为争取自己的“话语权”而奋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流露出来的心声,正是他毕生事业和人生目标的写照。
在他身后,一个时代无声地结束了。
(摘自《温故·1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1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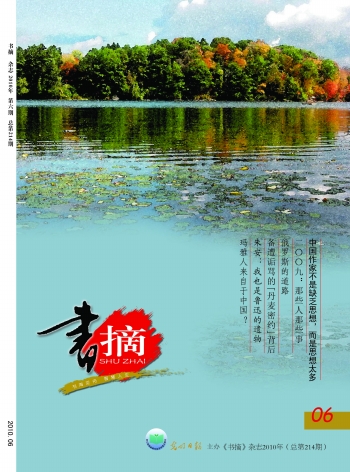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