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先生家的下午茶
我的父亲是陈占祥。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金风送爽的10月,我们一家在前门火车站下车,被接进了离火车站不远的“解放饭店”。
梁先生很快就请我们全家去清华新林院八号的梁宅做客。喝茶时,梁先生兴奋地对父亲说,这些日子太忙了,正到处招兵点将,把全国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到北京来。像建筑系的吴良镛、程应铨、汪国瑜、胡允敬、朱畅中……现在都是青年才俊,将来必是擎天之柱。还在邀请一些有资格做各部门领导工作的人。像戴念慈、吴景祥、赵深。大国首都的建设可不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有人在国内或国外受过专业训练,却没有实践经验;也有人实践经验很丰富,可没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要找到两全其美,又在同业中有口碑的人才,确是凤毛麟角。土建工程师和建筑师缺一不可,二者只有合作默契,才能造出品位高、效率高,并且经济实用的建筑。这是百年大计呀!
父亲应答说,这正是做规划最担心的事。规划做得再好,碰上蹩脚建筑师,就像碰上无厘头化妆师一样,把个闭月羞花的姣好容貌,做成一张大花脸,岂不是啼笑皆非。
梁先生说,衣服买得不顺意,顶多送人或丢掉;哪怕媳妇讨得不称心,一拍两散就是了。如果一片片的房子盖得不伦不类,那就是几十年上百年也无法纠正的错误。
父亲答:全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个北京城,我真是诚惶诚恐,唯恐愧对先人和后人。北京是传承了几千年文明史的瑰宝,规划时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不然就是千古罪人,会像秦桧一样遗臭万年的。
父亲回忆说:“梁先生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把茶杯举起来,和我的茶杯碰了碰说,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那天的下午茶,梁先生只约了我们一家人,大约是想和父亲单独谈谈,多了解一些父亲以前的经历。
他代表清华建筑系向父亲发出邀请,请父亲每周到建筑系讲授一次规划学。他说,清华有一个专门研究北京城建问题的小组。
林徽因插话说,最近有些机关部委,自己圈块地就盖起了房子,好像切一块豆腐那么简单。根本不知道要征询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意见,更不知道要事先征得有关部门批准。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连批地皮的人也不懂城市规划为何物,问题就更大了。
梁先生说,那就不是问题大,而是太可怕了。北京城需要整体保护,绝不可伤筋动骨的。
父亲说:西方工业革命的前车之鉴,中国不能重蹈覆辙了。当年曼彻斯特由于无秩序无计划地使用土地,住宅区和工业区混杂交叉,结果是水源污染、空气恶浊、瘟疫流行,曼彻斯特人口的平均年龄不到29岁!
林徽因立即情绪激动地说,伦敦、纽约何尝不是如此?半个世纪前的拆烂污,几十年都揩不干净。规划做不好,贻害百年。过去洋人在中国横行无忌,零敲碎打地乱造些不伦不类的洋房,有些建筑简直是恶俗不堪,在他们国内都是不入流的,却到我们这儿来耀武扬威,破坏了堂堂古都的优雅格调。今后这种荒唐事休想在北京重演。
父亲和梁思成夫妇年龄相距十几岁,但谈起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似乎有说不尽的共同语言。父亲的一口宁波官话谁听起来都费劲,不得不改用英文交谈。林徽因突然兴奋起来,她感慨说:这么多年,还没碰到过一个英文这么漂亮的中国人,真过瘾呢!
林徽因说:还是让他用英文讲课吧,这样效果更好些,建筑系学生的英文水平都不错的。
从此,父亲在清华每周一次的上课,用他蹩脚的宁波官话,实在用中文讲不清的概念就改用英文词汇替代,或索性都讲英文。父亲总是每周上课的前一天下午从城里赶到清华,当夜就住在梁先生家里,第二天课程结束再返回城里。
一起做梦的日子
我清楚记得父亲刚到北京时那种神采飞扬的样子。北京珍藏在他心中多年了,他像熟悉手上的纹路那样熟悉北京的大街小巷。说起北京胡同的名称,哪条街与哪条胡同相邻,父亲脱口而出,很少有误。
父亲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我天生就应该学规划吧!不过,我对北京的了解都是书面的,这对做规划来说是太不够了,一定要走遍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了解了每一处细节,才有资格说话。”
父亲的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任命登在了《人民日报》上。为了规划调查的方便,市政府派给他一辆银灰色的华沙车,一位专职司机。壮心不已的父亲正式走马上任了。
车里坐不下那么多一同出行的同事,父亲就索性和大家一道骑自行车,他说这样穿胡同进小巷更方便。
经过两个多月的奔走考察,他对未来北京的规划基本有了感性的认识。更让他庆幸的是,随时随地可以同梁思成夫妇这一对良师益友交流想法。
在此之前,梁先生对北京未来的规划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方案。历史悠久的北京规划早已成熟完美,无法把一个庞大的新中国首都行政中心再硬塞进旧城,它的功能已经饱和了。父亲说,犹如一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主人在里面生活了很久,各式家具都各得其所,使用时得心应手,风格也协调统一。即使有些已经破旧,修补一下不仅无伤大雅,还增添了岁月沧桑的韵味。突然有人非要把一大堆新家具塞进老房子,可房子里挤不下了,每一件老家具又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怎么办?把旧院子拆了,在废墟上建新院子?把黄花梨、紫檀木砸了,把锯末板、胶合板做的家具搬进去?把真正的宣德炉扔进废品收购站,把琉璃厂的仿古青铜供起来?
父亲说,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新林院八号和梁思成夫妇、金岳霖、程应铨畅谈北京城未来的蓝图,在温暖的梁家客厅里编织着他们共同的北京梦。在他们心中,明天的北京,将是一座有着世界最独特景观的东方花园。在世界各国首都中,很少有哪一座都城像北京这样,拥有位于市中心的南海、北海和什刹海那样大片的水面和绿地。
他们计划将来以三海为中心,把中南海围墙拆除,让三海与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连成一片。北面以什刹海、积水潭为船码头,驾船缘北直抵昆明湖。沿途两岸遍植垂柳,形成一道绿色长廊,游船在柳荫下缓缓驶过两岸精巧的小型码头和水边公园。这样,历代帝王的离宫就与城市环境紧密结合到了一起,把皇家的禁苑变成人民的绿地和公园。
未来应当在天安门T型广场建成美丽优雅的中式长廊。通透的中式长廊可以使园内的景观与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交相呼应,也可以与城内的景观融会贯通。市民们能坐在长廊中憩息,廊中一侧是皇苑内的亭台楼阁,湖光山色,另一侧是长安街繁华的街景,那时的古都才真正成为老百姓自己的城市。
金岳霖先生敲着茶几高声笑着说:你们的计划尽是水中月、镜中花。哪天老佛爷从陵寝中爬出来,一个个都推去午门问斩!
林徽因说,去午门之前,天安门前的“千步廊”也一定要恢复,那是一支千古绝唱!
梁先生说:“北京周围的城墙长达39华里,这是北京旧城的边界和最宏伟壮观的纪念性标志,也是城市建筑形体上的重要遗产,未来一定要把它建成举世无双的——”
“空中花园!”梁先生的话还没说完,父亲异口同声地和梁先生一起说出了这四个字。
回忆起这段谈话,父亲神色黯然。
即使是在40年后的康奈尔,说起被埋葬的梦想和自己为之付出过生命中的盛岁年华,父亲仍禁不住动容。不管梁先生后来主持了多少次批判“右派分子陈占祥”的大会,他从来都没有一句对梁先生的怨言,“任何时候,做人做事都要设身处地。如果我和梁先生的位置颠倒一下,我不能保证自己就比他做得更好”。父亲对我说:“我理解梁先生的处境,也永远珍惜我们一起做梦的日子。我们都太爱北京了!我们见过国内外那么多的城市,正因为见得多,才有比较,才更清楚北京有多么独特,多么珍贵。然而这些唯一的、别人永远不会有的宝藏,都被一天天地推倒了、铲平了,代之而起的是和西方各城市大同小异的高楼大厦。可我们心中的北京,永远和我们的梦想同在。”
离开“都委会”的日子
“都委会”终于解散了,“梁陈方案”进入尘封的档案库。父亲调入北京建筑设计院当了工程师。
“梁陈方案”失败带来巨大的挫折和失望是可以想见的,父亲毅然选择的道路,并不是他曾经想象的阳光普照的桃花源。
梁先生也有同感。他说当年解放军进城,拿着军用地图请教他,请他标出需要保护的古建筑和文物时,他的感动难以言喻;但曾几何时,这座没有毁于战争炮火的珍贵古都,却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化为烟尘,这是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
梁思成直言不讳地对父亲说:毛主席可以领导政治、经济,但他根本不懂建筑,他领导不了建筑,彭真也一样。党的领导可以不是内行,但外行必须尊重内行,不能乱指挥。
这样的话,梁先生可能不止对父亲一个人说过。
“你当时怎么回答呢?”我问。
“我说,无知可以原谅,无知而有权不仅不能原谅,而且危险可怕。”父亲说。
为了北京规划,梁先生和彭真争得面红耳赤,他理直气壮地对彭真说:“在政治上你比我先进五十年;在建筑上,我比你先进五十年!”
1953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该小组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办公,被称为“畅观楼小组”。梁思成、陈占祥、华揽洪等原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不再参与北京市总体规划编制。
林徽因生命中的最后岁月
1954年冬天,是林徽因生命中的最后一个严冬。在扑面而来的批判大潮面前,梁先生先病倒了。父亲和原“都委会”秘书长王栋岑赶去清华园探病,已经病入膏肓的林徽因强撑着起来迎客。她用生命中最后的能量,当面向王栋岑驳斥对梁思成的种种批判,为丈夫和自己做了犀利而无畏的辩护。
她对王栋岑说,你们拆的古董至少有八百多年历史,有一天后代子孙懂得它们价值之时,你们再建的就是赝品,是假古董。那一天会来的!她还谈了许多对批判“大屋顶”的不同意见。思路之清晰,锋芒之锐利,还有那不减往日的所向披靡之气势,完全不像距生命尽头只有几个月的垂危病人。
在此之前,郑振铎曾请文物界名人在欧美同学会聚餐。席间郑振铎对乱拆古建大为伤感,说推土机一响,老祖宗留下的文物就寿终正寝了。在场的历史学家兼副市长吴晗却不以为然,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官话。
梁先生说,那种味同嚼蜡的官话,连比他位高权重的彭真都不屑一讲,他却大言不惭,津津乐道。林徽因虽已病得弱不禁风,听后仍当即拍案而起,点着吴晗鼻子,疾言厉色怒斥的声势如击鼓骂曹。
父亲说,林徽因早逝,也许是她的造化。她是个多么率真的性情中人,敢怒敢言,快人快语,从不会审时度势,曲意逢迎;若碰上1957年的反右和后来的“文革”,她的遭遇不可想象。就如我们无法想象鲁迅活到解放后会是什么命运一样。或许正如某权势人物断言的一样,要么闭嘴,要么坐牢。
1955年初,林徽因病得更厉害了,需要进城就医。她的身体已完全禁不住从城内到清华的往返颠沛,可城内一时还没找到能住的房子。
父亲回家和母亲商量,决定把梁思成夫妇接到我家来住。我刚从住宿的学校回家过周末,听到父亲的提议,欢天喜地:“爸爸,我跟你去清华接他们!”
母亲边织毛衣边皱着眉头,犹犹豫豫地说:“肺结核可是要传染的呀,我担心孩子年纪小。”
父亲说:“注意隔离就行了,准备几套专用碗筷,多煮一煮,问题不大。再说,梁先生正在城里找房子,只暂时住些日子。”
我从学校回来,站在她住的房间门口,悄悄地向屋里张望。徽因妈妈穿着一件蓝色的旧棉袍,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顶。她半倚在床上,轻轻向我摆摆手,既是打招呼,也是示意我不要走近她。我呆呆地倚在门框上,远远望着她,眼前总是出现新林院八号一张张照片上那些让我难忘的美丽面庞。
我看着梁先生亲自打开炉筒上方的炉门,一铲一铲地往里添着煤块。那间卧室的取暖炉子很高,至少有一米二左右,梁伯伯看上去非常吃力。我去问父亲,为什么不让阿旺娘帮忙?连我也可以帮忙的。父亲轻声告诉我,梁伯伯说了,炉火是徽因妈妈的命,稍稍着凉就有危险。梁伯伯一直是亲自侍弄炉子,别人弄炉子他不放心。这么多年了,都是他自己动手,时刻监视煤火的燃烧情况,绝不能让煤块烧乏了。其实他自己,也患着多种疾病,由于患有灰质脊髓炎,常年穿着钢背心,但他还是竭尽全力地呵护着跟自己一样多病的妻子。正说着,梁先生走过来,从客厅炉子上一只蒸锅的金属盒子里,用镊子夹出消过毒的针头针管,放进一只白搪瓷的腰形盘子里。
“又该打针了?”父亲问。
梁先生抬腕看看表,点点头,端着搪瓷盘子进了卧室。无论是静脉注射还是肌肉注射,梁先生都技艺精湛,水平与专业护士不相上下,那都是长年照顾妻子练就的本领。林徽因体弱,切除过一只肾脏,有时忽然无名火起,易躁易怒,情绪激动。但梁先生永远不温不火,轻声细语,耐心安抚。为了怕主人误会,他和父母聊了很多关于中医的医理,说起阴虚阳亢患者常有的症状。他说,健康人往往不能体会病人的状况,我也是病人,对此有切肤之痛。物质决定精神,脏器的器质性病变,真的会改变人的脾气性格,那就是病,很难用理智控制的,不然病人和健康人就没区别了。梁先生在我家常谈起他对疾病的感受,仿佛多少难言之痛都被他对妻子博大深厚的爱意融化了。
“这是我见到的真正好男人,好丈夫。”一生中,我无数次听到父亲的感慨:“都说母亲对儿女的爱才是无私的,我看梁先生对林徽因的爱才是无条件的,义无反顾的。”
无论是母亲炖好的鸡汤肉汤还是银耳汤,或是蒸好的蛋羹,梁先生总是先用小勺尝一尝冷热咸淡,觉得合适了,才端进屋里。有时就坐在床畔,一勺一勺地给林徽因喂食。母亲为此曾有感而发道:“我一辈子不羡慕谁家荣华富贵,有钱有势;最羡慕人家夫妻恩爱,相濡以沫,像梁先生夫妇那样。”
不久,林徽因肺部大面积感染,高烧不退,住进了同仁医院。随即,梁先生也被发现传染上肺结核而住进了妻子隔壁的病房。父亲去同仁医院探望时,命悬一线的林徽因已经气息奄奄,她只是以生命中最后的力气,用力注视着梁先生和父亲。
“我只见她的嘴唇轻轻动了动,说不出话来。”父亲说,“看见她和携手一生的梁先生默默对视,久久无语,那种诀别前的相依不舍,真让人肝肠寸断。我别转头冲出门,才敢让泪水流下来。”
1955年3月31日,是梁思成夫妇结婚27周年的日子,也成了林徽因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夜晚。
与梁思成先生的永别
1971年年底一个严寒的日子里,父亲来到北京医院。从十几年前反右派的批判大会至今,父亲已经十几年没有见到梁思成先生了。他知道梁先生的难处,但他也更自尊自爱,不愿因自己的身份给梁先生添麻烦。
得知梁先生病重的消息后,父亲觉得必须去北京医院了,不然,可能会永远为此而后悔。
林洙在《梁思成与陈占祥的友谊》中写道:“他在北京医院住院两年多,基本没有亲友来看他,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听见病房里有谈话声和笑声。我正在惊奇,一眼看见陈占祥正襟端坐在梁思成的对面。他的头发梳理得整齐光亮,容光焕发,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和风衣。黑皮鞋擦得锃亮。那年头除了接待重要的外宾谁也不会这样穿着打扮。我的心为之一动,急忙转过身去,掩盖住将要流出来的泪水。十四年啊!十四年,这两位挚友终于又倾心交谈了。”
父亲在他《忆梁思成教授》的文章里则说:“1971年末,在那个难忘的寒冬日子里,梁先生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情真意切地向我说: ‘占祥,这几年,多亏了林洙啊!’”
我想,父亲把梁先生这句话作为文章的结尾,把无数句梁先生想说而没有说的话都说出来了。那是梁先生心中的一个结,系在他自己的心里,也系在他和朋友之间。就像中国写意画中的留白。
(摘自《多少往事烟雨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3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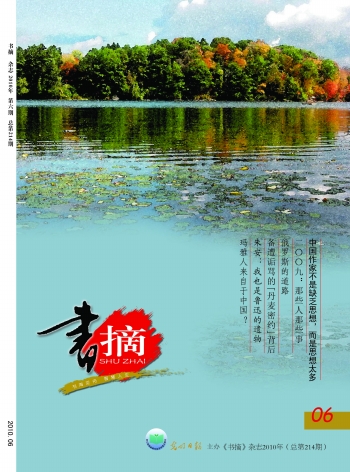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