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初中央即将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邀请党外人士一起参加。
到北京的当天下午,即赴政协礼堂,听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很清晰。最使人兴奋的是下面一段话:国内形势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时代已经过去了,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始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但绝不强迫别的民主党派参加。毛主席讲话一向很风趣,如谈到整风时,说这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和风细雨。从录音里听到他在讲话时,不时引起哄堂大笑,并听到刘少奇、马寅初等同志插话,真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我们听了录音,也感到兴奋、舒畅。
听毕,我和傅雷同志即相约赴中山公园聊天,我们觉得双百方针实在正确,党真英明,都认为今后更应响应党的号召,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尽力。正如《傅雷家书》所载,他当时给他儿子信中所写的,他衷心感到社会主义的可爱,感到社会主义国家很多,而“毛泽东全世界只有一个”(天下无双)。可见他那时正是最热爱共产党、热爱和由衷尊敬毛主席的。谁知后来竟也中了“阳谋”,陷于罗网。
第二天上海小组分组座谈,康生还特地做了启发报告,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听说也有不少代表对“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尚有疑虑,譬如,有人说:“要我发言,先要给我一张‘铁券’。”上海电影名演员石挥同志还以滑稽的口吻道:“这正如京戏《甘露寺》所说的,是贾化(假话)。”
3月10日下午,我刚回到《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解放日报》的杨永直同志已在焦急地等着,说“已接到通知,毛主席接见我们新闻界一部分代表,我到处找不着你,现在约定时间已到,我们赶快坐我的车去吧。”我没有坐定,即相随乘车赴中南海。
我们被引入客厅,毛主席和康生已在门口等候,听到康生逐一介绍,老人家伸出大手,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徐铸成同志?”慈祥地看着我说:“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放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纸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工夫再翻翻其他报纸。”对于主席的赞赏,我心中涌起感激的热泪,感到无比温暖、幸福。看看在座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其他首长没有在座,也没有中宣部的陆定一和周扬同志,仅有康生陪同接见,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我被安排坐在毛主席旁边。
康生先讲话,说:“今天,毛主席邀请新闻出版界一部分代表来谈谈,各位有什么问题请主席回答,请提出来。”会上沉寂了片刻,邓拓同志轻轻对我说:“铸成同志,你先开个头。”我就说:“关于在报纸中宣传双百方针,我觉得心中无数,难以掌握,怕抓紧了,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抓松了,会犯修正主义的错误,请教主席指示,该怎样掌握?”
毛主席含笑答道:“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多学一点马列主义,刚学会学不进去,会吐出来,这叫条件反射嘛,多学了会慢慢学进去,像瓶子装油,倒出来,总会漏一点,慢慢就学懂了。鲁迅学马列主义,是创造社、郭沫若逼出来的嘛,他原是相信进化论的嘛,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列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年轻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主席这最后一句话,使我出乎意外,姚文元曾在上海写些文章,常常揪住人家一句话不放,怎么会受到他老人家的赏识,认为他的片面性较少呢?
后来,毛主席问道:“各位在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究竟还有什么具体困难没有?”
我说:“我体会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意义上,是高价征求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慢慢再加以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我认为这就是高价征求批评。”
毛主席说:“你的意见很对,很好,说下去。”
我接着说:“我们《文汇报》开展电影问题的讨论,收到来信很多,批评相当尖锐,也有一些不同意见,我们故意放一放,好让大家把意见说完,等以后再开展讨论。但在上海却遭到了围攻(指张春桥组织的围攻),请问主席,我们该怎么应付?”
毛主席说:“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这样,批评、反批评、小结,这就叫正、反、合,这就是辩证法嘛,你同意不同意?”
我高兴地回答:“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接见约谈两个小时。那两天,毛主席还分别接见教育、文艺各界代表人物。
大概在12日晚上,上海宣传部长石西民同志召集上海全体代表开会,由陈望道同志汇报毛主席接见教育界部分代表的谈话,徐平羽同志汇报毛主席接见文艺界代表的情况,我则汇报毛主席接见新闻出版界的情况。记得姚文元这个“小八拉子”正坐在我旁边,我汇报毕落座后,曾低声对他说:“毛主席还表扬你的文章呢。”他脸红地点点头,掩饰不住其得意之色。
在大会进行期间,邓拓同志即告诉我,中国新闻记者访苏代表团即将在本月内出发,“团员人选已决定,请你任副团长”。我很感惶恐,怎敢当此重任呢?后来想,有团长负责,我挂个空名,大概也负不了什么责任,就欣然答应了。
大会将闭幕时,邓拓同志告诉我,访苏代表团一周内即将启程,三天内务必赶回北京。
留沪实际只有两天,到京的第二天中午,去访晤邓拓同志,哪知短短三天中,“行市”变了,原定任访苏代表团长的林朗同志(俄文《友好报》总编辑)不去了,改派我为团长。我听到这消息,真是“受宠若惊”,非常惶恐。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一向被称为“老大哥”,怎么可以让我担任团长呢?(全团十二名代表中,只有我和《光明日报》的张同志两人非党员。)我坚决向邓拓同志表示,不敢担负此重任。邓拓同志说:“这是中央决定的,你不必谦逊了。”我听后真是感激涕零,衷心感激党如此信任。总之,我那一段时期的心情,也仿佛如傅雷同志在“家书”中所表达的,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崇敬,达到了最高峰。
访苏时,赫鲁晓夫接见了我们。会谈后,就在他办公室里和我们全体合影留念。合影时,我靠他站着,他还挽了我的手。在飞机起飞前五分钟,苏联外交部人员才赶来分送每人一张刚冲洗出来的照片。这张照片,“文革”中害我吃了不少苦头,被造反派抄家时抄去,指为我的反动“罪证”,迫使我多次尝到“喷气式”的味道。
这次访问,共历时四十四天,加上回京后又清理团内事务,耽搁数天,那时,所谓“鸣放”高潮已接近尾声了。在莫斯科时,看到《文汇报》,认为有些标题太尖锐,火气太大,根据我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有些题材尖锐的新闻,标题应求平淡。反而内容一般,标题不妨“打扮”得突出些,这是老编辑的一般的常识。为什么这一段《文汇报》标题如此“火上加油”,我很不安。到京的当晚,即和本立同志通了“长途电话”,说了我的看法,问他为什么标题火气这么大?他对此含糊答复了。(直到“文革”以后,原《文汇报》参与编辑的同志告诉我,在那一段时期,编辑部负责人几乎天天接到市委“一言堂”——柯庆施的指示,要《文汇报》加温再加温。原来这也是引蛇出洞,“阳谋”的一个手法。)
回京的第二天晚上,我去访问邓拓同志,他说:“你们出国后,《文汇报》在贯彻双百方针及帮助我党整风方面,干得很好,所以很受读者欢迎,听说发行数已接近二十万了。”我说:“有些标题太火辣辣,我总不放心。”他说:“这些,是小毛病,不要紧。”接着,他对我说:“我们《人民日报》也有计划想提高一步,但是上面卡得很紧,比如,我准备写一组题目,共十篇社论,但报上去一直没有消息,写好的社论稿,大部分扣压了,其中只发了二篇,把我的计划全搞乱了。”接着,他悲愤地说:“有时,我真想辞去《人民日报》的职务,另外去干一张报。”
飞回上海后,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同志曾到我家中,希望我去参加即将闭幕的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也仿中央的惯例,吸收党外代表性人士参加,帮助党整风)。
我说,我正在赶写《访苏见闻》,而《文汇报》现在党员与非党同志融洽、合作得很好,我没有什么意见可谈,坚决回绝了。
第二天,白彦副部长又来,说:“会开得很热闹,你一定去听听,因为会议快要结束了,我们不准备发给你出席证,你拿我的出席证,今天下午一定去参加吧。”说毕,即掏出他的出席证交给我。
盛意难却,我当天就去了。发言者确是争先恐后,发言的内容,差不多全集中在消除党群间的隔阂即拆墙问题(听说这一名词,最初还是中央某首长提出来的)。
我由此触发,要求在第二天大会上发言,大意说:“墙”是很容易“拆”掉的,只要彼此尊重,有共同语言,党与党外人士就可以水乳交融,很好地进行工作。我举《文汇报》一例,说我和钦本立等同志,就合作得很好,遇事坦述相商,《文汇报》就不再存在“墙”的问题。可见,领导的党员,至少要懂一点本行业务,如果完全外行,那就“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
现在,领导应该懂行,已成为常识。可是我那天的一番发言,却闯了大祸,被指为大毒草,说是推广“反党经验”。而且,随后不久展开了反右斗争,“伟大领袖”还进一步指出:外行领导内行,是必然的规律。
当时,钦本立同志问我这个发言要不要见报?我说当然见报。我认为问心无愧,是一片热情,想介绍《文汇报》党内党外坦诚合作的事实,来平息大会上的争论。但一声令下,反右运动匝地而起,这就成为我的重要的“罪证”之一了。
上海的运动,从“抛”出陆诒等同志开始,市委宣传部还希望我“揭批”陆诒,“立功赎罪”,我断然拒绝。过了几天,才由一位复旦大学教授开始点了我的名,我知道风慢慢刮大,但还没有想到雨点,真会降到我身上来。
钦本立同志说:“我们不妨去看看石西民部长。”见面后,石西民同志对我说:我是了解你的,但我做不了主,必须请示柯老。
于是,我们又设法去面见那位“一言堂”。他开头就说:“这事不能由你一人负责。我已对钦本立说过:‘你的一只脚早踹进右倾泥坑里了。’又对我说:‘你自己从思想上挖挖,我想办法搭一架梯子,好让你下楼。’”接着,他说了一段话,使我惊心动魄。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以为了不起了。”原来,他对知识分子是这样看法,真对毛泽东思想深通三昧,不愧后来称为好学生了!
正在此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四次会议,我赴京出席。
初到京时,我曾与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三位先生一起共酌(我们这四位“酒仙”,照例每入京必聚饮一次的)。宋云彬兄叹气说:“我在杭州已被批过几次,恐怕此次在劫难逃了!”我还宽慰他说:“可能有人真正想反党,你是人所共知的党的老朋友,如果我们也被打成右派,岂不令人寒心?万一有事,谁还敢挺身拥护党?”云彬只惨然一笑说:“天下已定,以后不会有什么万一了。”叶、郑两位也说:时局真有些看不透,究竟要发展到什么地步?
过了一天,可能是康生之流授意的吧,在《光明日报》登了一条署名“新闻”,说我去年在民盟新闻小组谈过,《文汇报》复刊后,将一切听罗隆基的指挥。真是白昼见鬼。新闻界的朋友,都知道我这个人很倔强,从来不盲目接受什么人的指使,而且,任何人也不会这么笨,会当众说出心里的打算。
但这是一个信号,一场大风雨就要降临了!
运动完全是“有领导、有计划”进行的,而且早就做了精心的安排。纲领性文件自然是《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一宏文,比几年前我们听到的录音,已经过大改动、大补充,这是尽人皆知的。
7月初,上海统战部的刘述周同志到办事处看我。说“毛主席十分关心你,毛主席昨天接见,我也在座。毛主席特别提到你,说徐铸成的包袱很重,但无论什么样的包袱,丢了就好了。所以,特别叫我来传达他的意见”。
两天后刘述周又来找我,说:统战部长李维汉同志对我也十分关怀,已约定即日见面。于是我们同车到中央统战部。见面后,李维汉部长问我检查得怎样了。我说:我苦苦思索,实在是什么都倒出来了,但还得不到同志们的谅解,说没有交代清楚和章罗同盟的关系。他说:我知道你和章罗没有特殊的交情,我也了解你是一贯对党有感情的,为什么把报引到这条道路上去?受了什么人的鼓励报才这么办的?你应该讲讲明白。我说:“我这个人,脾气很顽固,向来没有什么人会诱导我走邪路。《文汇报》如果办的方针不对头,一切责任在我。”他说:“你的思想不用太褊狭,想想你的上下左右,和什么人接触过?有意无意受到什么影响?”我心想:《文汇报》复刊方针、计划是党中央审批的,邓拓同志、夏衍同志、姚溱同志最关心《文汇报》,但这些,我能讲吗?万万不能讲。他又再三逼我,我只得说:“我平素最钦佩的是傅雷、宋云彬两位,关于文艺学术问题我知识不够,有时向他们求教。主意还是我自己定的。”这间房子里,本来只有李维汉、刘述周和我三个人,讲到这里,我忽然看见旁边一间小屋里,有两个人在记笔记。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了。
宋云彬同志先我陷入罗网,而傅雷同志则因我这一句话,可能要受牵连了,自己追悔莫及。
批斗持续了一个多月,到7月底才结束,作为新协主席的邓拓同志一次也没有参加。我于7月31日乘车回沪,邓拓同志关照唐海一路陪我,大概是怕我寻短见吧。
8月1日傍晚回到上海。不久,又由上海新协出面,召开了会议,又展开了疲劳战术要我交代“罪行”,检查根源。大概共开了四次大会,“柯老”(柯庆施)自然不再“挽救”了。右派的一顶帽子,已飞上我的头顶。
《文汇报》的社长和总编辑,早已换了人。对我的具体处罚,是降职降薪,工资级别从八级降为十四级。我沾了“头面人物”的光,处分算是宽大的。《文汇报》被列为“阳谋”的重点,比例当然更高,其中北京办事处原有记者十余人,除了三人幸免牵及外,几乎一网打尽。
我只记下身历“阳谋”的经过,未加分析、评议,一切留待历史来做结论吧。
有一点想法值得提一下,从那次“阳谋”后,知识分子从此闭口不言,真是万马齐喑了,这大概是“杀鸡儆猴”的战略部署吧。这次“阳谋”的如愿以偿,为以后的“史无前例”做了准备。
(摘自《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2010年1月版,定价:2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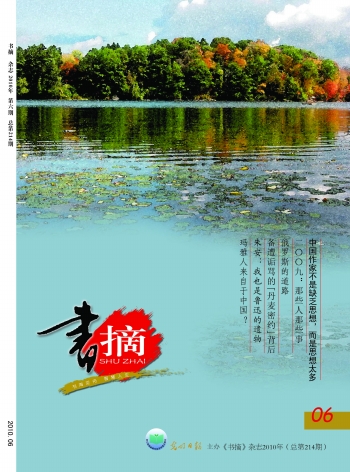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