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娘走后,母亲节几乎成了我的伤心日。曾写五律《母亲节感怀》:不堪逢此节,任流泪千行。痴望天堂远,追思溺爱长。欲孝亲却走,心空岁月凉。梦断慈母线,情怯再无乡!
母亲算得上大家闺秀。祖籍安徽桐城,我姥爷是当地最大的地主。母亲读过几年私塾,在那时的女孩中算是文化人了。八路军过江时,母亲十四五岁,聪明能干,深受工作队喜爱,让她帮着在村里做些妇女工作。以后,又参加革命到了江西,在九江行政公署做秘书工作。用现在话说,很体面、很风光、很有成就感。二十八岁时,与完成解放海南岛任务返回江西的父亲相识结婚。后来,我那辽宁去的奶奶却因过不惯南方生活,要“吃东北的大豆腐”,非逼着我父亲回东北老家。父亲文化程度低,有时签批文件吃力——实际上这是那时工农干部面临的普遍问题——我那极有孝心的父亲却真的以此为由要求退职还乡。时任南昌警备司令的老首长闻讯赶到车站痛惜大骂,却木已成舟。后来我打趣父亲,“唉,不回来我说不定也是高干子弟了。”老爸乐了,并无悔。回头来看,那时牺牲最大的便是随父亲退职的母亲。从温暖宜人的江西来到冰天雪地的东北,成了“家庭妇女”。
那时我刚五岁,却记忆犹新。刚回到东北时是冬天,满眼白雪望不到边,三匹马拉着的胶轮车压的车辙足有半尺多深。我们住的老屋,草房泥墙,北墙窗下放一张旧桌,土炕炕梢放一只残旧的炕琴柜。土炕连着一个上细下粗的土烟囱。烧柴做饭,时常弄得满屋子冒烟。母亲便在这样的屋子里住了下来。
母亲写得一手隽秀的毛笔字,八十岁还能熟记四书五经。她给我最深刻的印记是善良贤淑。困难时期缺粮,爸妈是退职干部,每月可从国家粮库领取几十斤大米白面,这在当时是天大的财富。不过家里人轻易吃不到,只有客人才能享受。而每当村人生病,母亲都要舀上两碗米面送去。经历长期的部队生活,父亲胃病严重,母亲顿顿都要给父亲做点好吃的。家里有个大搪瓷缸,是父亲的“小灶”,可我从来没看到母亲吃过一口。有时父亲发了脾气,母亲才不得不赌气地夹一点点,然后悄悄放到我的碗里。
母亲胆子小,最怕黑天。晚上串个门,东院走到西院都要找个做伴的,从不敢自己走。我上初二那年,附近一个同学骑着新买的红星牌自行车回家,半路被残忍歹徒抢车、杀害,一时间人人自危。有天晚上学校放电影,结束后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没有同路同学了。夜漆黑一片,根本看不见路,我转着圈不敢出校门。正在这时,母亲焦急的呼唤声从远处传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母亲怎么可能会到这儿来?等我又听了一遍,才确认是母亲。原来,母亲看天都黑透了我还没到家,顿时急了,连灶里的柴都来不及灭,一个人摸黑走了四里多山路赶到学校。母亲带我回到家时,院子里站满了人,邻居们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正要分头去找。邻家高大娘责怪母亲说:“你平时胆子小的连东西院都不敢走,今天怎么疯了!”那时小,直到多年后,我才认识到,那不顾一切的“疯狂”背后,是怎样的母爱。
有一次,母亲病得厉害,确诊是克山病。这种病死亡率极高。那几天我家院子里总是站满了乡亲,看病、熬药,干东干西。天佑好人,母亲幸运逃过一劫。但母亲的病还没全好,我也病了,高烧昏睡。弟弟做了汤,父亲切了最细的面条,邻居杀了老母鸡炖了汤送来,我却什么也不想吃。母亲强挣着叫人扶她起来,做了我最喜欢的鸡蛋汤,端来我面前。当母亲那冰冷的手触到我火一样烫的前额时,我在昏沉中哭了!我的病很快好了,与其说是药物的功效,倒不如说是母爱的滋补更确实些。母亲却因受凉、劳累,再度病危,又躺了一个多月才能下地。这次大病,母亲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后来我参军、转业,到县城、省城、京城工作,每逢稍有时间,总不由自主地跑回家陪陪母亲。九十年代初“深圳热”时,我得到一个极其难得的工作机会,风烛残年的母亲一听要去的深圳在几千公里之外,寝食难安。我虽真心不舍,却也坚决放弃了这次调动,相当于放弃了人生的一次重要机遇。朋友每每为我惋惜,我却至今不悔——母亲的安心足以补偿一切。
母亲走后,每逢看到朋友、同事尚有爹娘可孝敬,总是暗自神伤。父母在时,年节有盼头,回家有奔头。父母不在,这一切都空了。许多次回家,痴痴地望着熟悉的老屋,滚热的土炕,院内厨间的物品,用流泪的心丈量着生死距离,追思父母养育教诲之恩。我的父母之爱,方式、方法,甚至目标完全不同,但爱之深之切却完全相同。父亲眼不容沙,口不留情,言传身教,期望我正直、出色。母亲则细腻温暖,我的每一丝烦恼、病痛,都牵着她的心。我这大半生,从政、从军、从商、当记者,经历万千,阅人多多,也诱惑多多,尚属从容,未有大错,未失初心,实得益于父母。这些年来,我最喜欢唱的歌是《父亲》《母亲》《儿行千里》,最动我心的是那句“央求你呀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出门在外没有妈熬的小米粥”。亲爱的老爹老娘,我也这样央求你们,下辈子还做我的老爹老娘。
农村老家有块墓地,父母长眠于那里,周围种了一圈松树,洁净而简单。
(作者:郑有义,系中国作协会员、高级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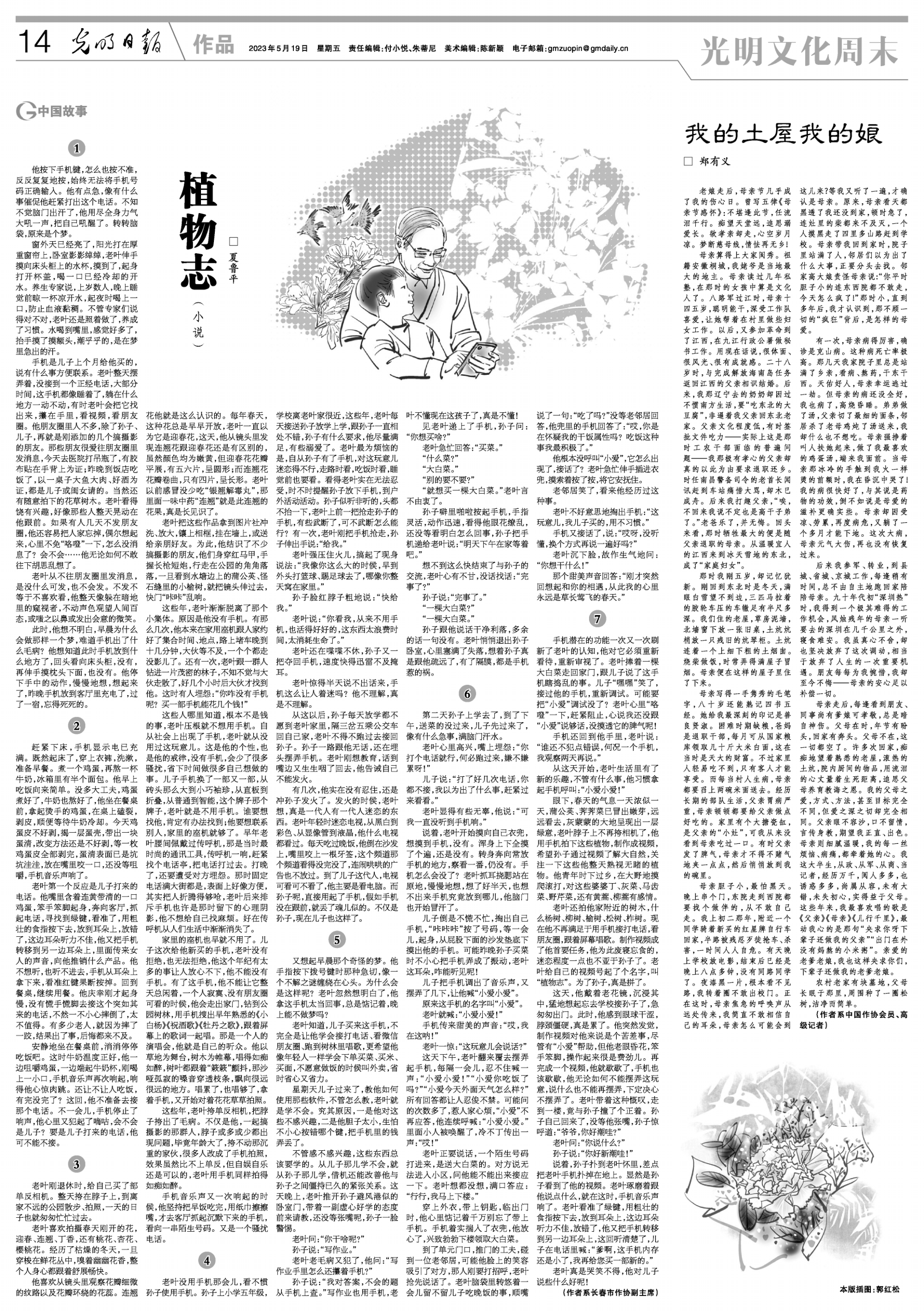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