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众多的文学作品已经对各类疫情进行了或真实具体,或隐喻抽象的描述。在阅读一本包含疫情内容的文学作品时,我们尤其需要关注它在创作时的初衷。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能够击中人类内心深处的情感。
Ⅰ
笛福的小说《瘟疫年纪事》是一部纪实与虚构相结合的作品。小说假托“始终居留在伦敦”的市民H.F.之手,描写了1665年的那场大劫难,实则创作于1720年马赛的霍乱之后,是作为记者的笛福多方搜集来的真实数据资料,加上他作为小说家精心编排的虚构故事。
作品中不时出现的统计表,以及市政府详尽而明确的规章,甚至江湖郎中推销药品时用的花哨字眼,一个教堂墓地里挖的大坑的具体尺寸,受到瘟疫流行打击最大的各个行业的详细分析,还有各个社会阶层在疫情中间的具体反应等细节,为作品平添了更多的可信度。与此同时,你又不能不说它是一部瘟疫期间的伦敦游记。笛福笔下的H.F.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尽管有时会被恐怖的场面和情节吓坏,隐退在家里,但过了三四天,难以满足的好奇心又促使他回到街上。H.F.在伦敦穿街过巷地游荡,尤其为他讲述那些个体的故事提供了可能,尽管那些故事有时候让人感觉离题太远。书中那些具体的街道名称,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和他们似真的故事,都使读者获得一种真实和身临其境的感觉。
与《瘟疫年纪事》中类似游记和“八卦”式的故事相比,加缪的《鼠疫》中对疫情的描述与剖析则更加浓缩与专注,也是本篇文章中最接近我们过去几个月经历的故事。
那场鼠疫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阿尔及利亚滨海的法属省省会阿赫兰。主人公里厄大夫并不仅是见证者,而且是事件的主角:是他第一个发现不断有老鼠死亡,随后是病人的增多,而且都伴随着高烧和腋下长肿块的症状;是他通过医师联合会的书记,希望这一现象得到当局以及相关机构的重视。随着疫情的日益严重,城市被封闭,罹难者越来越多……加缪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而又积极的人物:始终在救治病人的里厄医生,来自法国的公共部长之子让·塔鲁,他一边协助医生,一边记录下疫区的情况,直至不幸罹难;丧子之后抛弃了冷漠的态度,加入里厄医生救护队伍的法官奥通,同样在疫病中罹难;还有从一心逃离这座城市到加入救助队伍的记者朗贝尔等等。唯一真正负面的角色是柯塔尔,疫情开始时他自杀未遂,转而由从中牟利,鼠疫结束时他突然疯癫,从窗户向街上的人群射击。按照加缪的话说:“灾难令我们懂得,世界上值得钦佩的事情,比应当蔑视的要多。”
同样穿越疫区并成为人类大劫难见证的文学人物,还有《屋顶上的轻骑兵》中的意大利轻骑兵上校安吉洛。故事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的民族复兴运动正在酝酿当中。为了保护自己的组织“烧炭党”,安吉洛在决斗中杀死了奥地利军官施瓦茨男爵,随后为逃避奥地利人的追捕来到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恰逢那里爆发了骇人的瘟疫。对于疫病的描写贯穿了故事的始终。安吉洛一度被迫躲在屋顶上,从高处俯视疫病肆虐下的城市。在回归地面生活之后,安吉洛又跟随一个老嬷嬷为死人清洗身体,这也使他直接接触到了那些死去的人,或者某些房屋内部的惨状。接着,他又离开城市来到乡村,见证了离开城市逃难的人群以及乡间的生活,尤其是疫情下自然界的安详。自然万物的这种恬静与安详,给予主人公很多安慰与鼓励。
Ⅱ
提到疫情中的爱情,我们首先会想到马尔克斯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在那个世纪之交的时代,公共卫生条件仍然堪忧,流行病随时可能发生。作品通过三位主人公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反映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拉美社会的变迁:自由党与保守党的内战,各个社会阶层的沉浮,新世纪来临后各种新鲜事物的诞生等等。作品中也有对于霍乱的描写,其主要原因是城市卫生状况和饮用水,尤其是人们根深蒂固的习俗,比如人们相信靠诵读经文消灾驱鬼。乌尔比诺医生建议填平污水沟,而且发明了疫区封锁理论。然而,马尔克斯最想讲述的是一个沉浸在沸沸扬扬的气氛当中的爱情故事。在他的笔下,爱情就像一场瘟疫。三个主人公之一的佛罗伦迪诺·阿里萨在遭到心中的女神费尔明达·达萨的拒绝后病倒,他“脉搏微弱,呼气沉重,像垂死之人一样冒着虚汗。”于是证实了相思病具有和霍乱相同的症状。又有一次,他想象着达萨与医生的婚礼,于是高烧和发抖,感到发自骨髓的寒意,仿佛经历了一场霍乱。然而,他坚信“凭着一种爱的雄心,无论是这个世界,还是另一个世界中的任何艰难险阻都无法将它摧垮。”在小说的结尾,他终于得以与毕生所爱结合。他们在船上挂起代表瘟疫的黄旗,顺水航行而去。至此,爱情与疫情完美合一。
当然,我们也一定会想到意大利文艺复兴三位先驱之一的薄伽丘,以及他的旷世之作《十日谈》,尽管对于1348年佛罗伦萨那场严重瘟疫的描写仅仅出现在作品的开篇部分。薄伽丘简单描述了疫病的特征以及很强的传播和危害性,导致昔日繁华的城市十室九空,阴云密布。无数人在这次疫病中丧生,另一些人逃离这座城市避难。城里人出现三种反应:或躲在家里与世隔绝,或纵情欢乐和为所欲为,或者采取折中的态度,手拿香花芳草或一些香料外出,以便提神和接触充斥空气中的恶臭。然而,薄伽丘立刻告诉他的女读者们:“其实我这个悲惨的开头无非是旅行者面前的一座巉险荒凉的大山,山的那边就是鸟语花香的平原。”的确,在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他话锋一转,提到有七位娴熟文雅的贵族小姐和三位贵族青年,相约到一座乡间别墅躲避疫病,同时用讲故事来消磨时光。如此,便诞生了那100个不拘一格,天马行空的故事。
薄伽丘是一个佛罗伦萨商人和一位巴黎女性的私生子,童年在佛罗伦萨长大,青年时期跟随父亲到那不勒斯经商。当时的那不勒斯国王罗贝托·安如是一位开明而又修养的君主,在他的宫廷中汇聚了大量学识渊博的名家。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和赐予他的给养,以及那不勒斯宫廷与市井中蕴含的戏剧色彩与荷尔蒙,无疑对薄伽丘的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十日谈》中的故事取材十分广泛,从奇闻逸事到街头巷尾谈论的故事,人物上到王公贵族,下至三教九流,表现出对于爱情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其间不乏对教会以及僧侣之狡诈的抨击,以及对于贵族家庭腐化与堕落的抨击,同时也包含一些玩世不恭的态度:为达目的甚至可以不择手段,而这个目的大多与情爱有关。读者果然像是置身鸟语花香的平原上,在爱情故事的欢愉中忘记了瘟疫的痛苦,又仿佛摆脱了疫情招致的种种强制性束缚,就好像是冲破了宗教道德伦理强加给人们的约束,或许这才是薄伽丘真正的用意。
意大利作家曼佐尼的历史小说《约婚夫妇》创作于1827年,讲述的却是1628年—1630年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北部隆巴迪地区。小说以青年农民伦佐和露琪亚的婚礼受到恶霸唐罗德里戈的一再阻挠开始,以婚礼的圆满达成告终。其间,露琪亚曾几次被劫,随后又前往米兰寻找未婚夫;而伦佐在各种求助未果也到达米兰,先是被卷入饥民的哄抢并遭到“通缉”,随后兜兜转转在传染病院找到露琪亚。最重要的是,之前阻挠两个小情人结合的大恶人染上瘟疫而死。可以说,是瘟疫最终成全了一对恋人。难怪小说中的一个神父会产生如此的念头:“如果每一次瘟疫都能引出这样的结局,能让每一件事都只有收场,那么,咒骂瘟疫倒成了罪过了。所以,不妨让每一代人都遇上一次瘟疫,但条件是得病之后能够治好。”诚然,这对恋人的爱情故事仅仅是贯穿小说的一条线索,瘟疫仅仅出现在故事接近尾声的时候,而作家浓彩重抹的其实是17时期世纪意大利北方的政治、历史、社会现实,以及意大利北部的风土民情。主人公流浪的足迹所到之处,都是西班牙侵略者的蹂躏、意大利贵族之间的战争,以及小人物卑微而凄苦的人生,那场疫情大劫难以及各色人等的表现,更是将那个时期的境况描摹得淋漓尽致,隐含着民族解放的必要与渴望。然而,瘟疫的部分对于一对恋人的爱情故事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仅构成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而且满足了读者对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期待,同时也反映了作者本身对于宗教与道德伦理思想的笃信。
《屋顶上的轻骑兵》中的安吉洛也有一段类似爱情的经历:在穿越疫区的途中,他两次邂逅贵妇宝林娜,第一次是在城里被她搭救,第二次则与之结伴而行,屡次帮助她躲避驻军和巡逻兵的哨卡,将她从被隔离城堡中救出,又从霍乱的死神手中将她抢回。最终,二人却因道德礼数而分道扬镳。让-保尔·拉佩诺的电影将这段情感幻化为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成为贯穿整部电影的主线。然而,在让·吉奥诺的小说中,它仅仅是人们在疫情当中可能出现的反应之一,是一段小插曲。
Ⅲ
在很多文学作品中,疫病并非仅仅作为一种实际存在的公共卫生危机,而是影射了人类的某种“病态”生存方式,从而超越了疾病的范畴,成为一种隐喻和寓言式的故事。
意大利作家马拉帕尔特将小说《皮》的第一章命名为《瘟疫》。那不勒斯的‘瘟疫’是在1943年10月1日暴发的,正是盟军部队以解放者身份开进这座城市的日子。瘟疫不仅是小说的开篇,也确定了整部小说的基调:在经历战争的折磨之后,欧洲战败了,带着心中的罪恶感迎接他们的解放者。作为二战后期意大利与英美联军之间的联络官,马拉帕尔特见证了那不勒斯,意大利,甚至整个欧洲经历的一种特殊苦痛。作品所见证的各种战争经历,具有同样的主题与氛围,同样的隐喻手法,也用同样悲凉的腔调讲述战争期间悲惨的故事。这种悲惨不仅仅在于生命的失去,还在于尊严的丧失,以及对人性的亵渎。
同样地,加缪的《鼠疫》也并非仅仅描述1849年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发生的那次霍乱。作品中表现的那种“流放感,”那种痛苦、焦虑和挣扎,正是作家本人1942年在法国南部养病时的亲身感受。他在日记中就曾经把在欧洲大陆肆虐的德军比作老鼠。小说是通过鼠疫期间的隔离与囚禁带来的病痛与离别的双重痛苦,影射“第三帝国”和法西斯专制统治,以及那个吞噬众多人生命的“恐怖时代”。作品出版于1947年,当全世界都在高呼胜利时,加缪却肯定地说:下一次鼠疫还会唤醒老鼠,从而再次对人类造成破坏。如同所有的隐喻作品一样,《鼠疫》所表现的内涵远远超出它所反映的事件本身:它并非一种简单的疾病,也是精神和形而上学层面的鼠疫。加缪将鼠疫发生的地点设定在位于北非地中海沿岸的奥兰市,但从对城市和居民的描述上面,很容易看出那是一座物质文明发达,但精神生活空虚的城市的缩影,反映出现代社会的荒唐与创伤。
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作品《失明症漫记》,是另一个成功的隐喻故事,或者说是描写大灾难的寓言式小说。故事完全脱离或者说是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发生在一个不知名的城市,其主人公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疫病——白色失明症——的“零号病人”。当我们用“正常”的方式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它显得一切正常。然而,当我们突然有一天染上了“失明症”,并非眼前漆黑的失明,而是眼前一片白,无法看清楚“真实的世界。”然而,失明后的世界才是真实的。小说中有一句话:“世界中充满了活着的盲人。”在一个失去秩序的世界里,人类丧失了理智,人性变得丑恶,残忍,冷酷,卑鄙。人类社会所具有的这些丑陋之处,并非仅仅会出现在失明后的世界,它们始终存在,但我们始终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又与失明何异?针对这部作品的创作动机,作者说:“虽然我活得很好,但这个世界却不好。”他正是用“失明症”作为当代社会的暗喻和深刻思考。
意大利作家保罗·乔尔达诺在新作《新冠时期的我们》中写道:“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一句话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和平即将到来。仿佛即将来临的黑夜。仿佛是遗忘的开始。’战争结束后,所有人都急于遗忘,疫病也是一样:痛苦迫使我们面对模糊不清的真相,重新思考我们的优势;它鼓励我们为当下赋予新的意义。然而,一旦痊愈,这些启迪就会烟消云散。”人类是那么善于遗忘,尤其是那些痛苦。所以,战争的惨剧才会一遍遍上演,流行病也一次又一次地对人类造成重大灾难。尽管医学的发展突飞猛进,公共卫生和医疗设施也在不断改善,但与疫病共存或许是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而又无法避免的状态。
战胜疫情那一刻,我们仿佛又回到《鼠疫》中的那个火车站台上,等待或者已经在拥抱因为隔离而久未拥抱的亲人,同时告别疫情期间的那种“流放感”,也用目光和微笑告别在疫情期间曾经唇齿相依的人群,继而回归个人的“正常生活”。或许在这个时候,又会有一部文学作品诞生,用实情、爱情与隐情来讲述我们最近的过往,也用真诚的语言一遍遍提醒我们:不要忘记。
(作者:魏怡,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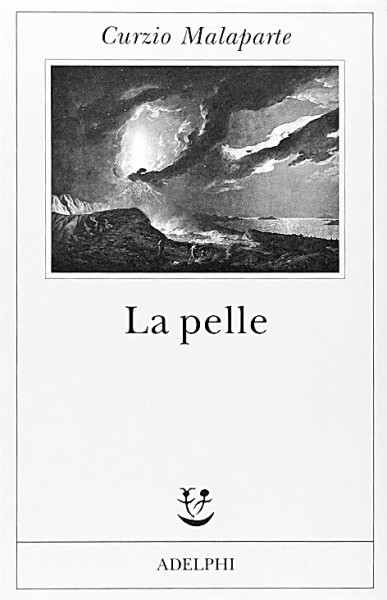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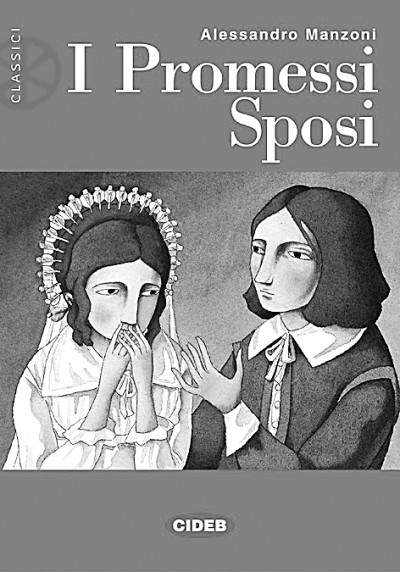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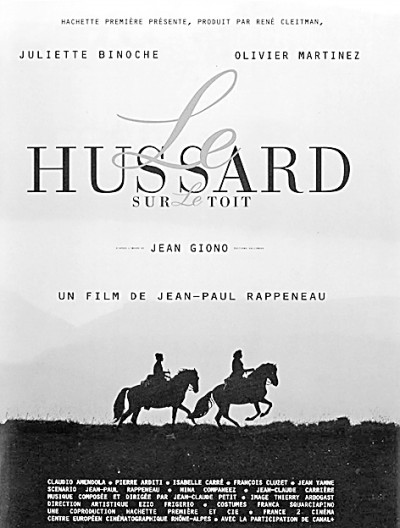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