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与商榷】
近年来,明代卫所制度的研究不断深入,成为明清史研究的新热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们对卫所属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卫所不再仅仅被理解为单纯的军事组织,还兼具行政管理的职责。具体而言,卫所在很大程度上像府州县一样,是独立的管理系统,管辖卫所内的人口、土地、财政、司法、教育和民政等方面,加之卫所又呈现出与州县不同的特质,这对明清五百多年的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全方位的影响,所以值得研究的内容极其丰富(参见顾诚:《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赵世瑜:《卫所军户制度与明代中国社会——社会史的视角》,《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等等)。
毫无疑问,近年学界对卫所的基本属性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如军户世袭、军民并立、互不统属等,但对卫所系统的独立性在定量、定性方面的认知还存在明显差异,这势必影响到对卫所基本属性及其运行的理解,影响到对诸多具体问题的判断。笔者认为,虽然明代卫所的类型多、分布广,但作为系统性的制度设计,卫所的基本属性应具有普遍原则。因卫所具有独立完整的管理权,将其视为传统意义上的辖区,要比视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区更妥当。
卫所属性的判定与辖地面积大小、划界清晰与否无关
学界对卫所属性理解的主要分歧之一是,卫所是否具有普遍的“政区”性质,而判断其政区性质的标准,是否可以用、如何用诸如卫所管辖面积(屯田数量)的大小、划界清晰与否,以及是否切割州县等指标来判断。有学者沿用传统历史地理学的观点,将卫所分为实土卫所、准实土卫所和非实土卫所,认为“沿海卫所的小地盘、防区和屯田区,皆不足以支撑它成为与州县相当的行政地理‘单元’,基本上不具备‘实土’特征”(李新峰:《明代卫所政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1页)。对上述观点,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因为《明史·地理志》使用“实土”卫所一词,只是借用了南朝“实土郡县”的概念,将防区内没有州县的卫所称为“有实土”。用有没有实土和“实土性”来分析明代卫所的“政区”属性,是对“实土”概念的误解(傅祥林:《“实土卫所”含义探析》,《丙申舆地新论——2016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00—405页)。
确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谭其骧在《释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中就提出:“置卫所以统辖军伍,设都司以掌一方兵政,其初本与地方区划不相关。洪武初或罢废边境州县,即以州县之任责诸都司卫所;后复循此例,置都司卫所于未尝设州县之地,于是此种都司卫所遂兼理军民政,而成为地方区划矣。”(《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0页)这句话被后人广为征引,以证明实土卫所的政区属性。然而,他后来对“非实土卫所”的解释却长期为人忽视:“《明史·地理志》将卫所分成实土、非实土两种,实际所谓实土卫所,指的是设置于不设州县处的卫所,无实土卫所则指设于有州县处。前者因无州县,故即称其地为某某卫、某某所,后者即以某州某县称其地,因其地极大多数土地人口皆属于某州某县也。但有一小部分土地人口是属于卫所的……并非真正无土。”(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书前影印插图)在这里,谭先生的解释已非常清楚,实土与非实土之别在于是否当地设有州县,并不是有没有土地以及面积的大小,事实上明代的内地卫所、沿海卫所以及在京卫所(在内卫所),也都是有屯地的。
如果认为只有设在府州县系统“力所不及”地区的卫所,才充当行政区划单位,也不符合明代卫所的实际情况。因为尽管边地卫所普遍被认为具有现代政区属性,也确实独立管辖有大片疆土,但不同卫所之间很难讲有清晰划界,大量的边地卫所(实土卫所、羁縻卫所)之间的边界,反而不如内地卫所、沿海卫所的辖地更清晰。正如周振鹤所说,“在古代,由于开发程度较低,许多政区都没有明确的边界,只有大致的范围”(《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中华书局2013年,第29页)。因此,管辖面积的大小和划界是否清晰这样的现代政区的指标,并不能直接对应古代政区。考虑到卫所类型的复杂性,为整体把握卫所的基本属性,虽然它已具备古代政区的基本属性,但把卫所称为“辖区”而不是“政区”更具有普遍意义。在卫所辖区内,不仅在明代卫所独立行使其管辖权,即便到了清代,卫所体系内的若干管辖权仍长期延续,卫所归并州县在清代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明代的卫所辖区及其管辖权的主要体现
卫所作为独立的辖区,一是表现为卫所在辖区内具有完全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管辖权,辖区内的治权与区外的行政系统并行存在;二是卫所管辖权与它的辖区大小并无直接关系,与是否独立成片、划界清晰没有必然联系。边疆实土卫所因连面成片,其政区性质会更明显,而内地卫所、沿海卫所等“非实土卫所”的辖区虽然以插花地、飞地等形式存在,但并不能否定其政区意义的存在。实际上,正是因为卫所具有类似于府州县的相应管辖权,它才被视为与之并列的独立系统。
卫所独立管辖一定的区域(屯田)。作为卫所存在的经济基础,屯田的独立性表现为卫所管辖权的独立,边疆实土卫所辖区的独立性自不待言,内地卫所不论它们的分布如何散乱错置,也都不影响屯地的官田性质和卫所对它的管辖权,即便到了明末依然如此。在华北,崇祯初年,浚县知县张肯堂称:“李自立,宁山卫军也,有地七顷……然而隶在卫者,不能去其籍也。”(《辞》卷5《李自立》)在中原,明末归德府(今河南商丘)侯方域称:“国初开设屯田,派坐甚远,幅员甚广。名隶本卫,地落他处,有相去数百里者,有相去数千里者。军产民产,相错其间。”(《壮悔堂文集》卷4《代司徒公屯田奏议》)。在西南,康熙《九溪卫志·凡例》有记,九溪卫屯田分布极广,“卫土非一隅,在慈利县图内者仅一卫城,其屯田一在澄州石门界,一在澄州图内,一在公安界,一在松滋界,一在越永定,在武陵界……”
虽然是插花分布,但卫所与相邻的府州县对辖区管辖权的划分很清晰。嘉靖《清苑县志·城池》说:“此县志也,何府治军卫亦志耶?盖府卫虽不可登于县志,然建设之所皆于清苑地焉,故志之。何书略耶?曰详在郡志矣,县志其纳,备参考焉,不敢悉惧其僭而赘也。”万历《定襄县志·田赋志》也记载了卫所和州县地近而不统属的关系,“按:屯地与民间相杂,其所从来靡可考辨,顾同一地耳。在民每石派粮一两,余屯则五钱,不啻损半犹然逋赋,何哉也?屯余自有丁差,业属本卫审编”。
明初卫所屯田的划拨原则,在内地拨给以无主地,不扰动原来的土地关系,在边地则以就近整块分配为主。明初设立卫所或州县以稳定局势为前提,内地不少地方是先设卫所再建州县,地方的行政权也由卫所官来兼理。如在颍州(今安徽阜阳),“(洪武元年)置颍州卫,命指挥佥事李胜守之。颍州自元季韩咬儿作乱,民多逃亡,城野空虚。上因如汴道,过其地,遂命胜筑城立卫,招辑流亡,民始复业”,就是由卫所官暂理民事(《明太祖实录》卷36〔下〕,洪武元年十一月)。在河南邓州,“守御前所千户所,治在州治东。明洪武三年命镇抚孔显兼知邓州事。六年,升正千户,颁印专理军务”(顺治《邓州志》卷9《创设志·所治》),同样是军政合并管理,军政官设置在先,行政官任命在后。明后期因田土归属已相对固定,中央再组成新的卫所,确实需要调整原来卫所和州县的辖境。在四川,明初叙南卫的屯田划拨与全国差不多,“凡武职一员皆有田。时当开创,各属腴田,听其自择,而卫有兵丁以备防御者,概发屯田”(嘉庆《宜宾县志》卷20《屯田志》)。但到万历初年新设建武守御千户所时,屯田及千户所的辖境就要“切割”附近的行政区(州县和卫所)了,“以九丝城都蛮作乱,巡抚都御史曾省吾勒兵讨定,割县属山都六乡,设建武所”(光绪《叙州府志》卷16《明周爻平蛮颂碑》)。建武守御千户所的辖区范围是,“府南四百二十里,东北至泸州卫九十里,东至永宁宣抚太平长官司八十里,西至珙县百五十里,南至镇雄府安静长官司八十里,北至长宁县百五十里……万历元年,剿平山都,水都震惧,悉归编户,拓地五百余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70《四川五》)。在这里,卫所的独立辖区和管辖权的划分明晰可见。
卫所对人口的独立管理。明代实行“配户当差”和“以籍定役”的人口管理和赋役制度,军、民、匠、灶等户类均世袭,其中军户的世袭性更突出。卫所军户专有黄册来管理,必要时再编“勾军册”,府州县户籍中要开列“州县军户”以别于普通民户。因不同的户籍承担不同的差役,他们的社会角色也不大相同,比如军户例不得分户,以保障军差的世袭轮替;户籍身份不同,就读的学校、参加科举考试的地点也可能不一样。现存极其丰富的明代科举档案(进士题名、碑录、登科录等),大都有户籍类型的清楚标注,军户的数量仅次于民户。此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影印出版的《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展示了数量庞大的明代世袭武官群体的官方档案,从中可见中央对卫所户籍管理的水平之高,军户拥有高度的独立性,而围绕军户的管理又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卫所经济管辖权的独立性。卫所屯地的官田性质,直到明朝灭亡都没有变化,虽然军田民佃或私下交易在明后期存在较为普遍,但买卖双方并无合法手续。卫所的仓储管理权虽然在明前期就交由附近的府州县代管,但卫仓服务卫所的功能定位并未有大的变动。明末,中央仍有明确规定:“卫所在省,则行文于布政司;在直隶,则行文于该府,一切应征钱粮,俱代为转行督催”(毕自严:《度支奏议·新饷司》卷10《覆凤阳卫所屯粮责成该府催解疏》),这里说的就是“代为转代督催”。当然,由于军政和行政两大系统互不统属,又要时常发生经济联系,必然会扯皮,军民经济纠纷屡见不鲜。例如宁山卫地处北直隶,屯田分散,管理权也多次调整,“直隶宁山卫虽设于山西泽州,其军余俱在河南屯住,请仍隶河南管屯官带管,岁纳子粒获嘉、滑县,以便放支”(《明宪宗实录》卷270,成化二十一年九月辛未)。这表明在卫所与府县不同的系统之间,州县渗透到卫所财务中的角色只是“带管”。
卫所司法权的独立性。卫所系统明初设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在中央,五军都督府下设有断事司,为正五品,专治五军刑狱。随着五军都督府的实际权力下降,断事官在建文时被裁。在地方,卫所的司法权长期存在,各卫所设有断事司专理刑狱,另常设有世袭武官担任的镇抚官,负责处理卫所内部的司法诉讼。如果军民之间发生了纠纷,两大系统间要协商处理,尤其是当军人侵犯了民户的利益时,不能交给府州县来审判,要经中央批准后,再委托专门的司法官处置(参见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线装书局2007年,第181~200页)。到明中期,随着权兼地方三司的巡抚、总督的派出,以及科道官体系的普遍建立,卫所与州县的司法权逐步合并,但主要是从上而下来调整卫所的司法权,卫所与府州县并行的局面并没有被打破,府州县必须得到授权,方可处理卫所的司法事务。明朝中后期,随着内地卫所与附近州县的社会交往日益加深,在军民杂处、高度融合的地方,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护与管理出现了军民合一的现象,这是两大管理体系长期并行的新变化(黄忠鑫:《明中后期浙江沿海“军图”初探》,《历史档案》2013年第1期)。例如明末浚县知县张肯堂在审判涉及卫所的案件时,仍然需要有相应的授权或委任才可处置,军、民的法律身份差异并没有完全消失。
卫所对行政事务的独立处置。古代,旌表是政府为表彰百姓在引领社会风气某方面的贡献所做的奖励,由各管理部门逐级审查,最终报中央审批,行政程序复杂。卫所具有行政管理的职能,在这一“民政”类事业中也在独立发挥作用。在边地的实土卫所,如辽东地区的旌表,均由卫所官奏报完成,嘉靖《辽东志》中有为数不少的旌表,均有“卫上其事,旌表其门”的记载(卷6《人物志·贞烈》)。在内地卫所,卫所官负责旌表事宜的记载也屡见不鲜,如武平卫(明属河南都司,治在今安徽亳州)右所副千户金源妻卢氏,“年二十三岁,夫亡。居丧循理,勤俭纺绩,守节无玷。景泰五年,本卫奏,表门闾”(成化《中都志》卷5《贞节》)。在广东,嘉靖《南雄府志·贞烈传》记有南雄千户李纯妻叶氏的事迹,“年六十余。十所军旗上其事,核实三次,未蒙旌表”(嘉靖《南雄府志》下卷《传·贞烈》)。到明代中后期,卫所中的儒学官员以及巡抚、巡按等官也参与卫所内的旌表事务。
明朝存在二百七十多年,随着时代的发展,明初的规定到中后期有了新的变化,卫所军政与州县民政两大系统也从彼此独立运行,到出现了统一的呼声和迹象,这一方面来自中央派出的巡抚、总督和科道官,他们的权力都可兼及军、民两大系统;另一方面是现实的需要,民政权力不断渗透到军事系统中。当然,直到明末民政也没有取代军政,军政系统的独立辖区和管辖权大部分还在。
综上,有明一代因为军、民两大管理系统的并存,各有各的组织架构,各有各的管辖权,形成了独立的辖区。在不设司府州县的边疆地区,卫所拥有高度独立的管辖权。在内地卫所、沿海卫所与府州县交叉错置的地区,实际形成了军政并存的“自然境”,比如“河南自然境”包括了河南布政司和河南都司的区域,山西“自然境”包括了山西布政司、山西都司和山西行都司的区域。明代的卫所与司府州县一样,具有“地理单位”的性质,只不过,司府州县是传统的典型政区,卫所则具备了行政区划的“必要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却不能以现代行政区划的概念或指标来衡量卫所管理体系,因为它是古代中国在边疆治理时带有明显的变通性、过渡性或灵活性的管理形态。鉴于明代边地卫所具有比较强的政区性质,而内地卫所同样拥有独立的管辖权却不可以现代政区的标准去衡量,所以可称卫所为“地理单位”,而从整体上严谨地表述明代卫所的管辖权属性,称卫所地理单位为“辖区”而不是“政区”更为恰当。
(作者:彭勇,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明代州县军户的制度设计与群体身份变迁研究”〔18BZS065〕的阶段性成果)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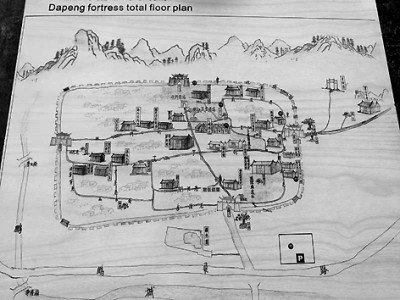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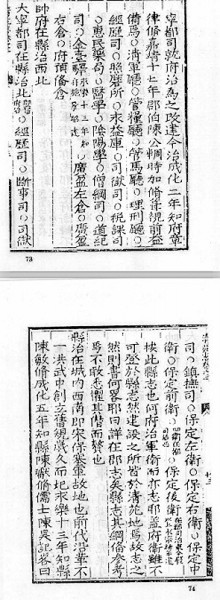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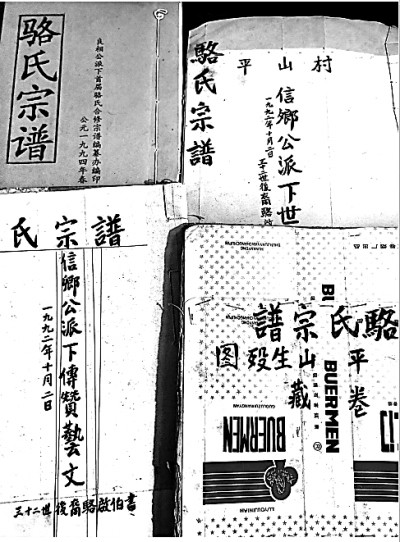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