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外文化交流史更加受到学界关注,各类著述不断涌现。张国刚教授的《中西文化关系通史》上下两卷,气势恢宏,是近年来关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成果。此书有以下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达通古今。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史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领域,从张星烺六卷本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到冯承钧对法国汉学界中西文化交通史名著的翻译,都为学术界积累了重要历史文献。方豪的《中西交通史》和沈福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意义重大,但在一些方面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各界新的需求。何芳川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下两卷是多位学者合作的结果,内容丰富,但因全书按照国家和地区来叙述,从而使整体历史感受到影响。近些年来,在各个断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均有精彩之作涌现,诸如刘迎胜的元蒙史研究、汤开建的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都成绩斐然,但以一人之力打通古今之作的通史性研究著作十分罕见,张国刚的这部作品是近些年来第一本。严耕望先生谈到治史时曾说,治史要“专精”与“博通”,这两条兼顾,对学者是很高的要求。而《中西文化关系通史》上卷“从张骞到郑和”、下卷“从利玛窦到马戛尔尼”,贯通古今,将专精与博通融为一体。该书实际是张国刚长期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一个系统总结。隋唐史研究,是他的学问起点,留德以后又致力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德国汉学史研究,成绩卓然。有了相关断代史的深入研究基础,再做通史研究自然能够做到通达。因此,该书是我国近年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值得关注。
第二,文明互鉴。本书选取“中国与西部世界交往和文化关系的相关史实”,构成自己的序列,不仅给中西文化关系史赋予了新的视角与内涵,而且凸显了对人类文明互鉴的关注与思考。在处理1500年以后中西文化交流史时,作者进行了化繁为简的安排。下卷尤为重视耶稣会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并以此为主线阐述文明的交流与对话,全书写到马戛尔尼来华为止。如此谋篇布局,既不与上卷章目如出一辙,更能凸显1500年前后中西文化交流的各自特点与重心。重点考察了耶稣会士如何进入中国,如何传教,如何描绘记录中国,如何影响欧洲认识中国,又是如何影响中国认识欧洲。耶稣会士不仅带来了中西的物质文明交流,而且也塑造着中西彼此眼中的形象。这种探索也关涉如何从整体看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问题。作者在序言中说:“19世纪是西方殖民主义向全球扩张的帝国主义阶段,像中国这种不曾如印度那样完全沦为殖民地的主权国家,也因为鸦片战争而被迫打开了国门,脚步沉重地迈向了近代;西学东渐日益强盛,以致出现西潮汹涌的另外一种单向流动的局面。”这是一个从长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作出的判断。笔者在10年前的大航海丛书序言中曾说,19世纪是西方人的世纪,晚清的败局刺激了每一个中国人,从此,“救亡图存”“变法维新”成为中国的两面旗帜。而要达到这两条,只有学习西方。如梁启超所说“参西法以救中国”,当“尽取西人之所学而学之”。毛泽东同志后来也描述过当时的情景,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只有学外国”。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东西方关系完全失衡了。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关头,人们似乎别无他路,这种局面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五四运动时期。从此,在东西方关系上,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似乎成为一种难以破除的二元对峙定式。
百年烟云,沧海一粟。回顾漫长的中西思想交流历程,我们应从整体上对中西关系做新的思考,或者说我们应将中国放入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考虑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发展问题。如果从文明互鉴的长时段历史来看,晚清只是弹指一挥间。而从张骞到马戛尔尼的这段文化交流历史方能更好地展示出文明的多彩、平等与包容。走出“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峙,在宏大历史进程中重新思考中国思想与文化的价值,是我们今天的重要任务。
(作者:张西平,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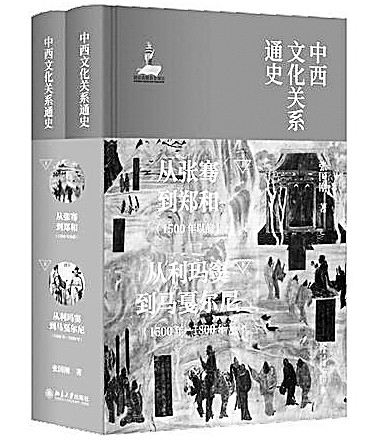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