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答问】
编者按
春节将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的“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一句“回家过年”,牵动着亿万中国人最温馨的情愫。然而近年来,一些年轻人却出现“怕回家过年”的心态。怕被催婚、怕被和别人比较、怕春节送礼不堪重负……各种有形无形的“怕”步步紧逼,令“春节社交恐惧症”随节日到来而升温。
“近乡情更怯”的现象折射出有关乡村治理现代化、乡村振兴的青年参与度等一系列问题。如何正视这种现象,并缩小城乡差距、弥合心理鸿沟?如何在日常的乡村治理中为青年留出可为空间,通过“两地情牵”驱逐“近乡情怯”?我们邀请专家为您解析、支招。
过年“有味、有为”,才能变“怕回乡”为盼回乡
光明智库:每到春节,很多离开乡村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感慨:脚下的回乡路不再艰辛,心理上的回乡路却并非“畅通无阻”。您认为,这些青年的忧和惧来自何处,怎样让他们的返乡之行温暖、安心、有意义?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桂华:
造成“近乡情更怯”的不只是个人原因,更是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这种变迁,既包括城乡关系变化,也包括生活在其中之人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人口大规模流向城市,市场吸纳农民进城,国家政策助推人口转移。城镇化改变了基层社会形态,“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社会逐渐远去,村庄社区从相对封闭不断走向开放。对于那些进城奋斗的年轻人,家乡从过去的生产生活统一体,变成了情感寄托的抽象体。
中国社会快速的生活变迁,以代际变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从50后到90后,每代人身上显现出不同的时代烙印。50后、60后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代进城农民,他们将城市看成“短期目标”,将乡村当作“长期目标”,进城务工是为了更好地返回家乡生活。从70后开始,进城农民逐步将城市当作落脚目标,将乡村看成歇脚之地。
几十年过去,城乡差距虽不断缩小,却依然存在。已经习惯城市便利生活的年轻人,对乡村生活多少会感到不适。更关键的在于体验的变化,最让年轻人失落的是乡村生活没有了过去的味道。过去的乡村生活是土里生长出来的,富有乡土气息。而今天,市场延伸到乡村的各个角落,乡村生活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但受限于经济条件,乡村市场所能提供的商品服务档次并不高,乡村越来越变成城市的“低配复制版”。“年味”淡化,返乡青年情绪无处抒发,乡情变乡愁。
与此同时,随着人口大流动、村庄空心化,乡村从熟人社会开始走向陌生人社会。过去过年是一项乡村公共活动,相互走动,互送祝福。如今的过年退缩为私人活动,交往局限于亲朋好友之间,谈的也总是婚姻、生育、工资等私人性话题,给人造成心理负担;过去的春节更重仪式性,现在则物化程度越来越高,过年总需要一大笔消费支出,给人造成物质负担。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进城青年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上离家乡越来越远。改变这种状况,关键是改变春节习俗,借着有意义的公共活动,让进城青年与乡村重新建立现实中与心理上的联系。
首要的是弘扬时代新风、推进移风易俗,防止春节过度物化,让过年变轻松。随着农民变得富裕,一些地区人情攀比的风气日盛,从腊月到正月,村庄到处摆酒席,农民一年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收入用于人情支出。还有一些地区,春节期间打牌成风,很容易演变为赌博活动。
进一步地,可以利用乡情搞乡建,让年过得更有意义。村庄公共事务要靠农民参与,春节是难得的村庄人口齐聚时段,村干部、党员可以利用春节将返乡人口组织起来,商议乡村发展方向,集聚乡村发展力量,推动乡村建设。返乡青年见多识广、思想超前,其中一些人创业成功、收入不错,他们有积极性为家乡作贡献。乡村基层组织应当珍惜并用好返乡青年参与乡村事务的热情,将其内心的乡情转化为乡村建设资源。
基层政府在这方面也可适当用力。可以拿出一部分乡村建设资金,支持当地村庄开展有价值的公共活动,如兴办乡村晚会、举办趣味比赛、组织村庄茶话会等,还可设置部分奖扶资金,用于村庄公共建设事务奖励与补助。资金量不在于大,关键是借此激励返乡青年,让他们返乡过春节时有途径参与到基层公共活动中,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出一份力。回乡有意义,自我价值得到彰显,乡村的春节才会过得“有味”,年轻人才会“返乡情更切”。
培植现代生活理念,弥合城乡观念鸿沟
光明智库:回乡过年,亲友往往关切询问结婚、工作、居住和生活条件等现实问题,让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倍感压力。您认为,如何才能避免关爱变成伤害,又该如何促进代际的理解和体谅?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原院长、文科讲席教授李小云:
离家,归家,回家过年承载着对于团聚的期盼。人们不论贫富都会带着礼物归乡,礼物把思念之情具体化,让人看到了实实在在的亲情友谊。回家过年的礼物馈赠和父母对子女完婚的热切期盼是人伦常情,反映了人类社会基本的道德规范和秩序原则。
然而,今天在外打拼的很多乡村青年却变成了“恐年族”。他们怕过年回乡,因为怕给红包不堪重负、怕父母亲朋催婚催生、怕在对比中丢自己与父母的脸。此类现象普遍存在,让回家过年这个传统文化重要民俗被商品化、功利化,节日的社会文化意义也被异化。这种异化一方面来自守土者和离土者观念与习惯的差异;另一方面折射出当今中国社会变迁导致的观念差距、心理震荡,是社会道德体系与物质发展之间不协调的呈现。
离开乡土的青年要对这种现象多一分理解。城乡差距、贫富差异是产生上述问题的深层原因。春节给亲人的红包薄厚往往超越了礼仪的意义,隐含了实际的需要。家里人普遍认为,城里生活好,能赚到钱,可以帮助家里解决困难,这是守土人对离土打拼者的预期。让亲人随时了解自己在外的日常生活,是降低预期的重要方式。信息化时代提供了便利的沟通手段,经常与家人发送微信、视频通话,告诉家人自己吃穿住用行等花销情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不切实际的预期。
而家人催婚其实并非只为催婚,实质上是传统社会亲情关怀的集中表达,是不擅口头表示关爱的父母所能找到的沟通话题。耐心交流、真诚讨论是对这种关怀最好的回应,难得回乡的游子应该和父母真诚讨论自己的婚嫁设想和实际困难,而非一味抵触与回避。
守土的亲友也需要理解,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面临着快节奏的巨大压力,城市生活需要很大开销,他们的收入除了养活自己,很难有很多剩余支持乡土家庭。城乡两个空间有着不同境况和不同观念,年轻人在外久了难免逐渐改变往日言行,这并非没有孝道、不重亲情。
年轻人不愿回乡也反映了农村精神文化工作的薄弱。农村基层文化生活往往更注重歌舞戏曲等活动,社会心理和道德文明建设成效有限。乡村振兴需要留住传统、补齐硬件和收入方面的短板,也要着力培植现代生活理念,弥合城乡道德观念和规范的鸿沟,这样才能真正留住年轻人的乡情。
未来乡村人口将由三类构成,青年离乡返乡都可推动乡村振兴
光明智库:解决“返乡情怯”,离不开乡村振兴。您认为,未来的乡村应该是什么样子?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有什么渠道反哺家乡?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将来我国也还会有三四亿人生活在农村。根据我国人口总量走势估算,如果达到人口高峰期时乡村人口为3亿左右,意味着城市化率将达到约80%,我国现有大部分建制镇,都有望发展为小型城市。
在经济规律作用下,未来乡村人口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专业农户。他们的总收入会与城市家庭相当,其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大致在30%~80%之间,其他收入来自农业产业链延伸环节以及非农业领域。二是农业产业链上的从业者。他们不直接经营农场牧场,主要活动在农业生产服务、农产品流通和加工领域。这两部分从业者会有一定交织重叠。三是住在乡村的非农户。他们有较高的非农业收入,可能也做一些农场工作,但住在乡村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谋求更高质量的生活。
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上述三类人群中的第一类,数量减少的程度会大于后两类。我国乡村振兴目标实现后,第一类人群会分散在小型居民点上,后两类则居住在大型居民点。那时,我国村庄数量会减少,大量农田退出耕作。但因为农业经济效率提高,我国的农产品供应会更有保障。所以,乡村振兴并不意味着乡村人口增加,其主要标志是农民收入增加、农业效率提高。
乡村可以存在一定比例的非农产业,并带来非农就业。但这种情形在总体上不会影响城市化率提高的基本趋势,因为大部分非农产业布局在城市更有效率。
出生和成长于乡村的青年,不论在哪里就业,都应该由自己作出选择,只要做到热爱生活、勤劳守信,就对社会有益。即使在城市工作、定居,也有益于家乡经济发展。家乡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耕地流转到专业农户手中,使农户平均经营规模增加,农业效率就会提高。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贡献。
吸引已经定居城市的青年回家乡发展需要具备足够条件。在现阶段开办家庭农场还存在市场环境尚未发育健全、进口农产品带来竞争压力等困难。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乡村发展的政策环境持续优化,以后农业经营的条件会越来越好,这一点值得期待。
换一个视角看,从农产品流通和农业生产服务环节进入农业经营风险较低,成本控制相对容易。青年可以从小规模经营入手,还可尝试兴办跨行政区的农业专业合作社,挖掘农业产业链价值。现代农业合作社还可采用公司化经营模式,有很大创新空间。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春雷、张云、王斯敏、蒋新军、康薇薇、马卉)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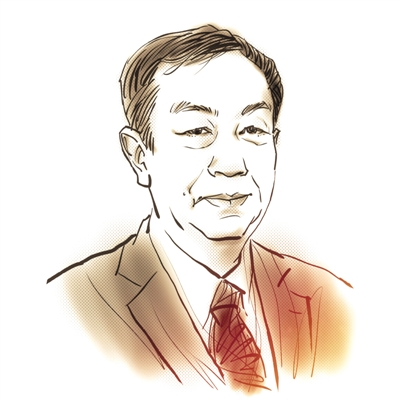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