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回归时我在天津组织、导演了澳门戏剧晚会,就是在他直接帮助下办成的。他知识渊博,热心澳门和内地戏剧交流工作,待人诚恳。他的逝世是澳门戏剧事业一大损失!”不久前,自我处得知澳门文化耆宿、戏剧大家穆凡中先生去世,耄耋之年的原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天津戏剧家协会前主席高长德同志,深情留下这样一段话。
穆凡中先生定居澳门近40年。家里都管他叫老爷,那派头,足!拄着文明棍,头发灰白眉角上挑双目炯炯,不见龙钟地溜达在狭挤忙碌的街巷间,京腔京韵唱上两口“非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再用山东味的粤语跟街坊问早安,穆老爷算是落地生根了。戛然而止,他铁定是抖着包袱儿哼着曲儿走的。人生如戏,被最好地诠释。
爷俩因笑结缘,我在澳门说过相声。穆老惊讶还有人到澳门说相声,我更不敢相信澳门还有人能懂行听出这是天津马氏相声的路子?就这样,跨越五千里,成为忘年交。近年他总是住院,我过境就停留静候或专程绕去澳门探望。他的女儿们说,爸爸视你如子,你给他带过太多的欢乐和安慰,每次和你见面他都回味绵长。穆老抬爱奖掖我,还不忘玩笑:“抱歉,我最小的女儿都当妈了,家里实在没有富余闺女了!”
“学的是工业民用建筑,干的是土木工程。”所有穆凡中先生出版的文学戏剧著作中,个人简介上来绝少不了这一句。看似不务正业的表白,我是业余我怕谁?实际上可比专业还专业。
那次住在利澳酒店,老爷遛早儿来“堵”我,邀我回家坐坐。32号巴士站在理工学院,他像位资深导游,和我说,劳您再随我多走两步。一座巨大的运动场映入眼帘。先生拿文明杖一指,双手拄上,冲那楼撇嘴:“这是我盖的,成名之作。”
1980年的澳门,远不如今日富丽堂皇,安定祥和,今人可能想象不出当年治安之杂乱,生存之艰难。澳葡政府征服小岛的“英雄”亚马勒的铜像,还屹立在葡京门前。那是澳门孩子最爱留影的地方,因为他们不知道骑马踏青苗的外国佬到底是谁,又曾经对澳门做过什么。
那时的穆老也就勉强称为老穆,来澳门“两眼一抹黑”。拉家带口第一难的是生存,以冶金建筑工程专长找到一份盖楼的工作,从入职就难掩他骨子里的直和呛。同时来做工的有三人。加拿大人月工资3000,上海人2100,为什么我1900?生活所亟,老穆还是低头干了,没想到不过多长时间,工程出了大问题,需延期交付。建设方要按合同罚到公司倾家荡产!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与我讲到此处,穆先生颇有冷对千夫指的气度,太多逆境中的韧劲,小眼神中不乏机智灵动,故弄玄虚地留下评书“驳口”,“我不仅没失业,工资一下子从1900涨到了8000!”
怎么会呢?“我给他们挑毛病!”他把自己关进小黑屋,戴上眼镜,俯在每一张没有中文的图纸上,研究每一个细节,很快,问题浮出水面。“体育场看台底下修的厕所,顶子是斜坡的,高个子人直不起腰;立体几何关系画错了,柱子四条线有一条和其他三条不在一个水平面上,修不了;观众席的高度,有些前后挡着,看不到全场……”老穆开连珠炮了,口吐莲花,建设方和外方代表脸色大变,赶忙拽住他:“兄弟,请到我办公室里面谈吧!”
老穆从地盘上的工程师,西服革履登堂入室,使老板逃过一劫,成了公司的中流砥柱,为中国人争了光。澳门建筑界都认识他了。说起这段往事,先生感慨万千,以京剧手眼身法步,用笑料十足的口风神完气足述说着,嘎、犟、智、勇,在他眉宇间,我读出很多。
很多人机缘巧合背井离乡来此,建设澳门,不忘心怀祖国,他们爱祖国,爱澳门,并把这份浓情传承给下一代,下下一代,打破文化藩篱,用故乡与家乡的艺韵在沙漠中躬耕滋养出一块又一块绿洲。以澳门人守望相助救亡图存为题材的首部本土原创京剧,就编自穆先生女儿之手,唱进了中国国家大剧院。
穆老爷的文字,如果你和他交谈过,一定要结合他的谈笑风生来读,准是忍俊不禁的!说到戏剧,“这个新的尾声,太直白,没有韵味,这就等于把《樱桃园》的底给刨了!”“底”是相声术语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结尾的意思,而“刨”是提前泄劲暴露,使“包袱皮”没卷好,最后“底”“抖不响”。
秉持盖楼时的执着钻研,穆先生哼唱北国的京剧,竟成为粤曲粤剧乃至澳门华文戏剧的行家。他关心大事,又最在意小传统,把恢复京剧等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世代相传的小传统,作为维系发展中华民族大传统的支柱来看,并为此躬身搦管,鼓与呼,在南国这中西合璧的小城,此等文化胸襟显得格外开阔,也让历史悠久的澳门富有不竭驱动力,焕发出文艺之光,耀过那华灯初上的纸醉金迷。
我与很多在津的艺友戏骨,竟通过澳门相识,或因同穆老爷这份奇缘而更亲密。一座繁华精致小城,曾经是戏剧研究的不毛之地,因他努力让澳门戏剧走出去、带回来,被世人所知。他总爱签名“澳门穆凡中”。我笑,您喝了亚婆井的水,也让亚婆井的水更好喝,濠江自此有了一泓戏泉。
“诗书非药能治俗,道德无根可树人”。这是悬挂在穆老书房迎门的一幅字。每知我去,他都提前好几天兴奋得招呼家里人准备,打扮精神,踩着锣鼓点,蹦登仓亮相召见我,聊起在整个澳门似乎只有我俩喜欢的戏和相声。老两口总是送我到巴士站,相望十字路口,隔着繁忙的高士德大马路,彼此挥手,久久不愿离去。
想起陪穆老和我爹在富华酒店一起饮茶聊天,时光再难回。
这些文字是我深夜陪床时蜷在病房楼道昏暗灯光下写就的。我父亲因复发中风住院整整180天了,言语、进食、肢体功能均出现障碍。穆老走时,正是父亲入院100天,我恨分身乏术难去送行。在最后的一段时间,穆老几乎每日都发来信息关切问候,他最后留给我一句话是“皇天不负有心人”。
父亲发病那天,我准备去澳门并约好去家中探望穆老,已行至拱北口岸,闻讯实时折身赶回津,竟与先生擦肩成永别。澳门是父亲唯一出境坐飞机头等舱去过的地方,穆老是他在澳门唯一不舍的好朋友。爸爸从来都放心我去澳门,他切身感受到澳门有太多像穆凡中先生一样普通而不平凡的同胞满怀拳拳家国情。爸爸对澳门念念不忘,除了对老朋友情谊难舍,正是期待这里更多元、更灿烂、更完美地助力共同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我告诉病榻上的爸爸,穆老走了,重病中他格外伤心大哭,我也泣不成声。
当晚,我不禁发出一条独白:再过拱北,我去看谁?没想到,澳门各位朋友看了,纷纷“保持队形”留言回复:我、我们……迢迢两地,燕云吴树,梦魂不惮濠江远。祈福父亲,祝福澳门,怀念远方的穆凡中先生。
(作者:刘利祥,本文系“中国梦·家国情”作品征集二等奖作品)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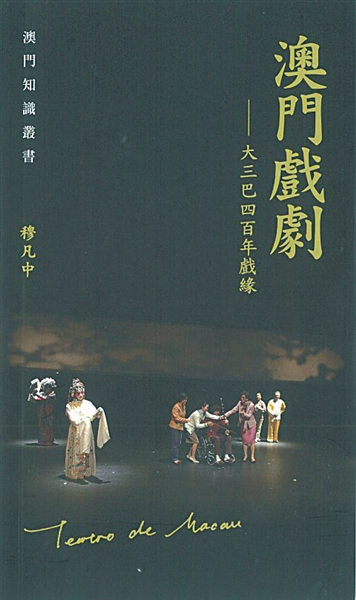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