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纪念路遥诞辰7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上,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钱远刚深情说道,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缅怀追思路遥,是为了弘扬陕西优良的文学传统,建构陕西文学的精神谱系,重申文学的现实主义正途及时代使命。
在路遥心中,延川县就是他的故乡和故土。他曾说:“我是在延川长大的,在延川成长起来的。所以对延川的感情最深。”作为《山花》杂志创始人之一,路遥非常认同《山花》对他的作用。在《山花》创刊10周年之际,路遥写下《十年》抒发他的感情:“艺术用它巨大的魅力转变了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我深深感谢亲爱的《山花》……如同一封家书,每一个字都是亲切的,让我感之不尽,思之不尽……”
深沉的情感离不开过往的经历。《山花》创刊之初的几年,以文学名义发行的报刊并不多,即使是一些报纸的文艺副刊,或者一些仍然以文艺为名的刊物,也多以标语或口号式作品为主。“但在延川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却冒出了《山花》,不得不让人震惊!”著名作家、陕西省文联原主席李若冰如此感慨。
虽然是县级文艺小报,但《山花》却是当地重要的“文学苗圃”,先后培养了三代20多位作家,延川也成了名副其实的“作家县”——从创办者、诗人曹谷溪,到蜚声中外的作家路遥,再到知青作家史铁生、陶正,还有更多后起之秀,如闻频、海波、远村等,他们活跃在中国文坛,被称为“山花作家群”。对于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县城来说,这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1.破土于早春寒月的精神食粮
当时的陕北,如同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写到的,“春天的道路依然充满泥泞”。这也是《山花》诞生的背景。
“山花”是陕北地区山丹丹花的别称。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一群因为热爱而不知惧怕的文学青年,在黄河畔的山沟里,创办了一份油印的文学小报。这些元气淋漓的陕北后生,在黄土高原粗犷奔放性格的生养下,始终抱着“与命运抗争、把光景过好”的人生信念。他们用全部创作热情和生命激情,浇灌着这颗文学种子,使之生根发芽,绽放开来。
20世纪70年代,清华附中的学生陶正,偷偷带着油印机来到延川插队,在当地一个小山村里办起了报纸。这张小报不仅探讨了中国的农民问题,还摘编了俄罗斯民歌等文学内容,这引起了时任延川县通讯组组长曹谷溪的注意。
一直以来,曹谷溪就和县里的“文人”交往甚多,见到陶正后,更是被小伙子身上的激情、坦率以及远大抱负所震动。曹谷溪心想,北京知青敢背着油印机在陕北农村办报纸,为什么我们不敢?
当时,一本《延安儿女热爱毛主席》的诗集引起了曹谷溪的注意,“咱们也编本诗集,也干它一场”。于是,曹谷溪、白军民、闻频、陶正、路遥等人合编了一本诗集,并印成油印小册子,此诗集后改名为《延安山花》,开始内部发行。
在延川县领导的支持下,曹谷溪、路遥一班人将诗集《延安山花》扩编为16开4版、铅字印刷的活页县级文艺小报,并更名为《山花》正式出版。第一期便发表了编辑路遥的诗歌《我老汉走着就想跑》。曹谷溪介绍,路遥起初发表作品时,还很幼稚,曹谷溪告诉他:“你能超过我。”路遥最初的诗歌均刊于《山花》,他的叙事诗《桦树皮书包》、短篇小说《伏胜红旗》《基石》等,也同样首先在《山花》上刊发后才引起外界的注意,并被选入省级文艺刊物。史铁生在路遥逝世后撰文回忆道:“后来我在《山花》见了他(路遥)的作品,暗自赞叹……我从小喜欢诗、文,便十分羡慕他。”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谈到《平凡的世界》时说:“我和路遥很熟,当年住过一个窑洞。路遥和谷溪办《山花》的时候,还只写诗歌,不写小说。”
在当时,这一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陕西日报》刊出调查报告《“山花”是怎样开的?——诗集〈延安山花〉诞生记》,点名表扬了返乡知识青年路遥:“城关公社刘家圪崂大队创作员王路遥同志,一年中创作诗歌五十余首,其中有六首在报刊上发表。据不完全统计,全县一年来共创作诗歌两千余首。这些革命诗歌,运用黑板报、墙头诗、诗传单、唱秧歌、朗诵会等各种形式直接与广大群众见面,有力地配合了革命运动。”
“《山花》虽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但却是延川这块文学厚土上长期积蓄的文学情绪的总爆发,是‘伟大的革命理想’与陕北人先天具有的浪漫主义品格相结合的产物。”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梁向阳表示,《山花》的旋律是“信天游”的,这里的青年正是通过“信天游”的方式来抒志咏怀,表现“崇高的革命理想”。曹谷溪曾说:“《山花》绽开在整个中国大地百花凋零的早春寒月。”
2.世上还有一种叫写作的“营生”
在那个年代,年轻人既不能经商,也不能外出打工,《山花》的出现让延川青年知道了世上还有一种叫写作的“营生”。
时为中学教师的闻频,是西北大学的毕业生。在延川,文化程度算是佼佼者。后来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自己的第一首诗《大娘的话》,就是创办初期曹谷溪交代的“任务”。作品经《山花》发表后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集收录,又被编入上海市中学语文课本。闻频说:“今天看来,它毕竟是时代的产物,但对一个身居陕北偏远山区的年轻人来说,其振奋和鼓舞可想而知。”
闻名乡里的“伞头”(秧歌队领头)海波,13岁辍学,与路遥是儿时密友、小学同学,也是《山花》创办者之一白军民的学生,当他拿着自己的第一首秧歌词递到《山花》时,曹谷溪不敢轻易接纳。怎么办?改!“业余作者水平差,有些作品都是编辑硬改出来的。”一次,曹谷溪在公开场合讲道,现在被公认为最有希望的文学青年海波,当时水平差得可怜,在《山花》上发表的第一首诗歌几乎就是几个编辑“做”出来的,“尽管这样,但我们很高兴。”
海波说,《山花》通过这些事例为农村青年指出一条路:努力创作,前途无量。后来海波成了延川的名人,一时间一大批青年作者蜂拥而至。
诗人觅程是“山花作家群”中的一员,他曾是延川贺家湾公社刘家河村一个非常贫困的青年农民,写诗没有稿纸,就在过时的日历背面写,时间一长,他将写诗的日历揉成了一个个纸球。曹谷溪从这些纸球中抄出了他慷慨激昂的诗句,经仔细修改,发表在《山花》上。激动不已的觅程也由此坚定地走上了文学道路。
《山花》编委在《山花》第一册合订本所作的说明中指出,“这一朵小小的花儿,生在人民群众的土壤里,淋沐着党的雨露阳光,正像她年轻的园丁一样,充满了生机,充满了希望。”这正构成了后来《山花》刊发之作品的基本特征。“相较于彼时同类诗作的口号、标语性质,《山花》所收作品因吸收陕北民歌的表达方式,而有较多生活气息,且不乏艺术的韵味。”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杨辉看来,《山花》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影响,除呼应时代潮流的显在原因外,始终扎根泥土是其根本所在。
史铁生中篇小说《插队的故事》,通过如歌的叙述,追忆了他当年在延川插队的故事,荣获全国中篇小说奖;陶正的关于陕北插队题材的《女子们》系列中篇小说、本地作家海波的中篇小说《农民儿子》同样获得好评;曾经的“县中队战士”荆竹成为宁夏地区重要的文艺评论人才;诗人闻频诗歌频频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亮相;而当年《山花》的发起者与组织者诗人曹谷溪,不仅推出了诗集力作《我的陕北》,而且其报告文学《陕北父老》也走向全国;散文作家史小溪、浏阳河的散文作品也把浓郁的陕北气息带到全国。
《山花》越办越火,县邮电所发现,《山花》编辑部成了全县往来信函最多的客户。据统计,《山花》累计发行达到28.8万册,连香港三联书店也有印刷发行记录。
贾平凹曾称,他第一次看到朋友和谷在《山花》上发表了处女作,“还很是嫉妒了一阵子”。路遥后来回忆道:“今天国内许多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当年都在这张小报上发表过他们最初的作品,有的甚至是处女作。一时间,我们所在的陕北延川县文艺创作为全国所瞩目,几乎成了个‘典型’。”
3.黄土高原迎来了一批北京知青
《山花》能够长开不败,绝非偶然。20世纪70年代,2000多名北京知青来到延川插队,他们带来的城市文化,给黄土地注入了一种新的文化因子,也再次点燃了延川人的文艺激情。
“来自北京的知青在这块黄土地里找到了与北京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真切地感受到了黄土高原上浸润着的人情味儿,以及这种生存方式中所潜在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李震告诉记者,这些本该在城市或者校园里开放的文学之花,纷纷在乡野里绽放了。他们或作为《山花》的编者,或作为《山花》的作者,或作为《山花》的读者。而北京知青的到来,也给当地的回乡知青带来了黄土地之外的文化气息,带来了城市青年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人生理想的新的参照系。
“陕北不大产虚伪,虚伪之作算不得真正的文学。我的文学创作的起点,应该是在陕北延川县清平川的一个小山庄里。”陶正在回忆中谈到,来到延川县插队时,他肩上扛着油印机,背上背着蜡版,农闲时间,就忙着写诗抒情,宣传革命理想。“我们自己编辑、自己刻版、自己插图、自己油印,也把自己的作品塞进去,辛苦而快乐,热情而狂妄。”陶正当时最有名的诗歌,便是与著名作家高红十合作的长诗《理想之歌》。
著名诗人梅绍静,当年是延安无线电厂的工人,她当年投给《山花》的第一首诗,被曹谷溪修改得只剩下几句原诗。她的第一本诗集——信天游体诗歌《兰珍子》由曹谷溪推荐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曹谷溪看来:“通过办《山花》我认识到对新人的扶持是最有意义的工作。”梅绍静逐渐崭露头角,诗集《她就是那个梅》获全国第三届优秀新诗集奖,《唢呐声声》《只有山风才为玉米叶子歌唱》等一大批作品以现代人的感知方式和诗性的言说方式,刷新了李季、贺敬之等老一代诗人的信天游体写作传统,在80年代诗坛形成广泛影响。
而延川当地的文学青年路遥也在长期求索与迷惘之时,在北京知青身上领略一种新的东西。据海波介绍,路遥不止一次提醒他,“要多和北京知青接触,这些人看问题准,表达能力强,像用手指捅窗户纸,一下一个窟窿。”闻频在回忆文章中说,“路遥平时话不多,不爱与人交往。但他爱和北京知青交往,可以说,是这帮知青打开了这个陕北后生的思路,把他的视野从这片黄土高坡,导向全国,导向世界,导向了社会的高层次。”
《山花》后任主编曹建标回忆,当时给《山花》投稿的作者远不止延川县境内的知青,还有更多延安、陕西乃至全国的作家,其中有多位后来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和诗人。“我发表处女作的《山花》正是它最火的时候。‘创作组’已经是延川县特有的一个文化单位。后来我翻看这一时期的《山花》稿件档案,随便写几个曾给《山花》投稿的作家名字,就足以让人肃然起敬:贾平凹、梅绍静、叶延滨、蔡其矫、史铁生等人。”曹建标说。
除了创作成绩最为典型的路遥,陶正凭借短篇小说《逍遥之乐》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史铁生以插队题材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连续两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3年全国获奖的20位作者中,竟有两位曾是延川插队的知青。”梁向阳说,“他们把延川视为‘第二故乡’。”
“尽管十分简陋,也没有公开的发行证号,但《山花》的文学身份以及它对来自北京和当地的两股文学青年的聚合意义,使它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标识。”在李震看来,“山花群”虽然生活在山沟里,却在心里呐喊着,“我是生命,我是艺术”,他们中的优秀者,几乎都有一段带血的生活体验。
4.“山花作家群”的“效应魅力”
“延川的几代《山花》作者,都是把根须深扎在大地之上的理想拥有者,他们讲述百姓身边的故事,反映群众的喜怒哀乐,用接了地气的、沾满露珠的鲜活作品建构了一个个意趣盎然的艺术世界。”梁向阳表示,像路遥这位从《山花》上扎根成苗的作者,就格外懂得珍惜这种传统。
路遥在“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上致辞:“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大众的精神需要……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这也正是“山花作家群”的共同心声。
几年前,从教师岗调到《山花》杂志社工作的高君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她告诉记者,《山花》在当地的影响力以及内容的贴近性,让每次出刊都成了“洛阳纸贵”,除了面向全国各大文学期刊、大专院校、图书馆的赠阅外,“几千册分发下去,往往‘一书难求’。”高君琴说,她的微信朋友圈曾盛传一张照片,一名清洁工人休息时,坐在路边认真阅读《山花》。
在河北开过书店,在北京当过“北漂”的高进,现在虽然在加油站工作,但心里更想“安静的写作”。当自己的诗歌在《山花》上发表,他捧着那本自带墨香的《山花》看了整整一个下午,“只有看到自己的诗刊发出来,那一刻才知道自己是那么需要被认可。”高进说。
“人民的刊物人民办,人民办的刊物人民看。《山花》一直在践行这样一个理念。”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白烨认为,《山花》给其他地方性文学期刊树立了榜样,“《山花》葆有文学的初心,它为文学爱好者搭建平台,抒发声音。文学以本身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将热爱它的人们团结成一个整体。”《山花》杂志社社长张北雄介绍道,杂志中“山花烂漫”的栏目主要就是发掘当地作者的原创板块,现在已经形成以延川为主的50多人创作团队,“有村干部、老师,也有务工者、农民,不少娃娃都非常有才气”。第二代、第三代作家群分别在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登上文坛。诗人远村被评为“全国十佳诗人”;倪泓的小说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经过近50年风雨历程,《山花》现在是一本县级文艺双月刊,继续承担着培育文艺新苗的作用。“山花作家群”的成功,对当地文化也产生了带动效应。
“延川山花”现象由文学辐射到整个文学艺术层面,涌现出一大批美术、摄影、戏剧以及民间艺术等方面的优秀人才。20世纪80年代初,延川的民间艺术家冯山云,通过自己的潜心整理,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民间艺术“布堆画”,把民间广为流传的布头剪贴的装饰品,送上了艺术的大雅之堂;民间剪纸家高凤莲独树一帜的民间剪纸,饮誉海内外,她也成为文化部命名的“剪纸艺术大师”;摄影家黑明,创作出记录北京知青在延生活的纪实摄影集《走过青春》,引起轰动;二曹的喜剧小品,通过象征、变形的手法,表现陕北人的生存状态等,引起很大反响。
“文艺激励人心的作用愈发突显,我们既要重视国家层面的宏大文艺,也要重视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群众文艺。‘延川山花’这种接了地气、心向天空的文艺现象,确实给时代提供了诸多启示。”梁向阳说。
“‘山花现象’就是作家扎根人民,从人民中汲取力量的例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说,“对于人民的信念,对于我们土地的信念,深深地扎根在这代人身上。他们一方面是心怀世界的,饱含着对世界、对人类的整体性关怀和责任。同时,他们也是有根的,他们的根深深地扎在中国的土地和父老乡亲们身上,片刻不忘对祖国、对人民、对父老乡亲的责任。”
(本报记者 崔兴毅 肖人夫)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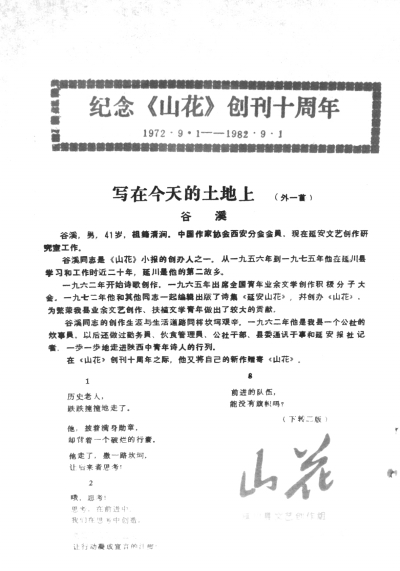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