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谢华良的儿童题材长篇小说《陈土豆的红灯笼》里,“红灯笼”是故事最后时刻才出现的意象,它是小说的“文眼”,是全篇故事收束时闪现的亮点。“雪天红灯笼”也是小说主题的形象浓缩。这也是作者谢华良创作上追求美好结局的“高潮”。整部小说的核心人物是陈土豆,显眼的意象却是一头叫“陈毛驴”的牲灵。这头毛驴从头至尾在小说中“活动”着,它是串接小说故事的线索,也是让人物往来冲突并最终实现和谐的主要元素。小说以“红灯笼”而不是那头“陈毛驴”为题旨,正是作者创作意图的一种刻意表达。
这是一部以“善”为故事底色,以“善”为人物性格共同点,以“善”为题旨的小说。这样一种创作想法很单纯也很美好,但要通过有效的故事、可读的文字实现并非易事。小说这样开始了故事并逐步推进:乡村里的留守儿童陈土豆,看到本家长辈“三楞爷”抽打一头毛驴,进而心生怜悯,又进而“意外”成了这头牲灵的“主人”。自从得到这一牲灵的“抚养权”之后,展开的却是一个接一个和陈土豆一样、有着善良内心的人物形象和他们之间发生的种种故事,这些故事有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这些冲突又通常因互相之间的误会产生,误会与冲突最终都能被消除,达到平和。小说写得如此美好,如此单纯,这也为小说故事的展开带来了格外的难度,即依靠人物一味的善良和情节单纯的美好,如何保持小说故事的起伏,如何打开事实上并非单色的心灵世界,如何保持小说的有效推进和阅读上的引人入胜,显然谢华良在构思上颇用心思。在总体上追求表达善良与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读到了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故事应当具有的复杂性。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复杂性并不只是为了保证小说故事的长度而设置的噱头。人性的复杂,时代的影子,都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呈现。15岁的陈土豆是一个留守少年,他的父母带着更小的妹妹陈小鱼进城打工,陈土豆于是以较小的年龄扛起一个“家”的名分。陈土豆的母亲后来带着陈小鱼回到乡村,父亲却因为躲债而不得归。本来是一个人过着艰苦生活的陈土豆家里,迎来的不是温馨,而是一拨又一拨来讨工钱的人们,这些人还多是亲友和乡邻。平静的生活无法继续,陈土豆的母亲只身一人又回到城里去了,陈土豆和他的妹妹继续留守乡村。这样的设置不但让故事变得复杂,更让故事背后透着现时代的生活影像。
小说的另外一条线索,围绕着少年陈土豆与本家的“三楞爷”、本乡的张豆腐之间的交往展开。如果说小小年纪的陈土豆与年长的陈三楞之间的冲突,还多是以误会的形式“戏剧性”地呈现,陈三楞与女婿张豆腐之间的争斗就多了几许真实的“火药味”,他们大打出手甚至到了动用官司的地步。这样的故事要拼接到一部以儿童生活为主的小说中并非易事。“陈毛驴”的贯穿就发挥了很有效的作用。小说借用一头牲灵的归属权不断转换,将互不搭界的人物粘连到一起,变成一个整体,展开了一幅具有真实性和立体感的当代乡村生活图景。小说还穿插了另一条颇具温馨色彩的线索,即张豆腐的女儿春妮与陈土豆之间的特殊情谊,陈土豆与妹妹陈小鱼之间的真挚感情,又通过对陈小鱼学业成长的描写,把这三个少儿,写成了一种亲切温暖的关系。小说在处理陈土豆与张春妮的关系时,既暗示了一种朦胧爱意,又坚持不让其相处越出友情的“红线”,分寸拿捏得可谓恰切。到最后,陈土豆的父母回到了乡村,一家人过上了难得的团圆生活。本来渐入正常的生活,因父亲陈水库的病痛预示着还将迎来不少艰难。然而,人性的善良,亲情、友情、乡情的浓郁,就在这样既纷繁又单纯的故事交织中得到充实表达。
作为一部儿童文学类长篇小说,《陈土豆的红灯笼》注重乡土气息的营造,从环境到意象,从人物名字到故事情节,“六畜兴旺”的味道颇有谐趣。小说设置了适当的背景,以体现故事环境并非世外桃源,而是实实在在的当代生活。小说把兄妹情、同学情、母子情、邻里情作为主色调,也加入了生活并不处处如意的复杂性。作者的用意显而易见,且也达到了创作的初衷。当然,如果作品在突出善即为美这一主题时,能够更加紧贴生活的土壤,表现出更具启示性的内容,能够把生活中的复杂和人生的不易与善的主题,在更深更广的境界中展现出来,那应该会使小说的力道更有强度。
(作者:阎晶明,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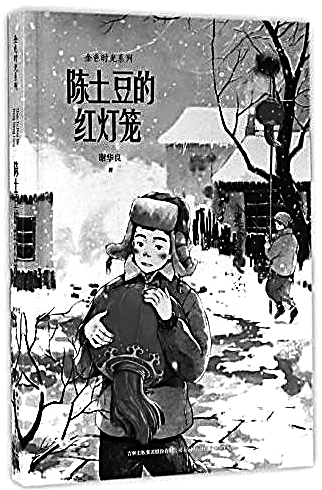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