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胜迅速翻开新书朴素的牛皮纸封面,映入眼帘的书籍第一页印有各式彩色古典图案,说不清是中是西。“这就像鲁迅,外表看起来是一个严肃的先生,其实他的内心是绚丽的。”
作为《鲁迅编印版画全集》的装帧设计师,张胜与鲁迅生前收藏及编印的版画打了五六年交道。编辑和设计过程经历过多次推倒、重来、修改,这让他对鲁迅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不久前,北京鲁迅博物馆主编的《鲁迅编印版画全集》由译林出版社正式出版,共收录了889幅鲁迅收藏的版画,除鲁迅生前出版过的作品外,还有一些他已编好却因故未能出版的,可以说是目前较全的鲁迅编印版画集。
“鲁迅既有严父般的威严,也有慈母般的爱心。”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说,编印这套书是为了给中国现代版画史留下一批材料,为鲁迅先生的艺术收藏体系作一个证明,让读者看到一个形象更为丰满的鲁迅。
1.一场跨越90年的出版接力
从1929年到2019年,这是一场整整跨越90年的出版接力。起跑者不是“文学家鲁迅”,而是被称为“中国新兴版画之父”的鲁迅。
1929年,一本名为《艺苑朝华》的艺术丛刊问世,拉开了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帷幕,丛刊由鲁迅倡导成立的美术团体朝花社出版。此后的8年中,他陆续编印出版了《引玉集》《苏联版画集》等10余种版画集,他为每一集写小引、设计封面,甚至自费出版。黄乔生说:“鲁迅当时编印这些版画集,是赶紧做、立刻办。”
然而,这也是鲁迅一项未竟的事业。
除了书籍,鲁迅最大宗的收藏品就是版画。鲁迅一生收集了中外版画超4000幅,其中外国版画2000多幅,涉及16个国家的300多位版画家。目前,这些鲁迅版画主要收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
1936年10月17日鲁迅生命中最后一次会客时,他赠送友人两本杂志及两本书,书名叫《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交谈中,他提到中国木刻艺术“进步很快,超过了我的预期,不过,缺点还不少。”两天后,鲁迅病逝,他的版画出版计划也戛然而止,留下几本刚编订好的版画集,成了后人口中的“因故未能出版”。
接过鲁迅版画出版接力棒者并不多,远不能与鲁迅文学作品出版相比。
2014年,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过《鲁迅藏外国版画全集》,2017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鲁迅编辑版画丛刊》,这些出版物都以鲁迅的收藏为基础,选取一部分进行出版。
“80多年后,摩挲着这些形态各异、古色古香的图册,我们仍能感受到鲁迅心灵的脉动。”黄乔生介绍,《鲁迅编印版画全集》中的原版原作鲁迅博物馆均有收藏,全集侧重还原鲁迅原初的编印思路,这套书一共12册,收录了鲁迅编印的中外版画集,除他生前已编印的画册之外,还最新编印了《拈花集》和《城与年》等他生前未及出版的画册。
跨越90年的出版,接力的不只是书籍,还有鲁迅传播艺术的精神,这精神是鲁迅自费出版《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时,写在扉页上的那句话——“有人翻印,功德无量”。
2.一个鲁迅研究者的丰富宝库
2001年第一次在鲁博看到鲁迅的版画收藏时,天津美术学院教师王顷内心“震动极大”,在他的印象里,鲁迅原是课本里那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老先生。“我惊诧鲁迅怎么会有这样的眼界和这么多的藏品,比照之前我印象中的鲁迅先生,这些版画所流露出的意趣,判若两人。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鲁迅在买西方当代艺术。”
在鲁迅丰富的版画藏品中,有富有力之美的德国版画、反映十月革命的苏联木刻、独特的日本浮世绘版画、风格秀丽的英国木刻。鲁迅对版画收藏付诸了极大的热情,他曾经委托在德国留学的徐梵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等朋友帮他购藏德国、比利时、苏联等国家的版画。
今天再看鲁迅收藏,学者们认为,鲁迅的美学思想就体现在他的版画理论中:
“青年木刻家刻人物就不如刻静物,往往把中国人的脸刻得像外国人。”
“精力弥满的作家和观者,才会生出‘力’的艺术来。”
“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
近年来,鲁迅研究界开始注意到鲁迅的美术世界是一个丰富的宝库。黄乔生说,过去我们只注意鲁迅的文字世界了,现在应该把鲁迅的美术世界和文字世界互相印证起来。
鲁迅为何对版画收藏、传播付诸如此热情?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认为,鲁迅在30年代勉力复兴中国版画,提倡新兴木刻,是基于木刻艺术的观赏性、普及性和战斗性;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孙郁说,鲁迅主张一要择取中国遗产,融合新机,使现代创作别开生面,一要引进外国作品,供青年美术工作者参考,使本土创作更加丰满,两翼并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董炳月则认为,鲁迅等一代英杰“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鲁迅的版画收藏为我们重新理解鲁迅的现代性提供了一个参照。
“鲁迅在美术上的影响首推版画。”黄乔生说,鲁迅的藏品非常多,鲁博现在还在做整理工作。鲁博的鲁迅生平展本来有两层,今后想拿出一层展示鲁迅的艺术世界。鲁迅还收藏有数千张汉画像拓片,下一步,鲁博还要联系专家学者,把鲁迅的整个美术世界介绍给人们。
3.一次对鲁迅“较真精神”的学习
《鲁迅编印版画全集》出版发布的那几天,黄乔生的心情有些复杂,是激动兴奋中又有些惭愧。“鲁迅用几年的工夫编印了十几种,我们这套书搞了五六年才出来,比起鲁迅的精神,有点落伍,感到惭愧。”
“千万不要把我们做的工作讲得太完美。”张胜与黄乔生有着一样的心情,说到这个的时候,他的神情从谦逊转为认真,“实在是因为,作为一个出版者,我们较真的精神与鲁迅差很远。”
鲁迅在编印版画上花费了极大精力,八年中,他联系印刷、托人装订,请人作序,甚至自费出版。翻译家黄源曾回忆,一个酷热的下午,他看见鲁迅“穿了一身短衫裤,正弯着腰折叠珂勒惠支版画选集”。
编书过程中,张胜按照鲁迅生前未及出版的《拈花集》与《城与年》所开目录,重新拍摄了鲁博的版画藏品,《小说士敏土之图》《你的姊妹》等则是从30年代的原版图书上扫描而来。这样反复打磨五六年,张胜却对自己的努力不甚满意,“如果每一张画都找到原版来拍摄,效果一定更好,这是我看到的却没有做到的,我们未用尽全力做到完美。”
“鲁迅1934年编辑了一本《引玉集》,今天我们推出这套书的意义还是‘引玉’。”张胜以是否推动了进步作为自己工作价值的判断标准,他认为,整理编印鲁迅的文化遗存,只是做到了保存。而鲁迅不只是文化遗产的保存者,更重要的是开拓者、建设者,“希望有2019这个年代的‘鲁迅’,把2019年代世界上最先锋的‘珂勒惠支’们,介绍给美术界。”
(本报记者 陈雪)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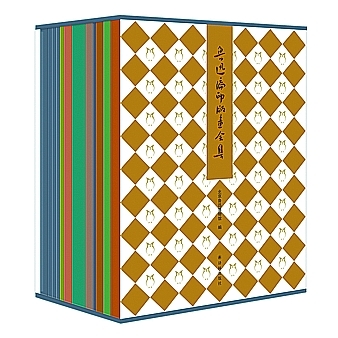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