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
韩国当代文学中的父亲与母亲形象,常常具有特定的指涉,在很多时候,父亲象征着半岛的国族史,而母亲则象征着半岛的受难史。不过,进入21世纪后,在韩国政治渐趋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个人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了两万美元的同时,年轻人逐渐产生出对个人的强烈渴望,以及与“国家民族”“父亲母亲”为代表的前现代共同体切割的欲望。
1.《妈妈,你在哪里?》
1963年生的申京淑在1985年以中篇小说《冬季寓言》崭露头角后,以199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风琴声起的地方》在韩国文坛稳站了脚步,此后几年,她陆续囊括了在韩国具有崇高地位的东仁文学奖、李箱文学奖,更在2012年以长篇小说《妈妈,你在哪里?》再下一城,荣获英士曼亚洲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女作家。
实际上,《妈妈,你在哪里?》在2008年即已出版,这是一则讲述母亲失踪的故事。从J市来首尔探望儿女的母亲,在首尔车站失踪了,这不仅让儿女们感到错愕,也让儿女们突然意识到此前对母亲的忽视,然而,也正因这种席卷而来的愧疚,让他们谁都不想承担这个责任,这让大家都受到了伤害。不过,母亲的失踪却也让儿女们在“寻找母亲”的过程中,重省母亲对自身的意义,最终承认了母亲的重要性。
在此,申京淑以母亲的失踪,来呈现现代人与现代生活的两难,即所谓以个人主义作为代表的现代价值,如何与以家族共同体为代表的前现代价值进行协商,以便维持一个平衡?在小说中,儿女们平日对母亲的忽视,正意味着现代价值与前现代价值正处在一种岌岌可危的状态,儿女们必须忽略“母亲/前现代价值”,才得以完整个人的价值。但是,与母亲共有的生活记忆与无法切断的血缘关系,却让他们始终与这个会破坏他们个体完整性的前现代价值维持一个欲走还留的暧昧关系,他们被这种暧昧关系拖住了后腿。
然而,母亲的失踪却也让儿女们重省母亲对他们所具有的意义,并让他们认可母亲的重要性,因而主人公“我”在最后说出“母亲,你知道吗?我也和你一样,这一生都需要妈妈”这种话。换言之,申京淑在试图让母亲失踪,以便与前现代价值进行切割的同时,却也发现自己其实无法真正割舍“母亲/前现代价值”。
申京淑的这一进退维谷,也正是现代人在传统与现代中游移的进退维谷。不过,这种进退维谷虽然让申京淑在拆解前现代价值的努力上落了空,却也更真实地勾勒出现代人对前现代价值,尚存有某种程度上的依恋,以及“个人/现代价值”与“国族家族/前现代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因此,申京淑让母亲在小说中只是失踪,而非死亡,她在该书《后记》中如此解释:“我想留下余地,母亲只是失踪了,还有找到的希望。”
但是,失踪了数个月的母亲是否还只是失踪?儿女们的这种“幸好只是失踪”的心情,是否只是一种为取消自身愧疚感的自欺欺人?并且,个人与家族共同体、现代价值与前现代价值得以不完全断裂,继续维持着欲走还留的紧张关系的首要条件,是必须继续把“母亲”镶嵌在那一甘愿牺牲奉献、埋葬自身欲望的神圣受难形象里。这是申京淑留下来的待解的习题。
2.《妈妈也知道》与《女人和进化的敌人》
申京淑留下的习题,到韩国70后作家的手上后,则显现出不同方式的反省与风景。2013年,韩国文坛70后作家的两位代表人物千云宁和金息,分别以《妈妈也知道》与《女人和进化的敌人》这两部作品,反思了韩国文学中母亲的既定形象,在她们的努力之下,韩国文学出现了全新另类的母亲形象。
1971年生的千云宁毕业于汉阳大学传媒系、首尔艺术大学文艺创作系。2000年,千云宁的短篇小说《针》被选入《东亚日报》“新春文艺”后,一篇成名,她独特的创作风格,也引发大量的模仿。
在短篇小说集《妈妈也知道》中,千云宁将焦点转而放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小说集收录的七个短篇,着重探讨在现代社会中看似自然却又异常的亲子关系。其中,在《睁眼闭眼》与《我的残酷而悲伤的孩子们》这两个短篇中,千云宁塑造出了一个被迫成为母亲的母亲。
这两篇各自独立却又彼此相关联的作品,起于一宗案件,但让人意外的是,嫌疑犯却是一对年龄分别只有14岁与7岁的姊妹。这两个“残酷而悲伤的孩子们”不仅其父不详,平日也无人照看,而她们姊妹俩的母亲在接受警方调查时,却跟警方抱怨说:“这不是我自己要生的孩子,她们是自己出来的。”
在此,千云宁将母亲的形象从原本的家国隐喻,回归到女性自身,就此,“母亲”终获主体性,“母亲”不再是家国、传统或是前现代的象征或替身,“母亲”就是“母亲”自己。千云宁让母亲具有了女性主义的内涵。
不过,比起千云宁,1974年生的金息走得更远。金息毕业于大田大学,代表作有《面条》《肝与胆》等,曾获得现代文学奖等殊荣。2015年,金息更以《根的故事》,拿下了韩国文坛最高荣誉的李箱文学奖。这部以老人、慰安妇、领养儿童等在现代社会被拔掉生命之根的人们为主角的作品,被评委会给予了如此评价:“以相对主义的视角照亮了悲伤的韩国现代史”。2016年,金息再一次将目光投向被拔掉生命之根的人们,推出了长篇小说《一日》,但这次金息则直接聚焦在慰安妇上,以此直面半岛的殖民创伤。
在长篇小说《女人和进化的敌人》中,金息不只不愿再复制神圣受难的母亲这一形象,更揭露出这种神圣形象背后可能存在的残酷与暴力,以及韩国社会中暗藏着的一种要求母亲必须具有牺牲精神的集体无意识。
在《女人和进化的敌人》中,小说主人公是一个母亲,为了让自己的小孩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未来,她决定与婆婆同住,以便随时使用婆婆的劳动力,让自己可以出去工作赚钱,让小孩可更早得到更好的生活空间。换句话说,这位母亲为了让小孩过上比上一代更好的生活,决心牺牲另外一个母亲,因为这样,从某个时刻起,她丝毫没有任何罪恶感地榨取婆婆的劳动力,而这也让跟佣人一般被媳妇任意使唤的婆婆,觉得自己宛如一颗“活化石”。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这位母亲被公司辞退了,这意味着让小孩搬到更好的生活环境的计划被迫延迟,甚至可能化为乌有,面对着可能无法获得“优秀母亲”这个高级赞美的母亲,只能把婆婆视为“进化的敌人”,将所有的怒气发泄在婆婆身上,以憎恶婆婆来释放自己无法成为一个“优秀母亲”的愤怒。在此,金息回应了申京淑此前曾讨论过的现代与前现代的进退维谷,但这次,现代的母亲则是要求前现代的母亲必须做出牺牲,以便成就自身,成就下一代。
据此,不管是千云宁笔下的被迫成为母亲的母亲,或是金息笔下那个企图以牺牲前现代母亲来成就自身的现代母亲,她们都是具有女性主义内涵的、具有女性主体性的、被摔出慈爱圣堂的母亲。这不仅解构了母亲这女性角色的神圣性、受难性,也对韩国社会进行了下列追问:是否每个女性都必定具有母性?母性是否如此与生俱有?母亲一定得承担这种社会不明就里所赋予的崇高价值吗?我们所存在的社会,尤其是男性,有对女性提出这种牺牲奉献、压抑欲望要求的资格与权力吗?
3.《我还要继续》
而“母亲”这一角色到了黄贞殷手里,又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形象。1976年生的黄贞殷,被韩国文坛誉为“文坛灰姑娘”。黄贞殷一向擅写都市边缘的荒唐景致,主人公也多数是都市边缘人,在她的长篇代表作《一百个影子》中,写的便是边缘人的存在与消失,都市的喧嚣与寂寥。而长篇小说《我还要继续》先是在韩国的重要刊物《创作与批评》季刊上连载,后黄贞殷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进行修改,才于2014年11月正式出版。
此前,黄贞殷曾在短篇小说《帽子》中,塑造出一个贫弱的父亲。在这篇小说中,每当父亲被忽视时,就会变成一顶帽子,渐渐地,父亲变成帽子的频率越来越高,帽子的帽檐也越来越高。在此,黄贞殷把父亲写成一顶不被重视、蜷缩在家中某一角落的帽子,以此削弱父亲的权力,并解构了韩国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家长制。而在《我还要继续》中,黄贞殷转而将这种目光移到“母亲”身上。
《我还要继续》分成四章,主人公则是小萝、娜娜与罗其。小说中,爱子在丈夫去世后,生活陷入绝望,此后,她的两个女儿小萝与娜娜的生活,就笼罩在爱子所带来的绝望阴影中,因而小萝与娜娜对母性、爱情与人际关系,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与怀疑。在这种情况下,住在隔壁的罗其及其母亲顺子,成了小萝与娜娜唯一的出口,一个救赎的可能。就在此时,娜娜意外怀孕,这让小萝与娜娜万分惊恐,在长期缺失母爱、在母亲的阴影下生活成长的她们,一方面因为憎恶母亲而拒绝成为母亲,另一方面也认为自己不配拥有爱,甚至是无力有爱、无力去爱。但即便如此,太阳还是会再次升起,生活还是会持续前进,因此她们说:“我们还要继续”。
这里,黄贞殷透过娜娜的怀孕,给予了小萝与娜娜一个可能,让她们得以以此去试探生活与命运中是否还有转机。但是,太阳还是会再次升起,生活还是会继续前进,爱子依然不会给予她们爱,她们也依然持续憎恶母亲,在一切都一如既往的情况下,娜娜最终会生下这个孩子还是打掉这个孩子?倘若生下来的话,这个孩子之后的命运为何?是会复制小萝与娜娜的命运,抑或是在她们两人试探出来的新可能中成长呢?对此,黄贞殷未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至少她已经先让这个世界多出了两种母亲形象:被憎恶的母亲和拒绝成为母亲的母亲。
4.《82年生的金智英》
就在韩国女作家们努力让“母亲”这一角色摆脱家国与前现代象征,夺回自身的主体性,并有了一些具体的成果时,赵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于2016年10月出版。在这本书中,赵南柱以“82年生的金智英”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很努力地抢回自己人生的主控权,但他们依然没有改变,他们还是将我们视作是一条“虫”!这里的“他们”与“我们”,分别意指以男性为中心的韩国社会和生活在这种不友善的环境中的韩国女性。
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一书的开始,当我们看到金智英一会儿变成母亲一会儿又变成挚友,假借她们的口吻对丈夫和婆婆说出自己的心声时,我们就知道金智英生病了。之后,在丈夫的安排下,金智英前往心理诊所就医。此后的内容,赵南柱以编年体的方式沿着金智英小学、中学、大学、求职、就业、结婚生子到离职当全职妈妈这一人生路线陆续展开。小说的叙述者或可说是金智英的心理医生,如此,将这本书视为是金智英的病历报告书也未尝不可。
透过金智英的病历表报告书,我们看到了金智英不能说是完全顺遂,却也是少有波澜的平凡人生。但这样平凡的金智英,究竟为何会罹患心理疾病?透过这份病历报告书,我们得知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妈虫”这个词。
何谓“妈虫”?“妈虫”是韩国带有贬抑意味的流行语,原指没有把小孩管教好的妈妈,后来变成讽刺有小孩却成天无所事事、到处吃喝玩乐、靠着丈夫养活的全职妈妈。书中,当金智英在心力交瘁的育儿生活中,好不容易得空,可以推着小孩去外面喝一杯一千五百韩元(约人民币约八元)的咖啡时,却听到隔壁的男性上班族如此嘲讽地说:“我也好想用先生赚来的钱买咖啡喝、整天到处闲晃……妈虫还真好命……我一点也不想和韩国女人结婚……”闻此,金智英茫然失措,仓皇离开,她不明白为何自己没有喝一杯一千五百元咖啡的资格?为什么自己赌上性命生下小孩,甚至放弃了所有的生活、工作与梦想,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却成为了这些男性口中的一条虫?
在此,赵南柱用病历报告书这一形式,将韩国社会对女性的歧视问题,透过金智英的患病呈现了出来,这不仅让女性读者感同身受,产生出“金智英就是我”这种共感,也让韩国文学多出了一个被歧视、被视作“妈虫”的母亲形象。
“妈虫”这一歧视性词汇出现的土壤,正是长期笼罩在韩国社会的一种意识:女性只能是男性的附属,母亲则必须牺牲奉献、抑制欲望。因此,当她们没有顺应主流的价值,产生出自我意志时,即便只是喝一杯一千五百元的咖啡,也会被韩国主流社会视为是理所当然的抨击对象,并认为她们被无视、被责备也只是咎由自取。而赵南柱则以《82年生的金智英》一书,对韩国社会的男性中心主义提出强烈的批判与抗议,并对韩国男性与韩国女性发出共同的提问:这样的生活,我们到底还要忍受多久?是以,赵南柱不仅是对男尊女卑的韩国社会发出抗议,更具有唤起女性觉醒的强大召唤力。这也就是为何《82年生的金智英》一书在台湾、泰国、日本甚至是在欧洲都引发关注,并在女性之间成为话题,近期更在日本卷起一股“金智英现象”的旋风之因。
跨入21世纪后,韩国女作家在处理多种议题的同时,始终不忘从自身的性别身份出发,对此前韩国文学中的母亲形象做出重省与解构。
申京淑透过在母亲失踪后油然而生的对母亲的依恋,很好地表现出现代人被卡在现代与前现代之间的两难,但与此同时,却也让“母亲”的形象更加固着在此前既定的母亲形象中,这不仅无法取回母亲的主体性,更让现代与前现代失去了沟通与真正和解的可能。
而千云宁、金息和黄贞殷这群70后的女作家,则联手抢回了母亲的主体性,使之具有了女性主义的内涵,并创造出被迫成为母亲的母亲、牺牲另一个母亲的母亲、被憎恶的母亲和拒绝成为母亲的母亲这些让人深思的形象。它们不仅丰富了母亲的形象,也让母亲的形象不再依附于男性论述,不再受制于此前以男性为中心所形构出来的神圣受难和一味奉献。
到了赵南柱,她则以金智英的病历报告书对女性做出社会性的提醒,她提醒韩国女性,光是在纸面文字上夺回母亲的主体性是不够的,必须在现实生活中也活出自我,不能在这个对女性不友善的社会中甘愿被消音。同时,韩国女性也不是某某妈或是某某太太,她们有着自己名字,也就是她们从小到大写在各种姓名栏位上的那个名字,她们就是她们自己。
(作者:蔡钰淩,系清华大学博士生)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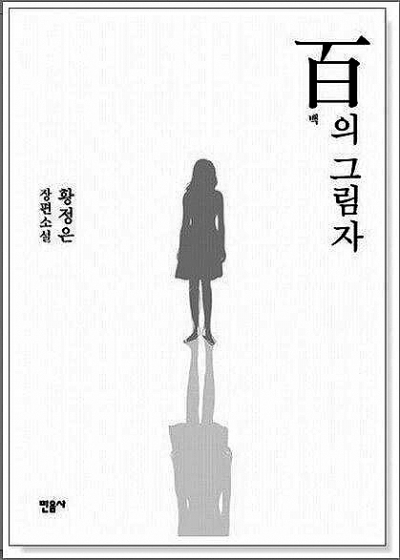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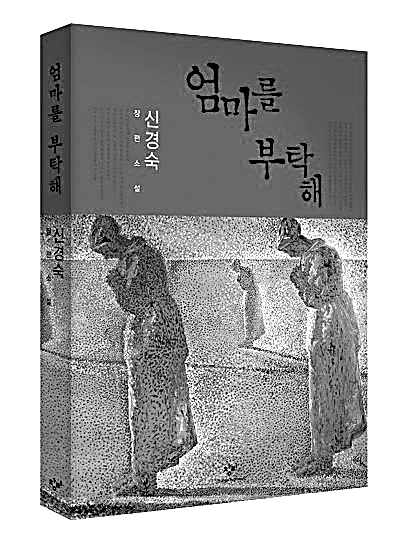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