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可以说包括了近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史研究和《诗经》《楚辞》研究,而其中尤以《诗经》《楚辞》研究为主要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他创获丰硕、成就卓著,蜚声海内外。
先看《楚辞》研究。陈先生的《楚辞》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他已年逾花甲,一千多年来蒙在楚辞研究领域的层层迷雾,促使他下决心要作一番爬梳剔抉的工作,努力还世人一个近真的《楚辞》原本面目。为此,他翻遍了历代的《楚辞》注本,认真系统地研读了马、恩和西方许多理论家关于人类历史及社会发展的论著,参考了大量的上古时代历史、文化、风俗、天文、地理、政治、军事等出土文物资料和历代文献,其目的在于还屈原与《楚辞》的历史真面目,同时对历来的楚辞研究诸说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尤其突出的是,陈先生在研究中有意识地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相结合,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多学科——历史、神话、考古、文化、地理、政治、军事、天文、动植物等相融合。在此基础上,他阐发了属于个人的独立研究和独到见解,其治学特点真正体现了自己所奉行的宗旨:不苟同,不苟异,不溢美,不溢恶,实事求是,无征不信。
陈先生提出,自己不愿无据而否定史有屈原其人,也不愿无据而肯定屈原的任何作品,凡古今人士所揭出的疑问,他都广搜前人成说,并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予以一一爬梳澄清。在《楚辞直解》一书中,他明确提出了属于个人独立研究的论见——屈原二十五篇诗歌作品,集中体现了屈原的人格、志向、理想、追求,是屈原个人真实心声的吐露,而屈原的思想,乃是兼摄了先秦诸子各家(包括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方术家、纵横家等),且又体现了他个人独特风格特色的一家。
不仅如此,陈先生还将对屈原认识的视野,置于世界文学史的高度,认定屈原的作品堪与古希腊荷马史诗、意大利但丁《神曲》、莎士比亚戏剧、歌德《浮士德》等世界一流大家作品相媲美,这充分体现了其高屋建瓴的深邃目光和宏微结合的真知灼见。
陈先生在阐释屈原及其作品的过程中,特别提倡历史唯物主义。他指出,我们研究古典文学,必须以客观现实、时代思潮、历史背景,以及作者个人的特殊条件,作为创作源泉的反映论,才能对其作出相应的客观评价,如只是从作者的主观情趣和灵感、个人想象和幻想、无目的的抒写和纯审美的渲染角度看问题、作阐释或解说,就会难以说通,也就难以令人信服。这充分体现了陈先生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研究立场和态度。
可以说,集楚辞全部作品注、释、笺、译、论之大成的《楚辞直解》一书,确立了陈先生在现代楚辞学界的地位和影响,他自然被聘为了中国屈原学会的学术顾问,并被列为二十世纪楚辞研究八大家之一。
陈先生的《诗经》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问世于20世纪30年代的《诗经语译》;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出版《国风选译》与《雅颂选译》;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集大成的《诗经直解》出版。但实际上,他为研究工作所做的各种准备,却早在青年时期即已开始。先生对自己的研究风格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读遍世上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决不妄下结论。他的这种有目的的广泛阅读,为他正式着手研究《诗经》打下了厚实基础,而他沙里淘金的治学态度,使其研究结论更能逼近文本的客观实际,更符合历史和社会的真实。
陈先生认为,《诗经》三百多篇作品从各个不同角度和层面反映表现了上古时代的社会生活,是上古社会和历史的一面镜子。对于历来争议较大的一些疑难问题,如孔子删诗说、采诗说、诗序作者、风雅颂定义等,陈先生都旗帜鲜明地表述了个人看法。
对于两千年来陆续问世的历代《诗经》注本,陈先生指出,它们虽然都有参考利用价值,却也不免门户之见和宗派情结,给本来就难以“确诂”的《诗经》蒙上了层层迷雾,使人真伪难辨、不知所从。鉴于此,陈先生态度十分明确,不唯古人所说是从,不做“毛(毛亨、毛苌)郑(玄)佞臣”“三家媚子”“朱子信徒”,也不对古人成说一概否定、全盘抛弃,而是一切从客观事实出发,是即是,非即非,明确弃取,毫不含糊,关键看是否合乎诗旨本义。
为此,陈先生既要和古人“抬杠子”——指谬正讹、去芜存精,也要和今人作辩论——辨必有据、辨伪求真。比较典型的例子之一,如对待“诗序”的态度。古人唯儒家说教为尚,自然将汉代问世的“诗序”奉若圣旨,而近期不少学者受“左倾”思潮影响,认为“诗序”是封建贵族阶级为维护本阶级立场利用《诗经》所做的儒家说教,全属牵强附会之说,应一律予以删汰弃之。而陈先生不然,他虽也认为“诗序”乃儒家说教,在解诗中较多地取用了“三家诗”说,但他并不对“诗序”一棍子打死,而是把它结合在具体的解析作品过程中。凡“诗序”解释合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者,他都明确表述为“诗序不误”,而且他还在《诗经直解》一书中每一篇诗的开首,引录了相应篇章的“诗序”,供读者参照,这显示了他与近世诸多学者的迥然相异。当然,对“诗序”所言有误者,他自然毫不客气地会一针见血指出其弊病,这充分体现了他“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客观认真态度。
陈先生诠释《诗经》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即为了解析诗篇本义,特别是其中可能涉及的历史与社会的多学科广博知识,他都会予以详尽的引证,而这些引证的材料,很可能要涉及天文、地理、历史、风俗、生物、考古、农业、军事、经济等多学科、多层面,他都会不厌其烦地加以阐释和说明,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案例,如《曹风·蜉蝣》《小雅·信南山》《小雅·宾之初筵》《周颂·良耜》《周颂·潜》等诗篇。
需要指出的是,与古人及今人各种注本相比,陈先生的《诗经直解》,有着独特的体式:原诗与译诗上下并列,便于对照阅读;译文力求正确、畅达,努力保存原始风味与民间习气,不苛求再创造;注释汇集前人成说,兼采近人新见,博观约取;解题(“今按”)尽力切近诗本义,扼要评述“诗序”与反“诗序”诸说;“韵部说明”方便读者了解诗韵。
陈先生之所以如此精心安排体式,乃是取了历代注家的长处,体现其兼顾普及与提高的良苦用心:既使一般读者借助本书的今译、注释,能读懂、弄通《诗经》,了解其内容与风格特色,又可使研究人员省却翻检之劳,借助本书可获得较多参考资料,便于参酌对照,从中获得启示,甚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
可见,无论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两个维度,还是从兼顾普及与提高两个层面看,陈先生的《诗经》研究都达到了很高的层次,他堪称二十世纪《诗经》的研究大家。许杰先生用“诗骚直解堪千古”来赞誉陈先生研究《诗经》和楚辞的杰出成就,来概括他毕生的辉煌学术业绩,应该说是言符其实的。
(作者:徐志啸)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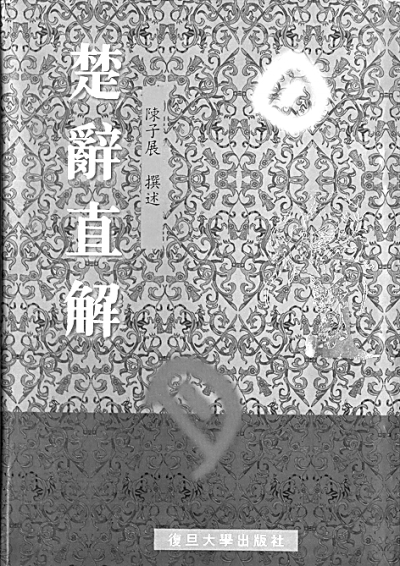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