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很多头衔和成就——复旦大学党委委员、研究生院院长,西藏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发表论文200余篇,获国家发明二等奖一次,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三次……但他更愿意称自己是“一名工作在青藏高原的生物学家,一名来自上海的援藏教师”。他说,人这一辈子,不在乎发了多少论文,拿了多少奖项,留下来的是故事。
他有很多传奇——15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毕业后从无线电专业转行植物学和生物信息学,短短几年就站上这一领域的学术前沿;33岁时已是一名副局级干部,前途一片大好,却毅然放弃所有职级待遇,来到复旦大学做一名普通教授;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30余年,学术援藏16年,在雪域高原跋涉50多万公里,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帮助和推动了西藏大学的植物学专业从“三个没有”: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申请过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到创造一个又一个“第一”,不仅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一系列空白,更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
他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参与SARS病毒和血吸虫基因组的进化研究,获得重大突破;科普类畅销书《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的中文版译者;2010年上海世博会英国馆种子殿堂里40%种子的提供者;义务参与上海科技馆科普工作17年,撰写大量中英文图文版,是深受青少年欢迎的明星专家和科学队长。
他叫钟扬,一位拥抱时代的先行者,一位播种未来的追梦人,他是先锋者,更是奉献者。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在追逐梦想,都在奉献祖国,他是扎根大地的人民科学家。
2017年9月25日清晨,在为民族地区干部授课的出差途中遭遇车祸,钟扬53岁的生命定格在那一刻。消息传开,网上网下,人们自发地追思他,怀念他。
他说,最好的植物学研究一定不是在办公室里做出来的,祖国那些生物资源丰富的地方才是生物学家最应该去的地方。所以,他选择了西藏,因为那里是国家生态安全战略重地。从2001年起,钟扬10年自主进藏开展科研,此后更连续成为中组部第六、七、八三批援藏干部。
16年间,他的足迹遍布西藏最偏远、最艰苦、最荒芜的地区,经历过无数生死一瞬。他一直对学生说,“只要国家需要、人类需要,再艰苦的科研也要去做”“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他深知,种质资源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事关整个人类未来。他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他把论文书写在祖国的山川大地,他用生命在天地之间写就壮阔的时代故事。
2015年,钟扬突发脑溢血,死里逃生苏醒后,第一时间口述记录下一封给党组织的信:
“这十多年来,既有跋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的艰辛,也有人才育成、一举实现零的突破的欢欣;既有组织上给予的责任和荣誉为伴,也有窦性心律过缓和高血压等疾病相随。就我个人而言,我将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在同事的记忆里,他是与时间赛跑的人。他的衣袋装着很多小纸片,上面密密麻麻写满待办事项,每做完一项就用笔划掉。每次出差都选择最早班飞机,只为到达后就能立即开始工作;他常在办公室工作到半夜,闹钟固定设在凌晨3点,不是用来叫他起床,而是提醒他到点睡觉;突发脑溢血后,只住了十几天医院就重新投入工作,而当时的他甚至连午餐盒都无法打开;他的随身听里是请学生录的藏语听力教材,他说:“没人规定援藏干部要学藏语,但是用藏语,是表达尊重的最好方式。”
“在我的课题组里,学生才是上帝。”这不是钟扬的一句玩笑话,在他的实验室里,每个学生做的都是最适合自身的研究。在他眼里,每个学生都是一颗珍贵的种子。就像收集种子一样,他用心培养,因材施教,期待他们长成参天大树。钟扬特别喜欢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他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尤其难,但培养好了,这些学生回到家乡,就能成为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军。十几年间,他培养的学生遍布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云南等西部省份。他说,“我有一个梦想,为祖国每一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
忙碌的科研教学之余,钟扬还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大众科普教育事业。在他看来,最应该做科普的就是一线科学家。他说,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事业,而科学家的特质就是从中提取欢乐,然后把科学和欢乐一起带给大家。
历经多个领导岗位,钟扬永远严格自律、简朴廉洁。一条29元的牛仔裤陪他跋山涉水,3件短袖衬衫就可以过一个夏天。他从不对职务待遇、收入条件提任何要求,他心里想的只有做事,做对国家有用的事。
告别会上,钟扬80多岁的父亲对治丧小组提出了家属唯一的要求:“只希望在悼词里写上,‘钟扬是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相关报道见7、9版)(本报记者 颜维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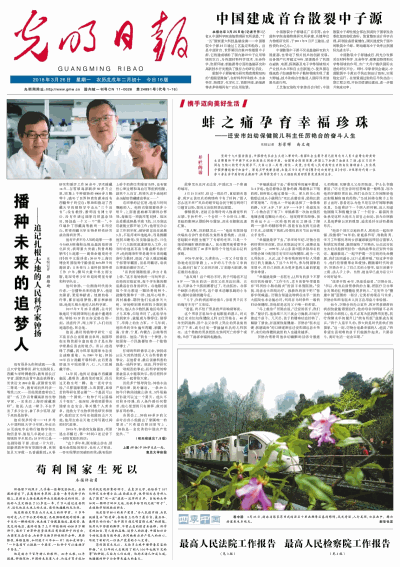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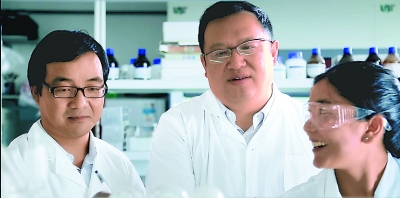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