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我与宿白先生并无深交,见他,多是在每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上。作为考古界的泰斗,在那种场合,想和他说话的考古人太多了,根本轮不上我开口。于是很多次就那么远远地看着众位考古大咖洗耳聆听他教诲的恭敬样子。
2013年春,“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如期召开,却没有见到宿先生。知情者说,宿先生91岁高龄,身体不太好,这么高强度的工作不敢请他参加了。就在那时,“抢救性”采访的念头在心里长了草。
电话打到家里,宿先生开始一直婉拒,“我那些做的事儿,没什么特别的”,总让我去采访其他学者。从7月开始,我隔段时间就打个电话,“死缠烂打”的战术终于奏效,他同意给我两个小时。
9月,一场秋雨让京城的气温骤降。绵绵细雨中,我如约按响了宿先生家的门铃。
不大的房间,老式沙发,木头桌子,柜子里、桌面上、沿墙边都堆放着大量书籍,这也和许多学界大家一样,一切就如宿先生的口头禅所说——“没什么特别的”。
虽然之前有过多次电话沟通,但说起考古生涯,老先生还是连连退缩:“都是些该做的事儿,没什么好采访的啊。”面对记者不依不饶的“纠缠”,宿先生笑了,开始用略带东北味儿的口音讲起了自己的“想当年”。
田野考古,无疑是辛苦的——“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拣陶片的”,这是人们对考古队员的描述,虽然夸张却也反映出田野考古的艰辛。然而,宿先生却总是说“没什么特别的”。说到1951年冬季在河南白沙水库考古,春节在工地过,他竟然说:“在深埋于地下的墓穴中竟也未觉寒冷。当时大家的热情很高,很专注,也就不觉得冷了。”说到1959年和1988年两次入藏做西藏地区首次文物调查,路途劳顿、高原反应,都被他轻描淡写地带过,而说起调查到的文物情况却是滔滔不绝。其实,明白人都知道,当年田野考古的条件比现在艰苦多了。
聊到取得的成就,宿先生的口头禅“没什么特别的”出现的频率就更高了。谦虚,在宿先生那里,不是形容词,而是化入血液、如同呼吸般自然。
采访结束前,我请宿先生为《光明日报》题个词。他略为思索,写道:“为文化遗产做点实事。”“咱们共勉吧。”他说。
(本报记者 李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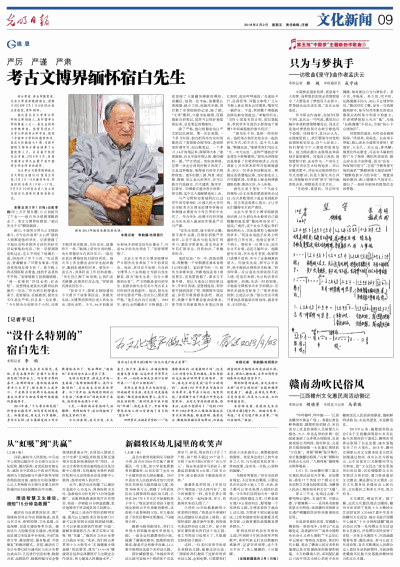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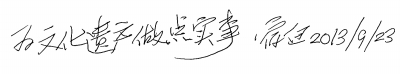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