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济先生一生对词学研究都抱有浓厚兴趣。少年时期,他曾在姑父松琴龙家中读过古今词集,奠定了厚实的词学基础。1912年至1917年客居上海期间,晚清词坛的两位著名词人——朱祖谋和况周颐,碰巧也寓居上海。刘永济以一首《浣溪沙》(几日东风上柳枝)向况周颐请益,况周颐大为赏识:“能道‘沉思’一语,可以作词矣!”朱祖谋也赞许刘永济“能用方笔”。
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被两位词坛老宿誉为作词得法,且有作词的天赋,这对刘永济来说,如有一种“登龙门”的感觉,并终身以况、朱传人自勉,致力于弘扬常州词学。后来,武汉大学同事苏雪林教授,常语含讥讽地称他为“旧式文人”,倒也恰切地说出了新文化人对刘永济的定位。
刘永济的词学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论“填词之事”,代表作为《词论》《宋词声律探源大纲》,重心在词调、声韵、歌辞;二是词史研究,代表作为《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其论述时有卓见,尤其是对吴文英词史地位的评价,在20世纪的大陆学界独树一帜;三是对唐宋婉约词细读,尤其是对吴文英词的细读,代表作为《微睇室说词》。
刘永济之所以偏重吴文英词,既是因为他上承常州词派的统绪,对吴文英词的文学史地位有大不同于主流学术的看法,也是由于在数十年的研词生涯和填词生涯中,吴文英词已经与其艺术生命融为一体。1940年,时年53岁的刘永济,曾作《减字木兰花》二首。其小序云:“岷沫二水汇合处,陡起一峰,林壑幽美,步磴周曲,曳杖其间,如入梦窗翁词境中也。”刘永济以山水景物比拟吴文英词境,可见他沉浸于梦窗词中,读的已不是词句,而是词句所展示出的意境。考察刘永济对吴文英词的细读,不应忽略了长存于其心灵中的这一境界。
《诵帚盦词》是刘永济自己的词集,收录了他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创作的词作。其间,大故迭起,忧患不断,词人之心,激荡不已,刘永济的词,就是在这样“艰屯”的岁月中写成的。从1931年到1949年,几乎所有重要的世变都在刘永济的词中有所呈现或折射。例如,1931年作有《满江红》(东北学生军军歌。辽吉沦陷,东北诸生痛心国难,自组成军,来征军歌,以作杀敌之气,为谱此调与之)、《满江红》(避日寇入北京,赁庑愁坐,示内子惠君)等;1932年作有《解语花》(壬申上元,淞沪鏖战正烈,故京灯市悉罢,客枕无寐,竟夕忧危。翌日,豢龙写示和清真此调,触感万端,继声赋答)等;1943年作有《鹧鸪天》(残劫关河赚泪多)、《鹧鸪天》(孤桐寄示《齐天乐》词,惠题拙著《笺屈六论》,兼及豢龙永逝之哀,赋此答谢)、《浣溪沙》(客谈北平广播荀慧生歌曲)等。这些词,或直写世变,或缘于世变,都足以成为后人的“论世之资”。即使那些唱酬、悼亡之什,也有其存史意义。
在数十年的人生经历中,刘永济乐于以诗词与亲友交流。他的复旦同窗陈寅恪,清华同窗吴宓、吴芳吉,东北大学和武汉大学时期的同事刘豢龙,终身对刘永济执弟子礼的程千帆,胞弟刘永湘,都与刘永济多有唱酬。在20世纪40年代的武汉大学同事中,较多见于《诵帚盦词》的有陈登恪等人,如1940年作《江城子》(六月廿六日偕家人放棹至柿湾,访登恪八兄草堂。饭后坐邬保良兄岩下屋,凉既宜人,顿忘炎暑,曛黑始归);1946年作《鹧鸪天》(听登恪话西湖匡庐之胜);1947年作《临江仙》(今夏,余与登恪有匡庐避暑之约,因循未往,而登恪归来为语劫后灵山,感而成咏)。陈登恪是陈三立的第八子,陈寅恪的弟弟。这些词作,在情感交流之外,还兼有日记的功能,依时序排列,便是一份年谱。如果要了解近代学人之间的朋友关系和家庭交往,这些词作无疑比所有的宏大叙事都来得真切有味。
(作者:陈文新)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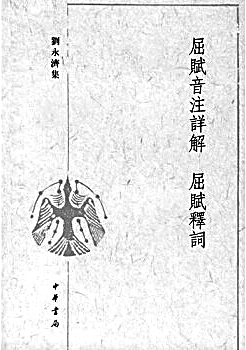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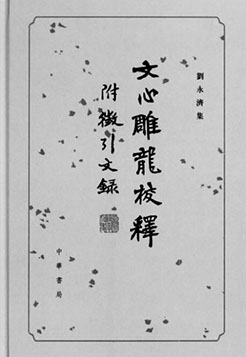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