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书话】
说到细读,人们首先想到的,大约是英美新批评派。这个活跃在“二战”前后的文学批评流派,提出的重要术语之一,就是“细读”(close reading),即通过细致的阅读,发现文学文本中的反讽、悖论等特点,进而引出关于语言之张力的论述。为了反对意识形态介入对文本的解释、同时也反对思想对艺术的侵扰,新批评派更注重从文本到文本的解释。而这一倾向,也造成了包括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在内的解构派对其进行解构批评的一个口实。
拙著《沙与世界:二十首现代诗的细读》中的“细读”二字指什么?它是从新批评来的么?如果要我做一个简单的回答,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十多年前,当我还在读大学二年级,一边旁听中文系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一边读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并试着写下第一篇诗歌细读的文字时,我对新批评派根本不甚了了。以后几年,也没有给予太多关注。那时的阅读兴趣,逐渐从文学转向哲学。而在哲学系上的不少课以及参加的读书沙龙,大都与“细读”或“精读”有关。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都曾在课上一字一句地读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观念》在老师带领的读书小组中也读过,《心经》和《尚书·洪范篇》则是在读书沙龙中听老师的详细讲解后多次读过。
工作之后身在文学院,才回过头来补“新批评”的课。虽然也有收获,可是像大学时读哲学书的欣喜乃至惊绝之感,并不是很多。因此,回想起来,倒是在哲学系的学习,对我后来渐次写成这些“细读”文字,影响更为直接一些。
话又说回来,“细读”是独属于“新批评”的么?在新批评派将“细读”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提出来之前和之后,难道没有过其他样式的“细读”么?现象学的方法,不就是关于细读的一个很好的范式?在《艺术作品的起源》中,海德格尔对梵高的名画《农鞋》所做的描述和阐释,既是现象学方法的经典呈现,也可以看做是“细读”的一个典范。随着新世纪的脚步被引进汉语学界的、以列奥·施特劳斯及其友人和学生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学派,对古典作品的论述与分析,难道不是“细读”?从《圣经》到古希腊经典,从希腊罗马一直到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距离今天更近的现代和后现代,不难发现,通过古典政治学派的“细读”和耙梳,西方思想的图景在我们的视野中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而他们对历代经典展开论述的基本方式则是“绎读”“解读”“解释”“释义”“义疏”“疏证”“讲疏”“剖析”……不只是“细读”,还是对“细读”及其意义的伸张与开拓。
虽然上述“义疏”“解释”等名目多变的称谓,多是中文翻译的结果,但是从其论述的具体展开方式来看,如此称谓也是名副其实的。它同时提醒我们,反观汉语世界自身的传统。与之相似的是,从古至今,无论是对四书五经的历代校勘、注疏与释义,还是各类选本的评注与绎读,抑或像李贽、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人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所做的旁批与点评,其实都是“细读”,只是侧重各有不同。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笔者在南京读书时,有缘读到的《德林老和尚讲〈金刚经〉》(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江味农居士的《金刚经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等具有醍醐灌顶之效的开示之作。这些文意通透的讲释,当然也是对经文的“细读”。类似的作品似乎不大进入主流学界的讨论视野,其谈论问题的方式与方法也较少得到学界的关注,但是作为一种中国式的学习和细读样态,它们无论如何不该被忽视。这些学习和谈论问题的方式,给予后学者的方便和启发,同样不容抹杀。
以上各种“细读”,路径和归旨各有不同,讨论问题的基本方式则是一样的:细致、虔诚、充满思想的张力与开解力。于是,就带来一个问题:“细读”只是一种阅读的方法吗?难道它不也是阅读、进而做事和为人的一种基本态度,甚至一种基本的德行?
记得多年前,笔者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翻开书即看到前面的《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竟提到“读法”八十一条。其中有:
(六十一)《西厢记》必须扫地读之。扫地读之者,不得存一点尘于胸中也。
(六十二)《西厢记》必须焚香读之。焚香读之者,致其恭敬,以期鬼神之通之也。
(六十三)《西厢记》必须对雪读之。对雪读之者,资其洁清也。
(六十四)《西厢记》必须对花读之。对花读之者,助其娟丽也。
读到这些话时,我几乎哑然失笑,禁不住腹诽金圣叹的天真和迂腐。及至读到:
(六十五)《西厢记》必须尽一日一夜之力,一气读之。一气读之者,总览其起尽也。
(六十六)《西厢记》必须展半月一月之功,精切读之。精切读之者,细寻其肤寸也。
又不得不叹服金圣叹实在是个“读书种子”,懂得如何读书。继而自我责备:如此天真、单纯、会心到虔敬的读书态度,去讥诮、毁谤它,实在是罪过。而所谓讥诮,不过暴露了讥诮者在做人上的虚浮、油滑,乃至庸堕。
从大学起十多年的学习,让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大至生活的基本观念与取向,小至如何看待别人的认真,包括认真到极致的迂痴,都是基本的人生态度问题。面对文艺作品时,这些态度又会直接影响、甚至决定我们从中会读到些什么,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和判断,并最终决定我们会成为怎样一个人。古典政治学派经常提起一句话:“敬畏,是从一个伟大的心灵所写下的伟大作品中学到教益的必备条件。”比敬畏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虔诚,乃至虔信——虔信不是迷信,不是取消自我的思想,而是经由自我辩驳之后的认知。我将这些称之为阅读的德性。虽然阅读的德性与人的德行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前者对后者具有可能的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比如马一浮先生就曾说,读书的目的不在以“博文”炫人,而在“穷理”,更在“畜德”。这样的中国读书法,是值得我们记取并师法的。
(作者:宋宁刚,单位: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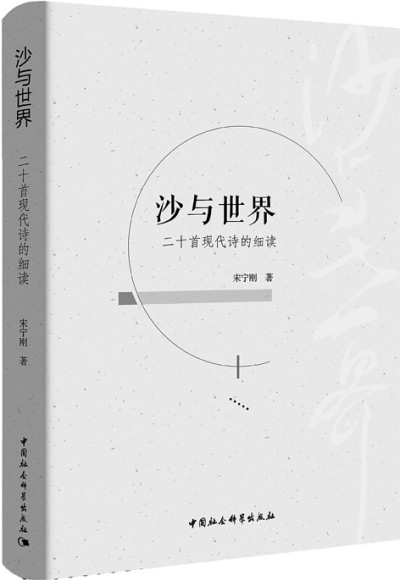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