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本只有184页的“亲民版”《高数笔谈》,让东北大学92岁的退休老教授谢绪恺成了“网红”。每天从早到晚,打到出版社及老人家里的电话不断。微博上700多条留言,有400多条是求购谢老新书的。出版社加印的图书售罄,亚马逊、当当、京东等网上书店也同时挂牌“缺货”。
7月16日上午,记者来到谢绪恺位于东北大学北门附近的家。站在门口迎接记者的谢老笑容可掬,让人相信了那句话:大学精神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深奥,而恰恰是恢复人类的天真。
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从1950年我走上学校讲台,到2005年退休,我在大学教书整整55年。作为从一线退休的老教师,偶然翻阅一本高数教材,我感到十分惊诧。”谢老说,数学应当是最好学的,因为它讲道理,但现行高数教材不仅品种单一,而且晦涩难懂,为此我决定为学生写一本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高等数学参考书。
1.32岁提出“谢绪恺判据”
谢绪恺是四川广汉人,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电机系无线电专业,被安排到上海民航局工作两年。1949年5月到广州,恰好是国民党大溃退,本来应当去台湾的他无意间看到了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了解到国民党的昏庸与腐败,于是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应聘来到东北后,谢绪恺曾任大连工学院电信系讲师,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来到东北大学(当时为东北工学院),历任电气工程系讲师,数学系副教授、教授,是当年东北大学控制理论“第一人”,并编著有控制科学早期教材之一《现代控制理论基础》。
据谢绪恺介绍,在自动控制科学领域,控制系统的稳定性研究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稳定性是控制系统最重要的特性,控制系统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外在和内在因素的干扰,例如运行环境的变动、控制系统参数的改变等。因而,自动控制理论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研究控制系统的稳定性问题,并且找出措施来保证控制系统的稳定运行。经过大胆假设和缜密论证,谢绪恺打破常规,给出了线性控制系统稳定性的新代数判据。此时,他刚刚32岁。
所谓“谢绪恺判据”,用谢老自己的话说就是“稳定性是系统能够工作的首要条件,就好像人走路不稳就要摔跤,我就是要尝试用一个代数判据来描述系统的稳定性,分别给出稳定性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这样的判据较之经典判据计算量要小得多,因而使用起来更方便,工程的实用价值更大”。
1957年早春,中国第一届力学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谢绪恺主动提交论文,并破天荒被邀请参加。开会当日,钱学森、周培源、钱伟长等众多力学界大师悉数到会,盛况空前。提起这次半个多世纪前的会议,谢绪恺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我所在的小组共5人,一位哈军工的老教授讲完后,我第二个发言,步入会场时不觉眼前一亮,钱学森先生在第三排正中赫然就座,其后一排偏右的是著名数学家秦元勋先生,我内心非常激动,在汇报自己在线性系统稳定性方面的一些探索时,渐渐进入角色。”
令年轻的谢绪恺惊喜的是,钱学森先生高度肯定了他另辟蹊径的创新思路,还点拨他说:“可以将你判据中的常数改为随机变量,这项工作尚无人开始研究,肯定能出成果。”不久后,秦元勋先生在北京主持了一个微分方程讨论班,并邀请谢绪恺参加,继续深造。其间,秦元勋先生高兴地告诉谢绪恺:“我已向华罗庚先生汇报了你的成果,华老一听,马上拍桌子说:‘成果太漂亮了’!”前辈的期许令谢绪恺备受鼓舞,激励着他在学术的道路上策马扬鞭。
1959年,复旦大学数学系主编的教材《一般力学》中,将谢绪恺在力学学术会议上所报告的成果命名为“谢绪恺判据”。10余年后,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聂义勇改进了判据中的充分条件,于是有了“谢绪恺-聂义勇判据”。清华大学教授吴麒、王诗宓主编的教材《自动控制原理》将“谢绪恺-聂义勇判据”与世界公认的两大判据——“劳斯判据”和“赫尔维茨判据”并列,将原有的两大判据变成三大判据,从而在稳定性方面开始出现以中国人命名的研究成果。
2.学校“复课第一人”
正当谢绪恺在学术道路上意气风发时,却被错打成右派分子,到昌图农村扫马圈改造。在常人看来,这无异于命运的一次“滑铁卢”,却不料成为谢老一个人生的新起点。
“回首我的人生,应该以1958年我下放到昌图劳动为转折点。到昌图劳动之前,我每个月能领到149.5元的工资。有一年假期,我翻译了一本书,就赚了3000元。就当时的消费水平而言,可谓高收入,可是我还不满足。到昌图农村后,我看到农民生活极度贫困,却无怨无悔,质朴善良,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分土豆给我吃,这对我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震撼。”谢绪恺说,人生有两条道路,一条路是追名逐利,追求物质享受。第二条就是我最终所选择的,满腔热血地为人民服务,勤勤恳恳,将自己融入人民群众。想通这些,我不再患得患失,把全身心都融入教学工作中,虽然后来也遇到过很多困难,但始终能够笑对人生。
在接下来超过半个世纪的岁月中,谢绪恺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横跨自控系、数学系,涵盖本科生、研究生的近20门课程,他给数万名学子留下汗湿衣襟的背影。这位温和而坚定的老人说,就像大树离不开泥土,自己离不开学校和学生。
“他为我们讲的第一堂课是拉普拉斯变换,一下把所有学生都给镇住了。课后答疑时,不管被多少学生重重包围,不管问题有多难,谢老师都能对答如流,我们发自内心地佩服他!”原沈阳市人大副主任、东北大学校友宋铁瑜是谢绪恺的学生,回忆起当年上课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文革”开始后,学生开始停课闹革命,谢绪恺焦急万分,却又无可奈何。1970年,有学生在路上偷偷叫住谢绪恺:“老师,能不能为我们补补课?”正在迟疑的当口,学生又发话了:“老师,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我看过您的档案。”这句话让谢绪恺热血沸腾,冒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风险,在由几个学生轮流“放哨”的宿舍里,偷偷给学生们补课,成了“文革”期间学校“复课第一人”。
1994年,东北大学理学院组建,各项工作千头万绪。谢绪恺受校党委之托,69岁担任理学院首任院长。这位早可以退休在家、含饴弄孙的老人每天早早来到办公室,很晚才回到家中,认真思考并规划着理学院的未来。
学科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谢绪恺非常注重人才引进,方肇伦院士就是他任理学院院长期间,从中科院生态所引进的优秀专家,连同此后引进的10余位博士生导师,共同撑起了理学院的人才大厦。“站得高才看得远”,他大力倡导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使理学院形成了用高水平科研成果反哺教学的传统……短短3年时间,谢绪恺带着理学院逐步进入良性运转的轨道。
到1997年离开理学院院长岗位时,谢绪恺已经是72岁的老人了。可是他仍然没有“回家”,又受聘到网络学院,教了8年离散数学,直到2005年才彻底告别讲台。谢绪恺开玩笑地说,其实我还能上讲台,我就是怕死在讲台上,给别人添麻烦。
“谢绪恺是我的老师。我1980年来校攻读硕士学位,现代控制理论课程就是谢老师教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东北大学教授柴天佑对记者说,他一直把谢老师作为学习的榜样,谢老师身上有许多优秀品质。一是做学问精益求精。现在很多人做研究急于发表文章,真正把学问做深的人很少。而一个老师是需要把学问做深的,这样才能把课教好、把人培养好。二是对教学高度负责,能把科研和教学密切结合。我记得当年上控制理论课的时候,谢老师讲解的内容推导完全是用工程来解的,体现了他对控制理论的深入了解和深入掌握。三是谢老师对学生充满了爱。老师一定不能忘了初心,只有以身作则、认真负责,才能培养出好学生来。
3.高数原来这么有趣
高等数学是棵大树,有多少学生挂科挂在了这棵高树上。这虽然是一句调侃的话,却道出了许多学子共同面对的困难。
谢绪恺说:“数学是有魔力的,那种魔力可以让人忘记解题过程的苦思冥想与寝食难安,当找到答案并且得出证明的那一刹那,成功的兴奋与激动战胜了所有的劳累与辛苦。”追求真理、接近真理的幸福感,让谢绪恺觉得数学是如此之美。
数学本来就来源于群众实践,本不该高居庙堂之上,谈起目前学生们普遍觉得高等数学比较难这个问题时,谢绪恺分析道:“我国现行的高等数学教材品种单一,而且偏重演绎推理,很难兼顾工科学生的特点。如果说数学系学生要学会数学是什么,那么其他专业的学生只要会用就行了。”为此,在编写《高数笔谈》之前,谢老对这本书的定位就是:将数学问题工程化、工程问题数学化,使工科数学通俗化、接地气,用浅显的语言来说明深奥的数学原理,为学子们写一部“用怀疑眼光探究高等数学的手边书”。
“记得在2015年11月3日上午,我第一次来到谢老家中商谈书稿出版事宜。令我没想到的是,见面当天我和谢老竟然从上午9点一直谈到中午12点30分。”东北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向阳告诉记者,“一进屋,谢老就非常热情,特意给我准备了水果、饮料和茶水,谈话间得知我和谢老算是半个老乡,所以谈的话题也比较多。”
谢绪恺从2015年开始着手写《高数笔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完成全部书稿。整部书稿22万字,100多张图表都是他亲自手绘。为了保证自己有足够的体力完成著作,谢绪恺专门编了一套健身操。只要身体能吃得消,他就投入到书稿的撰写当中。
为了让学生们“一看就懂”,谢绪恺尽量将深奥的定理与日常生活、常见问题、寓言故事结合,深入浅出地讲述出来。比如谈到极限,他写道:五个婴儿自呱呱坠地,日复一日,吸吮乳汁,逐渐成长。但有史以来,尚未出现高过4米的人,这就是极限。谈到拉格朗日定理,他说,兔子和乌龟赛跑,假设兔子平均速度是10米/秒,实际奔跑过程中,兔子的即时速度不可能一直大于或者小于10米/秒,在从速度大于10或小于10的转换过程中,必然至少有一瞬间等于10米/秒。在谢绪恺给学生出的习题中,更是包揽了哲学、文学、国学等各个学科,让人读来亲切自然而又忍俊不禁,例如习题1.1第1题是庄子有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试据此构造一数列,并求其极限。
谢绪恺在完成了一小部分书稿后,希望让更多的读者看到样稿,让读者看看这种写作方式行不行,然后再根据读者的意见进行调整。他委托出版社副社长向阳找到十几个学生,让他们看样稿。当时看样稿的学生不知道作者是谁,这也是谢绪恺特意交代的,他担心一旦师生知道样稿是谁写的,就可能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
“2016年5月,在我大四快毕业时,收到一份‘特殊的邀请’——为一本高数教材参考书提修改建议。接到这个任务时,我很惊讶,作为学生干部,写个活动策划、总结还算拿手,但是给图书提修改意见还是第一次。特别是拿到书稿时,才发现这居然是一笔一画写出来的手稿。”冶金学院研一学生田雷对记者说,直到半个月前,在学校官方微信上看到关于谢绪恺老师《高数笔谈》一书的推送,我才知道,一年前的手稿竟来自于一位90多岁高龄的老教授,还是一位在现代控制理论方面知名的学者。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无论我以后工作还是继续搞科研,谢老的《高数笔谈》都将作为一本实用的工具书伴随着我。
“数学原来可以这么有趣,”喻金同学是理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大三学生,是学习数学的高手,但对于谢老的书,也是赞不绝口,“看谢老的书,就像是和一位博学的长者在面对面地对话。”
在一年多时间里,谢老手写了500多页书稿,画了100多张图表,进行了10余次的面谈改稿、10余次的校稿和30余次的电话沟通,每一处细微的修改都要经过反复的推敲。
“在签订出版合同时,我曾建议谢老向离退休处申请出版经费资助,当时邸馗书记和徐峰助理非常支持。可谢老对我说:我写这本书不图名、不图利,他说不想申请离退休处的出版资助,不想占一个名额。我还提出要向他支付作者稿酬。他告诉我说如果出版这本书有作者稿酬,他会把所得稿酬用于购买这本书,再免费赠送给学生。”向阳告诉记者,最后,谢老自己承担了2.3万元的出版费用,放弃了作者稿酬。
4月14日下午,谢绪恺教授《高数笔谈》赠书仪式在东北大学汉卿会堂举行。他把用自己稿酬购买的图书赠给师生,并在扉页上庄重地写上东北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知行合一。”
现在,谢绪恺正秣马厉兵准备写《高数笔谈》的下篇《工数笔谈》,他一再嘱咐出版社副社长向阳,一定要多搜集大家对第一本书的意见,以便写第二本书时参考。
(本报记者 毕玉才 刘勇)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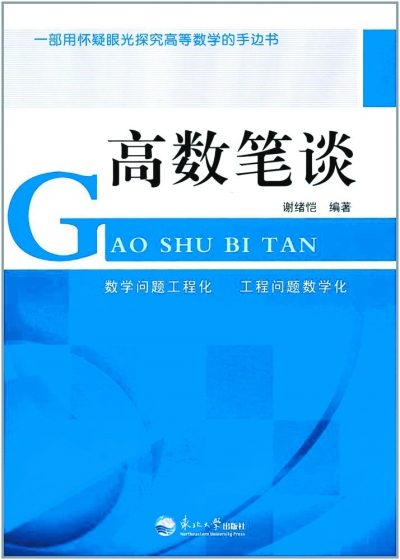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