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者说】
余冠英先生曾经非常谦虚地说:“我不是文学史家,我至多就是对古代文学,尤其是对先秦乃至汉魏六朝诗歌略知一二,不敢说是一个文学史家。”其实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说他是一位文学史家,一点也不为过。甚至可以说,余冠英还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史家。
简单地说,余冠英一生做了几件事。一是教书,一是学术研究,一是花了大量的精力做编辑工作。余先生这一生,在工作和生活中交往的朋友不胜枚举。说到他的朋友圈,大概可以分成几类,然而其实有很多是区别不开的。
第一类就是朋友。和余先生有君子之交的,朱自清是最密切的一个。余先生在1926年下半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他介绍了同宿舍名叫朱理治的经济系学生入党。朱理治先生是1907年生人,比余先生小一岁,晚一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北京的军阀抓共产党,风声很紧,余冠英和朱理治的左派倾向很明显,当时相当危险。余先生没办法,当天晚上就带着朱理治藏在朱自清先生家里,躲了一宿。其实,朱自清那个时候就知道他们俩是共产党员,但是在风声紧张的情况下,朱先生还是仗义施以援手,说明他们的关系不是兄弟胜似兄弟,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他的“朋友”,如果说有第二个,那就是吴组缃。余先生和吴组缃先生是怎么认识的呢?其实,一开始吴组缃的哥哥和余冠英是同学,两个人很要好。后来吴组缃又考到清华经济系,第二年转到文学系,两个人通过他哥哥认识,很谈得来,交情自然越来越深了。
第二类是老师或老师辈的人。余先生的老师辈,同时跟他也有很多交往的,俞平伯先生算一个。当时两人在一个组,一直一起工作,余先生是组长,俞平伯是组员,可谓订交一生、不离不弃。还有一位,是闻一多先生,他长期做清华和西南联大的中文系主任。有一件事,当年萧涤非先生在四川大学教书,因为国民党要让他加入,他不愿意,结果被国民党找茬解聘了。萧涤非孩子多,全家被困在四川,连吃饭都成问题。他写信给余先生,请余先生帮忙,想去西南联大教书,甚至说如果大学没有位置,教附中也行,只要孩子们不挨饿就可以了。余先生当时在西南联大教书,他拿着萧先生的信找到闻先生求情,闻先生不太了解萧先生,就问萧先生学问怎么样。余先生说,他是我大学同学,同一届,而且在清华足球队一起踢足球,交往很多,学问也非常好,所以我可以打保票。闻先生说,我信你,于是便给萧先生安排了一个教职,在中文系教书。可见,闻一多先生对余冠英先生非常信任。
闻先生孩子多,抗战期间生活困难,一度要靠给别人刻印章挣点钱以补贴家用。余先生当年家里人口少,情况要好些,所以曾经为了帮助闻先生,也按照闻先生刻章的润格,请他帮忙刻了一方闲章。可惜这枚印章在“文革”时被抄走,丢了。余先生曾经对我说:“很可惜,那是闻一多先生留给我的唯一纪念。”
1946年夏,闻先生遇害以后,在朱自清先生主持下,清华大学成立《闻一多全集》编辑委员会,余先生责无旁贷,做了四个具体做工作的编辑之一,投入很多精力积极参加当时的民主运动,而且不惧风险,从始至终参与了闻先生的后事料理,还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到对闻一多先生遗稿中唐诗研究部分的整理之中。《闻一多全集》之所以能够很快结集出版,当然也浸润着余先生的很多心血。
第三类是同学。萧涤非先生是其中之一,上面说过了。另外有一位是郝御风先生,余先生晚年经常念叨的几个好同学之一,后来是西北大学的教授,但专业不是古典文学。上学的时候他和余先生是好朋友,也是“唧唧”诗社的成员,后来搞文艺理论、文艺学研究。每次他来北京,或者是余先生去西安,两人都要见上一面,一起把酒言欢,回忆彼此的青涩年华。
第四类是同好。这一类里有的算是同学,有的算师兄或者师弟,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有三个,一个是浦江清,一个是李嘉言,一个是许惟遹。这三位都是教授,都英年早逝。这三个人和余先生是当年很谈得来的朋友,浦江清和李嘉言都是研究汉魏六朝的专家,浦江清曾是陈寅恪先生的助手,学问很好。
第五类算是师弟。他们都比余先生小几届,大概是在1933年到1935年入学或者毕业的同学,王瑶、季镇淮、范宁、何善周、曹禺、钱锺书、李长之、林庚,这些人进清华都比余先生晚。王瑶先生在抗战爆发前就考取了朱先生的研究生。我曾经去王瑶家拜访他,当时跟外公说,您能不能给我写个条子,我去王先生家不让我见怎么办。他说你就去,就说我让你去的就行了,并且告诉我王家住在哪儿。我去到王先生府上,夫人出来了,问我是谁。我说是余先生让我来的,他让我来找王先生。王师母就马上进去了,很快王瑶先生便走出来,和我聊。我说,我现在搞现代文学,想来跟您请教。王先生就说,你搞新文学,去问你外公啊,他比我还熟。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外公曾经搞过现代文学,搞过新文学。王瑶先生跟我亲口说,他自己最初搞新文学,第一批资料就是外公给他的。“他毕业之后,兴趣转向了,去搞中古文学。我那时候跟朱自清先生学中国文学,但我对新文学感兴趣了,所以余先生就把他当年买的所有的文集、诗集,以及他订的所有杂志,一股脑地都送给了我。”所以,王瑶先生客气地说:“我研究新文学还是跟你外公学的呢!”当然,这是玩笑话了,当不得真,但是这说明两个人当年的交往还是比较密切的。后来他们因为年事都已高了,又不是搞同一个专业的,所以交集也就越来越少。有一次,我陪余先生去吴组缃先生家做客,如果不是聊了一上午,已经很累了,说不定他和王瑶先生这两位老友也能见上一面呢。
第六类是师友。第一个是郑振铎,第二个是何其芳,第三个是沙汀。余先生和这三位在工作上接触很多,彼此交往也不少。有一段时间,他每周都到何其芳家里,去讨论问题,大概就是编写“中国文学史”的那段时间。
第七类是同事。同事呢,其实主要分两个时期,一个是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这一段,另一个是后来他在文学所那一段。早期那一段,有王力、陈梦家等人。余先生和陈梦家都爱写诗,他对陈梦家也很推崇。陈梦家相对年轻,年纪小,但是写的诗和后来他研究文字学,都非常好,余先生和他交往多一些。后来在文学所,同事就多了,有长辈的,比如王伯祥、孙楷第,比他年纪大;蔡仪、吴世昌和他年纪相仿;吴晓铃、唐弢,比他年轻几岁。另外,陈友琴和陈翔鹤,年纪也比余先生稍微大一点。
第八类应该叫学友。其实,周振甫先生应该属于这一类,晚年余先生和他走得比较频繁,也可以归到朋友那一类。学友里面有程千帆先生、王运熙先生,包括比他年轻的,像陈贻焮先生、廖仲安先生、徐放先生、林东海先生、李华先生。这些人和余先生联系都很多,相互之间有交流。本来,陈贻焮先生和廖仲安先生,尤其是李华先生,都是执弟子礼的,一定要叫余先生为老师,但是余先生却把他们当作朋友,走得也比较近。程千帆先生非常尊重余冠英先生,他经常给余先生写信,几乎每次写诗都会寄来,手书,请余先生指教。王运熙先生非常内敛,性格似乎不太外向,学问做得非常扎实,搞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也搞汉魏六朝研究,他每次有新书出版,都认真地寄送给余先生,公公正正地向余先生请益。他每次到北京来,都到余先生家里看望,两个人虽然话不多,但是那种高层次的交流,我觉得很感人。
第九类,就是有点亲戚关系的人。比如说,来往较多的赵朴初先生。赵朴初先生比余先生出生晚,是陈含光先生的外甥,即余先生大舅哥的外甥,论起来还比余先生晚一辈。还有一位,就是南京大学的卞孝萱先生。原来,卞孝萱先生和余先生到底有什么亲戚关系,我始终搞不明白。后来卞孝萱有一篇小短文,我一看就明白了,卞先生在文章里说得非常简单明了。他说:余先生是陈重庆先生的女婿,陈重庆是卞家的女婿。等于说,余先生的岳母姓卞,就是这种姻亲关系。卞孝萱先生早年来过余家,后来在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偶尔和大舅余绳武先生碰上,便在一起叙叙旧。
再有一类,算是同志。有两个接触较多的人,一个是胡乔木,一个是朱理治。余先生跟胡乔木是什么关系呢?胡乔木的哥哥也是余冠英的同学,后来通过他,胡乔木便认识了余先生。1949年以后,余先生和胡乔木建立了联系。
最后一类,就是他的学生。
(作者系余冠英外孙女婿)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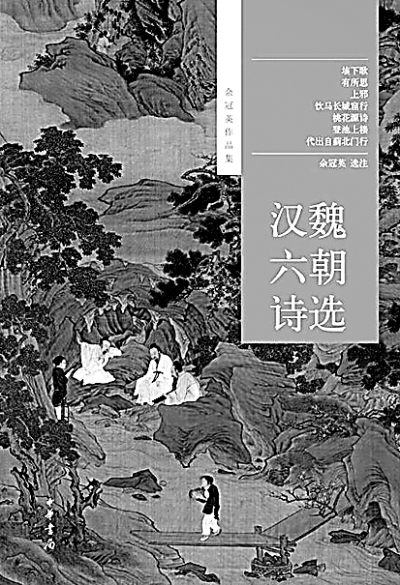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