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所记述的主要内容,乃庸常生活中的平凡事,然而沈复却能以诗化的情怀,体悟快意与欢乐,即使辗转流徙,也能感念生活之厚遇。
夫妇乃人伦之本。《浮生六记》即以《闺房记乐》开篇,而其诗化情怀、快意欢乐,在《闲情记趣》《浪游记快》《中山记历》中亦多有描述。沈复和其妻陈芸,乃姑表亲,两小无嫌猜。陈芸“生而颖慧,学语时,口授《琵琶行》,即能成诵”,四岁父亲去世,寡母幼弟,生活艰辛;既长,娴于女红,三口之家因而得以维持生计,后来得到《琵琶行》诗卷,“挨字而认,始识字”,并逐渐学会了作诗。隆冬深夜,陈芸藏暖粥小菜以款待送亲城外的沈复,遭亲友善意调笑而羞涩难当。小小情事,却成为两人日后时时谈及的佳话。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沈复与陈芸成亲。陈芸和善勤快,“初甚缄默,终日无怒容,与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处下以和,井井然未尝稍失”。两人精神相通,感情深厚,“自此耳鬓相磨,亲同形影,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沈复外出归来,“芸起相迎,握手未通片语,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觉耳中惺然一响,不知更有此身矣”;两人相处,年愈久而情愈密,“同行并坐,初犹避人,久则不以为意。芸或与人坐谈,见余至,必起立偏挪其身,余就而并焉,彼此皆不觉其所以然者,始以为惭,继成不期然而然”,且因而感叹:“独怪老年夫妇相视如仇者,不知何意?”
夫妇情感的深笃,在于他们有着共同的精神追求。结婚前,陈芸就喜欢作诗,或一联,或三四句,多未成篇,而沈复戏题为“锦囊佳句”。结婚后,闲暇之时,往往与沈复课书论古、品月评花,“自以为人间之乐,无过于此矣”。如论古文诗赋,极为简洁精到,情趣盎然,陈芸喜欢李白诗潇洒落拓,“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爱”,幼时以诵读白居易《琵琶行》而识字,堪称启蒙师。沈复调笑曰:“异哉!李太白是知己,白乐天是启蒙师,余适字‘三白’,为卿婿,卿与‘白’字何其有缘耶?”这样的生活,显然是精神相通者的人间清福。赏月我取轩,论及佛手与茉莉香气之区别,陈芸说:“佛手乃香中君子,只在有意无意间。茉莉是香中小人,故须借人之势,其香也如胁肩谄笑。”很是形象,又将二人之亲昵情态呈现出来。沈复与陈芸相亲相爱,立足于彼此的尊重与自尊,以平等心态,有约束,有界限,并非泯灭自我,因此才能保持爱情的久长与纯真。沈复甚至说出“来世卿当作男,我为女子相从”之语,可见其内心平等尊重以及对陈芸爱恋之深。
陈芸不重视外在物品、服饰的追求,不看重珠玉,而于破书残画极珍惜,“书之残缺不全者,必搜集分门,汇订成帙,统名之曰‘断简残编’;字画之破损者,必觅故纸粘补成幅,有破缺处,倩予全好而卷之,名曰‘弃余集赏’”,不惮烦倦,“于破笥烂卷中,偶获片纸可观者,如得异宝”。夫妇二人爱好相同,“一举一动,示之以色,无不头头是道”。
他们的生活颇俭朴,“瓜蔬鱼虾,一经芸手,便有意外味”,喜食乳腐、卤瓜,而且往往能够因陋就简,发现庸常生活中的诗意与欢乐。“贫士起居服食以及器皿房舍,宜省俭而雅洁,省俭之法曰‘就事论事’。”赁居萧爽楼,嫌其暗,遂以白纸糊墙壁;以旧竹帘代栏杆,用旧黑布条,连横竹裹缝之,“既可遮拦饰观,又不费钱”。沈复感慨曰:“以此推之,古人所谓竹头木屑皆有用,良有以也。”因陋就简,却不苟且,而是追求雅洁,追求生活中的诗意与快乐。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含而晓放,陈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堪称诗意生活的典范。赁居避暑之时,请邻翁购菊花,遍植小屋四周,欣然赏菊,希望能够拥有一方菜圃、数间茅屋,陈芸说:“君画我绣,以为持酒之需。布衣菜饭,可乐终身。”
情趣可以涵养精神。沈复是一位很有情趣之人,“见藐小微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处处留心,又能设身处地,通观物我,时时得到审美的享受。“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空。心之所向,则或千或百,果然鹤也。昂首观之,项为之强。又留蚊于素帐中,徐喷以烟,使其冲烟飞鸣,作青云白鹤观,果如鹤唳云端,怡然称快。”又蹲于土台之下,目光与土台相齐,“定神细视,以丛草为林,以虫蚁为兽,以土砾凸者为丘,凹者为壑,神游其中,怡然自得”。此种玄想,体现出淳朴的天真意趣,是纯真善良天性的展露。
沈复爱花成癖,喜欢栽种盆景,并拜盆景大师张兰坡为师,精剪枝养节之法,悟接花叠石之术。沈三白插花精妙,或亭亭玉立,或飞舞横斜,姿态神韵毕现。制作盆栽极其妙致,“点缀盆中花石,小景可以入画,大景可以入神”。在沈复的启迪下,陈芸鉴赏力亦颇不俗。夫妇二人同作一盆景,采拾山野有峦纹之石,用宜兴窑长方盆,堆叠岩峰,巉岩凹凸,若临江石矶,上植茑萝;盆一角用河泥种千瓣白萍,“至深秋,茑萝蔓延满山,如藤萝之悬石壁,花开正红色,白萍亦透水大放,红白相间。神游其中,如登蓬岛。置之檐下,与芸品题:此处亦设水阁,此处宜立茅亭,此处宜凿六字曰‘落花流水之间’,此可以居,此可以钓,此可以眺。胸中丘壑,若将移居者然”。乡居时,陈芸教人做活花屏:即以木条做成屏风架,将花盆置于屏风架中,植藤本香草,枝条绿叶攀缘而上,“多编数屏,随意遮拦,恍如绿阴满窗,透风蔽日,纡回曲折,随时可更,故曰活花屏”。
沈复喜游览,置身于大自然,将个体的生命体验融通宇宙,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得其天真意趣。七夕节,夫妇二人于我取轩赏月:“是夜,月色颇佳,俯视河中,波光如练,轻罗小扇,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状。”陈芸遂感喟:“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兴否?”闺中良友,款款深情。中秋节登沧浪亭赏月:“少焉,一轮明月已上林梢,渐觉风生袖底,月到波心,俗虑尘怀,爽然顿释。芸曰:‘今日之游乐矣!若驾一叶扁舟,往来亭下,不更快哉!’”沈复赴吴江,陈芸潜出深闺,相伴游太湖,“渐见风帆沙鸟,水天一色。芸曰:‘此即所谓太湖耶?今得见天地之宽,不虚此生矣!想闺中人有终身不能见此者!’闲话未及,风摇柳岸,已抵江城”;返程之时,“霞映桥红,烟笼柳暗,银蟾欲上,渔火满江矣”。沈复、陈芸约二三好友游苏州南园,经陈芸精心谋划,“择柳阴下团坐。先烹茗,饮毕,然后暖酒烹肴。是时,风和日丽,遍地黄金,青衫红袖,越阡度陌,蝶蜂乱飞,令人不饮自醉……游人见之,莫不羡为奇想”。
事实上,为生计所迫,沈复三十年来转徙各地幕府,“天下所未到者,蜀中、黔中与滇南耳”,虽备尝辛苦,但也得以壮游天下,领略江山胜境。沈复十五岁赴山阴、杭州从学,探奇寻幽,登高而眺望,“觉西湖如镜,杭城如丸,钱塘江如带,极目可数百里”。又与知己顾金鉴同游寒山、支硎山、鸡笼山,访明末徐枋隐居处:“村在两山夹道中。园依山而无石,老树多极纡回盘郁之势,亭榭窗栏,尽从朴素。竹篱茅舍,不愧隐者之居。中有皂荚亭,树大可两抱。”乾隆四十八年(1783),入维扬幕府,得以游金山、焦山以及扬州胜景;第二年又至海宁,游陈氏安澜园,许为园林第一;又观钱塘江潮,看弄潮儿搏击潮头,惊心动魄。后入徽州绩溪,得以游历火云洞天、山寺、仁里花果会。数年后,赴岭南经商,道经长江,经历小孤山、滕王阁等,最后翻越大庾岭,进入岭南,沈复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在岭南的游历、观感。
《浮生六记》以白描手法写平凡庸常的生活,能够以诗化的情怀,发现并体味生活的快意、夫妇之爱的深挚,是深于生活的体悟、从心田流淌出来者,淡雅简洁,而非单纯的文字技巧所能达到。日常生活平凡庸常,甚至波澜不惊,只有以诚挚之情对待人生,感念生活,发现其天真意趣,追求生活的本真,才能体悟生于太平盛世之欣然与快意。
(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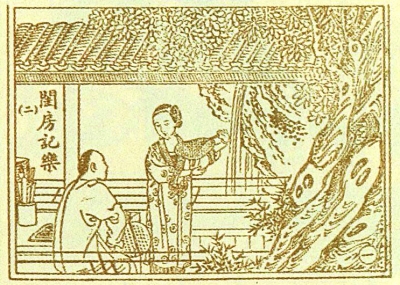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