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琰的诗集《西梅朵合塘》可以看作是个人生活的积累和对乡梓的思念。蓝天、草原、雪山、牛羊、白龙江、牧场、山壑、院子里的花椒树和柿子树等,串成了她的回忆,构成了她的诗歌景观。在王琰这里,诗歌是有味道、有色泽、有灵趣的。
比如,红土尕庄泥土里植物的味道、雨天里一只撞到电线的野鸡、秋天里成熟的柿子、溪边欢悦奔跑着的孩子、遥远的夏季牧场里星星一样的牛羊、骑马出诊的父亲和种菜养鸡的母亲,都是生命心灵的清澈记忆。
“村庄变小了/院子变小了/身高比往事矮。”(《旧家院》)语言思辨,意境扩大,把个人的生活带入了整体世界。而“故事性”,则是诗文本不可多得的内涵。有时一个小事件或者一个大的时间限量,都会像云游天空。诗境所展示的,是衡量记忆的尺度。“旧家院”并不旧,它打磨着往事、拉长了人生,是一种“天真性”到“感伤性”的转变。
“我用汉字写下三面环山的句子/方圆百里,没有人知道我自以为满腹经纶。”(《青春期》)一个人如同一只鸟,无法拒绝大地举起的树枝。那株树,是襁褓,或窝巢。大地是母性的喻象,带着阳光和水等生命物质,滋育记忆。水光清澈,生命如流。山色空蒙,灵魂如碑。王琰思考自由的世界,感受天地对生命的拥抱和护佑。
“天亮前许多纯净的事物正在变成天空的颜色/西梅朵合塘/花和鸟的故乡。”“草丛深处的嘎拉鸟被惊醒/慌慌张张飞上天去/一书生偶然路过草原/看见花儿草儿/都是散落的绝句。”(《西梅朵合塘》),王琰有意安排“书生”出现,从沉静的大地深处,或者说从历史的语境中,以一句惊奇,让原有的幽闭通过古诗意象,瞬间“敞亮”在现世的视域面前。
“牧羊人在风中/把整个白天/赶进了羊肚子。”(《措宁的春天》)辽阔的草原,牧羊人顶着大风牧放羊群的姿态,得以显现。诗眼在于,“整个白天”与“羊肚子”的对比,一个大,一个小。大的,骤然变小;小的,骤然变大。时间与空间没有界限,质与量没有界限,却能融为一体。这种时间的快速更迭、错动,在《出诊》里也有:“父亲和母亲都出诊的时候/白天,我们兄妹三个站在桌子上哭/夜晚,我们兄妹三个抱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哭/哭着哭着没有眼泪了/就长大了。”童年瞬间消逝,人刹那间长大。似平静,却难掩淡愁。王琰把电影里常运用的“时间蒙太奇”手法嵌入诗文本,自如地将诗境扩大或缩小。
观念世界是无尽的道途,各自寻找,各自行走。王琰对甘南大地有着独到的沟通和理解,对诗歌的理解也一样。她说:“诗歌在我的写作中,有着特别的重量,像是拉着辆上坡的板车,一步一步,一刻也不能松手。”
天地是整个的天地,记忆是片断的记忆。在写作的途路上,每一位诗人,都是“带根的流浪人”。问题是,应该如何不丢弃原本的角色,携带自己人生的“根”行走?胎记在身,籍贯在心,正确认知自己的“出处”最重要。王琰的诗歌,是以个人化的叙述,抵达理想的人生。字与句,句与段,是声响的组合、梦境的叠加、希望的垒筑。我读《西梅朵合塘》如同在开遍鲜花的湖畔,感受到天地浩大馨香的抚爱。
(黄恩鹏,作者系解放军艺术学院研究员)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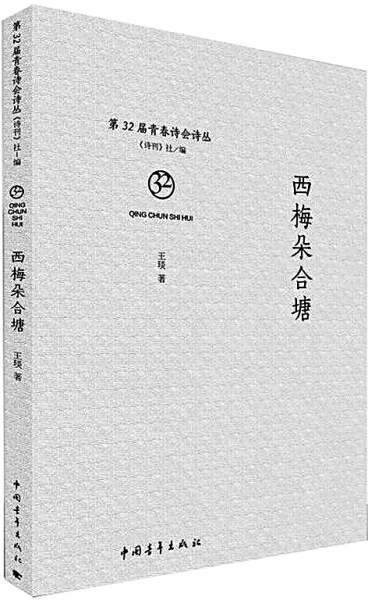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