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过眼】
20年前,诗人龚学敏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重走长征路,写出长达2500多行的抒情长诗《长征》。最近,修订后的《长征》全诗共分23章,保留了原有的主题和体例,着重诗歌艺术的提升,化繁为简,语言更凝练,意象更精粹,意境更高远,延展了多维阐释的可能性。
与过去甚至当下众多书写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给人干瘪乏味的印象不同,龚学敏诗意地触摸历史,他的《长征》是一部诗意充盈的现代抒情史诗,富有浓郁的抒情气息和鲜明的艺术特质,风格如一而又气象万千,不断打破读者的期待视野,刷新固有的阅读体验。
龚学敏的《长征》淡化叙事,着力抒情。在诗歌主体部分,历史事件的时间和动作是残缺甚至隐藏的,仅在“注释”部分补充相关信息。整部长诗是这样开篇的:“十月的细雨从战马瘦长的鬃上滑落在/瑞金的红字中央和云石山标语们清瘦的灰色衣衫上/一条叫作红军的崭新河流/在1934年深秋/被声音的子弹击中的天空/伸出新鲜的名字……”长征开始的时间像一个凝固的音符,动作是一条流动的河流,伴随这时间和动作的是细雨、瘦马、灰衫,是一种悲壮激昂的情绪,诗味隽永。《长征》携山水与历史同行,意象缤纷。龚学敏是从雪域山川中出走的诗人,山水已融入他的生命,即便面对宏大历史题材,他也常常以山水写历史,日月星辰、花草树木、山川鸟兽等自然意象纷纷进入《长征》,史诗的片段就像一幅幅古典山水画,有繁复,有留白,使原本沉重的历史鲜活起来,为诗歌增添了空灵俊逸之气。
作品还以侧笔展现历史风云,还原历史风貌。长征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涉及战略部署、正面战场等,《长征》以侧笔写之,注重细节,还原那些“人”以及“人们”在特定历史情境中丰富的快乐与痛苦。英雄们并不总是冲锋陷阵、一往无前的勇士形象,他们也有眼泪,有乡愁:“年,作为与家含义相同的汉字,/像天空中的雪花一样/落在英雄也一样会模糊的瞳孔中央……过年就是,异乡的雪花,开放在英雄乡愁默默的/孤独之中。”女性也不仅仅是革命文学中常见的“女汉子”,还有懂得歌声与爱情的思妇,在“走远路的人啊/竹子花开了”等诗行中,柔情婉约的女性特质得以还原。
以美的姿势雕刻历史的伤痕是《长征》的一大特色。诗人呈现的不是惨烈而是壮美:“单薄的浮桥/一次又一次地把惨白的骨头伸出来/触摸河底的淤泥。/在流动的水和行走的草鞋之间/清贫的浮桥/正在用母亲的胸怀/爱抚地看见死神的孩子。”这是长征以来的首次浴血大战,诗人展示的是战后的场景,那些消逝的生命是一种壮美的告别。重塑历史的过程中,作品抛却陈词,语言是崭新的。古典文学的辉煌曾经压低了现代人的天空,梅花是林和靖的,月亮总是李白的,现代写作者常有动辄罗列典故、堆砌辞藻的弊病,《长征》的语言运用推陈出新,几乎没有陈词滥调,比如在渡湘江这一段,没有看到湘君湘夫人潇湘妃子,完全是诗人自己独特的新鲜感受。此外,这首长诗也拒绝口号式的宣讲,布满了看似不符合逻辑的跳跃思维,细细思之却在情理之中。
诗歌如何观照历史?文学如何介入主流话语?这是一个长久的困惑,《长征》提供了一种可能。读《长征》,会发现漫漫征途中有崇高的英雄,有哀怨的思妇,有血雨腥风,也有草木、河流、星云……刚柔相济,诗味兴浓。读《长征》,会不由惊叹:原来历史的文学书写也可以如此丰满细腻、绚丽多姿。龚学敏执着于艺术的打磨,在机械复制时代依然追求“艺术品的光韵”,形成了独有的诗风。钟嵘在《诗品》中说:“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长征》因长征壮举的豪迈与诗人的英雄意识,展现出一种大格局、大气象,“风力”与“丹采”在此融合,实现“思之美”“力之美”“辞之美”的统一。
历史本身是丰富的,期待多样发掘。龚学敏在《长征》序言中说,长征是一个永远存在的诱惑,具有神秘性、穿透力和不可思议,充满无限的魔力,永远不会有人为它写出全部史诗,但每个人都有可能写出属于自己的《长征》。龚学敏的《长征》是别样的,是他独特生命体验中的长征。
(作者单位: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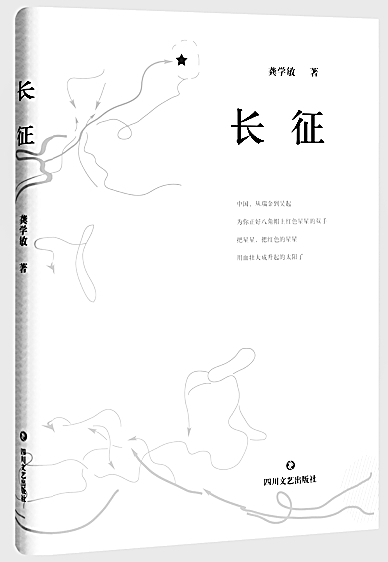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