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换一个视角看世界,你会发现意外的美丽,对艺术史的考察也是如此,换一种文化背景来探索中国艺术,或许可以将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呈现出来。德国汉学家雷德侯的《万物》就是这样一个标本。
在某个圣诞节,儿时的雷德侯得到一份特别的礼物,一组再普通不过的绘有中国风景的拼图游戏。只是,这款拼图游戏与雷德侯之前所见的都不同,图板没有弯曲的边缘线,也没有相关联之外形,而全都是简单的长方形;且每一片都没有固定的位置,如山峰可任意放进风景中间,楼阁板块可放于田野,山间也行,骑马的人物既可以面向山岗,当然也可以背向山岗。让这位小男孩感到奇妙的是视线,因为每块单独的图板上,地平线始终通过其中点纵横左右,尽管这些图板可以组合成无数形式,但从地平线看构图总是清晰明了。显然,对于已习惯西方透视原理的雷德侯来说,这种观看与组合方式让他惊喜不已。
你可能怎么也想不到,一副拼图游戏会成为一本关于民族文化的巨著的最初灵感。其实,拼图游戏与民族艺术的文化心理是相通的。雷德侯和他关于中国艺术的《万物》证明了这一点。对于拼图游戏的文化体验在这位德国汉学家的心灵深处打下烙印,并为他之后的研究道路埋下伏笔。20世纪60年代,雷德侯有机会与青铜器研究专家瓦迪姆·叶利赛耶夫一起合作,叶利赛耶夫是中国青铜文化的痴迷者,他将古代中国青铜器的纹饰划分为一百种独特母题,并将自己关于中国艺术的体会与雷德侯交流,他认为中国人首先规定基本要素,而后通过摆弄、拼合这些小部件,从而创造了艺术品。对青铜纹饰的拼图把玩,再次点燃了雷德侯关于研究中国文化的激情。
多年之后,当雷德侯成长为研究东亚艺术史的青年学者,之前关于拼图的文化体验经过学术砥砺,逐渐生成一种关于他者民族艺术的假设:这种复制、转移与置换的文化生产模式普遍地存在于中国艺术中。因为幼时所埋下的那颗种子,雷德侯共同用了二十年时光,分别在科隆、波恩、巴黎、台北、海德堡等地学习中国艺术、东亚艺术、汉学。从他1969年的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清代的篆书》、到1979年的专著《米芾与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再到1998年的《兰与石——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藏中国书画》,都是这粒种子成长的见证。功夫不负有心人,《万物》终于得以付梓并获得美国亚洲学会设立的列文森图书奖,雷德侯也因此获得巴尔赞奖,成为继贡布里希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艺术史家。
在《万物》中,作者采用了完全外在于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来对中国传统艺术的主要门类进行逐一考察,分析了中国艺术创造的工艺技术与制作方式,尝试揭示各门艺术之间的共创法则。这一考察几乎包括了中国古典艺术所有门类:青铜器、书法、绘画、瓷器和建筑,还包含民间工艺乃至印刷术等。《万物》的副标题是“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副标题几乎概括了作者对中国艺术研究的主要思想,即“模件化”理论则是他所提出的中国艺术创造范式和思维体制模式。通过对器物、文字、绘画、建筑等进行周详论证,他指出了中国艺术制品的批量生产特征与模件化特点。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有史以来,中国人创造了数量庞大的艺术品:公元前5世纪的一座墓葬出土了总重十吨的青铜器,公元前3世纪的秦始皇兵马俑以拥有七千武士而傲视天下,公元1世纪制造的漆盘编号多达数千,公元11世纪的木塔,由大约三万件分别加工的木构件建造而成,17—18世纪中国向西方出口了数以亿计的瓷器。这一切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都是因为中国人很早发明了以标准化的零件组装物品的生产体系。
在雷德侯的引导下,中国艺术被裂解成为巨大的拼图游戏,而人们在这场兴趣盎然的游戏中也悄悄地体验和接近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内在层面。从器具到普通的文化生产,雷德侯认为这种方式是根植在中国深层的文化和思维体系之中的,由此古代文人阶层的艺术表现形式也必然受到影响,所以他还提出“文人画之模件论”以讨论中国文人绘画的审美创造。比如历代范本的拓本临摹和审美标准的定制,书法模件化在于书写练习传承,符合规范文字便成为法帖,被奉为后代研习典范。《芥子园画传》也是典型的图式模件,画谱具有物质上的印刷和母题的标准化,是对文人画的各类构成元素较为完整的解析集册,单纯的母题元素及其特定的美好寓意,类似的梅兰竹菊、山林水石等即是如此。不过,雷德侯并没有将艺术中的创造性与规模化完全对立,而是推崇中国的“造化”即创新,在他看来,中国艺术的模件化并非现代的机械复制,大量生产的同时也保持了丰富的多样性。比如兵马俑的各部分的组合方式丰富多变,又如历史名画家通过《芥子园画传》来学习绘画的有的是。
就像作者小时候所得的那套中国拼图里的地平线,《万物》以模件化与大规模生产为基线发现了中国艺术模件化的奥秘,另辟蹊径展开对中国式思维乃至中国式社会文化的解读。“万物”这样一个书名是不是就很中国化呢,很容易让人想起老子的《道德经》。显然,雷德侯不仅仅意在揭示中国艺术的特色,更是想通过对中国艺术的分析,展现中国文化的某些本质特征吧,或许模件化生产以多种方式塑造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但艺术及其生产背后的中国社会体系和作者眼中观察到的中国文化生产的本质特征,值得人们思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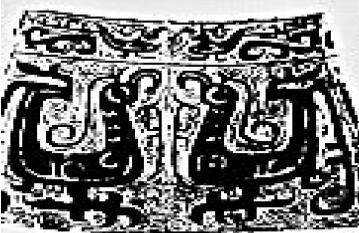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