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翘楚】
“彝族是一个充满诗的民族,数量惊人的创世史诗和古老民歌是吉狄马加诗歌创作的不竭源泉。那绵延不绝的群山,翱翔于群山之巅的雄鹰,缠着英雄结的男人,扭动腰肢的姑娘,鳞次栉比的瓦板房,月琴动人的吟唱,更为诗人打开了想象的翅膀。吉狄马加在《服务与奉献》中写道:如果作家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神性背景,那么苍茫的大小凉山就是我精神的家园……如果说我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我承认我是在延续着一种最古老的文明。——题记”
2016年6月,诗人吉狄马加收获了2016年度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颁奖仪式特意选择在吉狄马加的故乡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举行。
领奖时,吉狄马加难掩激动——
“感谢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评委会,你们的慷慨和大度不仅体现在对获奖者全部创作和思想的深刻把握,更重要的是你们从不拘泥于创作者的某一个局部,而是把他放在了一个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坐标高度。”
对于当今诗坛,吉狄马加有着自己的理解。在他刚开始写诗的年代,朦胧诗初兴,诗歌刊物的发行量达上百万份,一首诗可以让诗人家喻户晓。如今,虽然诗坛已经不复当年的繁盛,但他仍然认为“目前中国诗歌状态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宽松的文化氛围,自由的创作思想、表达内容和艺术手段,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诗之源
很多人认识吉狄马加,始于他的那一声呼喊,“啊,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自画像》)。这个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青年,在20世纪80年代一步入诗坛,就因诗中强烈的民族使命感、独属于彝人的丰富感情和色彩,引起众人的关注。然而,这个年轻诗人的目光并未囿于家乡山水,双脚站在大凉山土地上的他,视线投向的是远方的世界。
生于1961年的吉狄马加,可谓年少成名。当第一本诗集《初恋的歌》斩获中国第三届新诗(诗集)奖时,他年仅26岁,与其同时获奖的还有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北岛。从《星星》诗刊脱颖而出,到获得新诗(诗集)奖,再到组诗《自画像及其他》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诗歌奖一等奖,仅是数年间的事。
邓友梅初读吉狄马加的诗歌一时“失神忘我”,觉得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思绪和神韵在心中升腾”,他相信,这是只有彝人自己才能写出的诗歌。
从创作之初,吉狄马加就一直对一个问题苦苦求索:为什么很多民族人口很少,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却能产生世界级的作家?为此,他开始了大量阅读。在祖先的“这个世界”之外,他从外国文学宝库中找到了自己诗歌的“另一个世界”。
2001年,吉狄马加在《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发表文章《寻找另一种声音》,记录了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的世界级作家和作品。
普希金是吉狄马加的启蒙者,这位俄罗斯诗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良知给了他强烈的震撼,灌溉了他的诗人梦想。而非洲裔黑人作家和非洲本土黑人作家则给予他最多的心灵共振,改变了他对文学价值的判断。
也正是这个时候,吉狄马加开始真正关注彝族本土文化,意识到“每一个民族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不可替代的”。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更为他探究彝民族历史、神话和传说带来启示。
早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这部作品就深深触动了吉狄马加。当时,马尔克斯的作品在中国并不畅销,“我们完全是凭着一种直觉,开始关注马尔克斯等拉美作家的作品。”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常与他讨论拉丁美洲文学给彼此带来的新鲜感受,为这些作品超越地域局限,具有更广阔的全人类的视野感到震撼。
这群生活在边缘地带的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野心勃勃:“一定要把自己的文学标杆的制定放在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在中国”。
吉狄马加相信,一个诗人要真正成长,就必须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和养育。他将此概括为“纵的继承”和“横的移植”。“纵的继承”是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中国数千年所形成的伟大文学传统中吸取养分,“横的移植”就是向世界各国、各民族优秀文学学习、借鉴。
2008年10月,在“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吉狄马加在谈及对中国诗人写作产生深刻影响的外国诗人时,列举了一长串名字,诗人伊沙对此印象非常深刻。他一直觉得自己的记忆力好,却也想不出来一个需要补充的,不禁兴奋地对与会的女诗人潇潇说:吉狄马加的发言太好了,等于是代表几代中国诗人向这些伟大的名字致敬。
大目标让诗人有了大格局,广涉猎给诗歌增添了新厚度。20世纪90年代以后,吉狄马加的诗歌褪去青涩,不断拓展表达疆域,除了反复提到家乡的土地、彝族的同胞外,也逐步深化了他的人文情怀与世界主题。
诗人西川评价吉狄马加:“世界政治、文化、历史视野,在整个当代中国诗歌界都是罕见的”。面向世界成为这位彝族诗人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的、与众不同的特征。
立陶宛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称吉狄马加为民族诗人和世界公民。这个彝族诗人的笔深深地植根于养育了自己民族的大地的子宫中,而飞翔的翅膀却又越过大凉山脉,跨越国界、民族,创造属于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西川说:“对吉狄马加来说,家乡和远方毗邻而在。”
诗之韵
2010年3月,在“光明的歌者”艾青百年诞辰纪念诗歌朗诵会上,吉狄马加的演讲隽永深情——
“我爱戴并且由衷地敬仰艾青。从踏上诗歌的道路,我就一直是艾青的追随者,犹如在混沌中跟随一支火炬前进。”
艾青诗歌中特有的苦难与爱的气质,渗透进吉狄马加的诗歌底色中,艾青诗歌主题中对光明的渴望、对历史的关切、对真理的敬仰、对自由的礼赞,也在吉狄马加的诗歌中被反复吟唱。
钟情于精神,沉醉于使命,吉狄马加像艾青一样,手持火炬在诗歌王国中行走,他的诗歌不是朝向狭隘自我的窃窃私语,而是面向大众的黄钟大吕。
“今天许多诗人太关注自己眼皮底下的事,但对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类的命运却少有关注,这是我们必须改变的。”
诗人对诗人的认同,也是自己诗歌的标记。吉狄马加只热爱“诗歌疆域里的雄狮”。2016年3月,他重新研读俄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诗歌,并为其中的代表人物马雅可夫斯基写下400余行的长诗——《致马雅可夫斯基》。
这个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的伟大诗人继承了普希金的史诗传统,用如椽之笔见证了风起云涌的时代,掀起了一场席卷人们精神世界的抒情风暴。
“你的纪念碑高大巍峨——谁也无法将它毁灭/因为它的钢筋,将根植于人类精神的底座”
《致马雅可夫斯基》
对马雅可夫斯基进行诗歌式的追认,正是对其诗歌价值的认同与呼唤。长诗中,吉狄马加一并罗列了很多名字,将他们归为同一阵营,巴勃罗·聂鲁达、巴列霍、阿蒂拉、奈兹瓦尔、希克梅特、布洛涅夫斯基……这个来自东方的现代诗人遥望星河,追忆这些远去的同行者。
复苏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抒发恢弘壮阔、灼热的情感,将个人忧思与时代、历史、未来、世界连接在一起,正是吉狄马加的诗歌特质。他认为——
“诗歌应该具有见证的意义。它是诗人对思想、灵魂乃至宇宙万物的感受,它有时就如同一束光,而这束光能刺穿时间和历史的厚度。”
在吉狄马加看来,只有成为一个民族和时代的见证人,才能真正担当起这个民族和时代精神的诠释者。
法国诗人雅克·达拉斯将此描述为“以高山上雄鹰的视力,明察平原上的现代变化”。在吉狄马加的诗中,充满了对暴力与武装侵略的激愤,对歧视、排斥的反抗,对和平的强烈渴望,对人类平等的信仰,“对包括岩石、河流、山脉、云彩、空气、水、火、土地等所有的生命都有灵魂的确信。”(委内瑞拉学者、诗人布利塞尼奥·格雷罗语)
面对大时代、大事件,吉狄马加也从不失语。在他看来,诗歌的秘密在于“绝不回避现实,关注发展与未来”。永恒的主题和时代的命题相互碰撞,一首首具有精神高度、又能见证时代的经典之作孕育而生。
2010年青海玉树发生地震后,吉狄马加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他为藏族人民在面对苦难与离别时的独特信仰而深深感动。地震过去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晚上,吉狄马加走到玉树的嘉那嘛呢石经城。那里由25亿块嘛呢石堆放而成,是目前全世界人工堆放石头数量最多的石堆,每一块嘛呢石上都刻有六字箴言和经文。
吉狄马加一直记得那个夜晚——
“天空群星灿烂,很远处好像有白塔在慢慢上升,群山好像慢慢变得透明,野外的牦牛都像水晶一样。这个时候,我告诉自己,要写一首《嘉那嘛呢石上的星空》献给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人民,他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的爱和生命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
诗人回到帐篷用两个小时写了初稿,第二天四点就起床,又用了三个小时把这首诗完成。吉狄马加最爱在黎明的时候写诗,“大概在黎明的时候所有生命都在苏醒,在那样一个时候我会听见诗歌在内心召唤,我能真切地感受到,我需要找到更好的语言,在没有瞬间遗忘的时候把它写下来。”
2013年,长诗《我,雪豹……》问世,诗人叶延滨称它为吉狄马加的标志性作品。
雪豹,一种濒危的猫科动物,它们离群索居,远离人迹,孤傲地生活在雪线附近,是世界上最高海拔的象征。三江源是目前全世界雪豹分布最集中的地方,有五六千只。野生动物学家乔治·夏勒长期在青海追寻和考察雪豹的生存状况,吉狄马加与他有过多次接触,非常崇敬他的付出。
长诗也是对这位杰出动物学家的致敬。诗人借由雪豹的独白叩问存在的意义,表达了对自然的敬畏,对独立人格的坚守和对永恒的追问。
与《嘉那嘛呢石上的星空》一样,《我,雪豹……》是长期酝酿、迅速写就的作品。400余行的长诗,真正进入写作阶段,只用了四天半的时间。吉狄马加将这首诗歌的成功归功于强大的精神背景。“只有思想武装起来了,我们才能用笔去触摸事物的本质。”
对于诗坛上一些人为写诗而创作,沉湎于象牙塔里的遣词造句,偏执于技术形式的矫揉造作,吉狄马加并不赞同。他认为,诗歌永远不应失去对文化、社会、生存和人性的观照。相比那即逝的情绪、缥缈的玄思,他更看重厚重的思考、真诚的抒发。诗歌应超越一般性阅读和审美的范围,超越语言和修辞学方面固有的意义,作为一种精神象征引领人类从熙熙攘攘的世界走向一个更为高明的高地。它不应是“贵妇的宠物”,而应“写在天空和大地之间”。
诗之语
2015年,吉狄马加离开工作9年的青海,重新回到工作过11年的中国作协,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在面对众多媒体的采访时,吉狄马加很难回避一个问题,“如何平衡诗人与官员两种身份?”他并不掩饰对多次回答这个问题的无奈。于他而言,行政工作是他的职业,而写诗不是。“把写诗说成是一种职业,我认为是可笑的行为。”
在吉狄马加生活的高原和民族中,诗人是被神所选择的具有灵性的人,诗人更像是一个角色,是精神的代言人。通过充满灵性的写作,力求与自己的灵魂、现实乃至世间的万物进行深度对话。
“我接受有关我‘身份’的任何称谓,但我作为一个诗人的‘身份’,将穿越我生命的所有的生和全部的死。”
任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期间,吉狄马加没有放弃诗歌,并且创作了不少作品。他感慨,青海这片土地历史文化丰厚,给予他很多滋养,一方面提升了他的思想高度,一方面提供了思考问题的载体。“有机会到青海工作9年是我的幸运,这对我以后的创作都会有极大的影响。”
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的创办更证明了吉狄马加“两种身份”的互为补益。创办一个具有世界地位和国际品质的现代诗歌节一直是他的梦想。
早在1997年,吉狄马加就参加过哥伦比亚麦德林国际诗歌节,那是南美最大的国际诗歌节,同时也是目前国际上影响最大的诗歌节之一。诗歌节的盛况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立志回到中国后也要创办一个面向世界的诗歌节。“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聚会,能像一个诗歌节那样给人和生活带来希望和梦想。”
2007年,由吉狄马加倡导发起,在青海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支持下,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成功举办。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诗人会聚青海湖畔。第二年,参会诗人扩展到5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迄今为止,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已成功举办四届,国内外影响巨大,累计有近1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名诗人参加,被称为世界上第七大国际诗歌节。
在吉狄马加的努力下,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青海国际诗人帐篷圆桌会议、达基沙洛国际诗人之家写作计划、诺苏艺术馆暨国际诗人写作中心对话会议、三江源国际摄影节、世界山地纪录片节、青海国际水与生命音乐之旅以及青海国际唐卡艺术与文化遗产博览会已经成为中国进行国际文化交流和对话的重要途径。
吉狄马加注重诗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他的诗歌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文字,他多次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与国际文学界对话与交流。无论是其诗歌被翻译的外语语种的数量,还是其本人在国际诗坛上的亮相频次,在中国诗人中都非常突出。
有人认为,真正的诗不可翻译,诗就是在翻译过程中失去的那个部分。吉狄马加承认,诗歌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但当诗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时候,又会找到新的活力和生命。“人类对诗歌的翻译一天也未停止。”
诗之魂
“作为人类精神文化代言人的作家和诗人,我们必须标明自己的严正立场,并将身体力行地捍卫人类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身体力行”确实是吉狄马加区别于其他诗人的重要特质。
学者张清华评价吉狄马加:“在当代诗人中,也许像马加那样写出了优秀作品的诗人并不少见,但像他那样努力践行而且实现着诗歌中爱与光明、人类精神的融通交汇、生命尊严与文化多样性的维护的文化理想的诗人,却堪称凤毛麟角。”
在工业化社会消弭差异,消费时代瓦解信仰的今天,每年都有无数种语言在消失,有不少民族的文化都面临着难以传承的危险。面对这一现象,吉狄马加在多个场合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与关切。
长诗《我,雪豹……》中诗人借雪豹之口呐喊:“我的历史、价值体系以及独特的生活方式/是我在这个大千世界里/立足的根本所在,谁也不能代替!”
吉狄马加也如雪豹一样,以殉道者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忠诚守卫着受现代文明威胁的文化生命力。
2014年,吉狄马加获得姆基瓦人道主义大奖,被授予“世界性人民文化的卓越捍卫者”称号,他是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中国作家和诗人,也是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亚洲人。
法国诗人雅克·达拉斯称吉狄马加是一位既含蓄有致又勇于行动的诗人,只用不多的话语就能把诗的气息传向远方的诗人。这也许得益于他曾用脚步丈量过世界的很多角落,呼吸了来自不同地方的诗歌的空气。
吉狄马加曾在普希金生活过的地方进行虔诚的探访,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墓地守候了两小时;在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他专门抽时间与当时还在世的米洛拉德·帕维奇长谈了一个多小时;在智利,他来到巴勃罗·聂鲁达的墓地祭拜,听消失了的卡尔斯卡尔的印第安人族群的悲伤往事……
吉狄马加承认,真正保持一种属于自己的阅读和写作习惯,对一个经常出现在聚光灯下的人来说很难。但他需要通过阅读来提高自己的思想深度,以更高远的视角,去观望和回望自己民族的生活,审视自己民族的历史。
“真正的诗人,在离开这个喧嚣的世界之前,我想也只有诗能给他带来片刻的宁静。诗或许就是一种从生到死的庄严仪式。诗人在写作时,灵魂和心灵都是寂寞的。我也是。”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吉狄马加就离开了大凉山,在不同的地方书写着自己的人生故事。但故乡一直在他的心头萦绕。于他而言,彝族的酸菜汤、坨坨肉,终生难忘。“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诗人那样,一次次地回到自己的故乡,在那里寻找并获得永不枯竭的灵感。”他不无痛心地提到,大小凉山仍然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他会积极地参与到为故乡消除贫困的工作之中,尽自己的一份努力。
我写诗,是因为我的忧虑超过了我的欢乐。
我写诗,是因为我想分清什么是善,什么又是恶。
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哪怕是对一个小小的部落做深刻的理解,它也是会有人类性的,我对此深信不疑。
我写诗,是因为在现代文明和古老传统的反差中,我们灵魂的阵痛是任何一个所谓文明人永远无法体会得到的。
《一种声音——我的创作谈》
吉狄马加很喜欢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的一句诗:“要知道摇篮的吱嘎声和朴素的摇篮曲,还有蜜蜂和蜂房,要远远胜过刺刀和枪弹。”他觉得这说出了世界上所有诗人的心声。
虽然面临很多困难,但吉狄马加从来没有丧失过对诗歌的信心,他相信只有诗歌能让人们辨别出正确的方向,找到通往人类精神故乡的回归之路。“诗歌永远是黑暗中的火把,是为我们擦去眼泪和悲伤的那一双温柔的手。”
作为一个诗人,吉狄马加最大的梦想是在自己的创造力还没有枯竭之前,能写出一批可与大诗人比肩的史诗级作品。“我以为在任何时代,都会有人在倾听诗人的声音。”
2016年3月,在希腊雅典举行的希文版吉狄马加个人诗集签名发行仪式上,他面对记者的提问时说:“中国诗歌今天达到的高度,毫无悬念将高于其他的艺术门类。”他坚信:“诗歌的存在是人类迈向明天最真实的理由。”
吉狄马加,彝族,诗人、作家。1961年生于四川大凉山。1982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长,中国诗歌学会顾问。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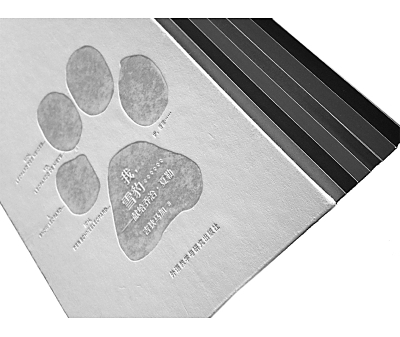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