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读书会】
嘉宾:
汝企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翻译家汝龙之子)
童道明(翻译家、戏剧评论家、剧作家)
刘文飞(翻译家、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
濮存昕(表演艺术家)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类文明是由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在他举例提到的一系列具有世界级影响的文艺大师名单中,俄罗斯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位列其中。
在我国爱好外国文学的读者心中,阅读契诃夫,最权威的中译本出自翻译家汝龙先生。汝龙之于契诃夫,正如傅雷之于巴尔扎克,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亚,草婴之于托尔斯泰。
2014年、2015年分别是契诃夫逝世110周年和诞辰155周年,文化界因此刚刚掀起过纪念这位巨匠的热潮;2016年,又恰逢汝龙先生百年诞辰,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由他翻译的《契诃夫小说全集》,奉献给喜爱契诃夫和汝龙的广大读者。
2016年6月末,一场主题为“永远的契诃夫、永远的汝龙”的文化沙龙在京举办,本期光明读书会整理刊载其中的精彩内容,期待通过各位专家的评述,再次走近这两位可亲可敬的大师。
永远的契诃夫
童道明:现在喜欢契诃夫的人越来越多,刚才休息的时候,有一个青年人走过来说,“童先生我喜欢契诃夫”,然后就走了,也没有告诉我他是哪个单位的。我到清华大学去,又有一个女生过来说,“童先生我喜欢契诃夫”,说完也走了。
为什么契诃夫会让人喜欢?作家爱伦堡1961年写了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如果没有契诃夫那样少有的善良,就写不出后来他所写出来的这些作品。”我以前读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十分在意,后来才觉得太有道理了。俄罗斯人在讲到契诃夫的时候都说他的善良,契诃夫是世界上第一个不写人和人冲突的作家,他的小说里面没有反面人物。
此外,在表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方面,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能超过契诃夫。契诃夫非常厉害,因为这个主题是现代的,而他用传统的方法写出来了。
刘文飞:我曾经去过契诃夫的故居,最感动的就是童先生说的契诃夫的善良。契诃夫是平民出身,有钱后买了一个大庄园,自己挑了最小的房间住,其他给父母、弟弟妹妹。他买了庄园不久,当地发生瘟疫,他就把家当做诊室,接待有传染病的人,分文不取。有学者说:“契诃夫在文学中从来不指点别人怎么生活,不开药方,但是在生活中,他到死都一直给别人看病。”契诃夫身上的善良是一种生产力,是他的生活方式。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善良的契诃夫》,后来去中国传媒大学做讲座谈契诃夫,就想把这篇文章复印出来给同学们,所以就去复印店。店主是一个三四十岁从河南来打工的人,他一边复印一边问:你写的?我说是。他说契诃夫我知道。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们课本上有。我说你记得哪篇?他一下说出三个:《万卡》《变色龙》《套中人》,如数家珍。一个作家在另外一种语言环境里有这么持久深刻的影响,甚至连靠打工谋生的人也知道他,我觉得这是文学的力量和契诃夫本身的力量。
据说濮存昕先生是出演契诃夫戏剧数量最多的中国演员。还有一个统计,在所有古典的戏剧家中,被演剧目最多的是莎士比亚,在现代剧作家当中,被演剧目最多的就是契诃夫。在小说、戏剧两个领域都同时有现代影响的作家,俄罗斯大概只有契诃夫。
四川美院有一个很有名的画家叫何多苓,一幅画可以卖几百万、上千万。他为契诃夫短篇小说《带阁楼的房子》画了40幅油画,出了一本书。诗人欧阳江河为此写了一个序言:“我们这代人中的不少人曾热爱过契诃夫的小说,这不是一般意义的喜爱,它有些类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整整一代人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般的喜爱,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把这个喜爱看作我们这代人的集体的青春病和内心情结,看作某种基本的人生感情,其中掺和着我们的梦想、初恋,以及为这种梦想、初恋的到来所准备的伟大的空虚,和由于这种梦想、初恋的缓慢地、悄悄地、几乎觉察不到的消逝所引发的麻木、难以言语的忧伤,我将这一切视为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青春遗产。”
濮存昕:俄罗斯文学对中国进步的影响是巨大的,是潜移默化的,是中国革命的一种人文准备。我们剧院的前辈,包括曹禺先生,都或多或少受益于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学为很多中国读者打开了认识世界、认识历史、认识生活、认识人本身的空间。
契诃夫是俄罗斯的文化财富,此外还有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等一大批名家。因为有这样的资源和传统,俄罗斯人觉得自己了不起,但是我们中国有一个开放的、学习的心态,我们对契诃夫、对托尔斯泰非常尊重。
契诃夫的作品写得非常有趣,非常漂亮,他给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重新认识生活,注意到其中流失的那些细节,和那些最有价值的人性的本质。
我小的时候就读过契诃夫的小说,很有帮助。在我还是一个很生涩的青年演员的时候,又开始演契诃夫的作品。童道明先生曾经夸赞我说,小濮这个人是被角色提升的。我能演契诃夫的作品,真的是非常受益。通过不断学习,我们这代演员慢慢成长起来。我看过六台不同版本的《樱桃园》,今天自己演,会有自己的直觉和角度,也就是创新。
永远的汝龙
汝企和:左克诚先生曾在文章中说:“汝龙,一个富有理想,以翻译工作为自己终身事业的人,一个默默无闻、淡泊谦虚,从来没有想过名与利的人,一个不知享受、毕生辛劳、忘我工作整整一辈子的人。汝龙一生翻译1000多万字的作品,比翻译家傅雷先生的译作还要多。尽管有如此丰厚的译作,但终生只在夜以继日工作的汝龙从未想过怎样介绍自己。他一生除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这两个社会头衔外,没有其他社会头衔,也没听说他得过什么社会荣誉。”这个评价简洁地勾画了我父亲的一生。
“几十年如一日”这几个字被人们用烂,然而真正在工作中做到这一点却谈何容易。父亲的翻译工作就正是这样。
他为了专心翻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辞去大学副教授和系主任的工作,之后的岁月基本都是在独立翻译的情况下度过的。当时的稿费相当优厚,他有太充分的条件可以享受,然而他却从未停止过辛勤的翻译工作。为了有更多时间进行翻译工作,他深居简出,社交活动少得不能再少,每天几乎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翻译。在一般人看来,他的生活实在是太单调了,没有周末,很少娱乐,几乎与世隔绝。翻译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也是他最大的乐趣。
父亲对自己的译作要求非常严格,每次出版前都要反反复复修改。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人们很少看到俄语书籍,所以当时父亲只能通过英语的译作转译契诃夫小说。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为了使译作更加忠实原著,发奋从头开始自学俄语,并买了俄语的契诃夫全集,此后他又将以前转译的几乎全部契诃夫作品重新翻译了一遍,这期间花费的心血更是其他人难以想象的。
为使译作更为生动,父亲十分注意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还没有现在这样的音响,他买了当时最好的美国进口的收唱机。每当父亲觉得没有翻译原作的激情时就停下笔,听几张激昂的古典音乐唱片,再回来翻译。
父亲经常关注各种美术展览,还以高价买了一套日本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里面收藏世界各国各个时期的名画,精美绝伦。他在翻译感到疲劳时就取出来翻阅。
父亲对翻译有他独特的理解,他经常说文学就是人学,是研究人的世界观的,是描绘人世间悲欢离合的,文学翻译不仅要耗费脑力,更要耗费感情,要想感动读者,就要加倍地投入感情,翻译出来的小说才能感人肺腑。
巴金先生是父亲终生的良师和最好的朋友。父亲常常对我讲起,当年选定做文学翻译工作之后,他曾经为选择莫泊桑还是契诃夫而感到困惑,是巴老的指点才使他翻译了契诃夫的几乎全部作品。巴金先生这样评价我父亲,“他热爱翻译,每天通宵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受虐待的恶劣条件下,仍然坚持翻译契诃夫全集,他让中国读者懂得热爱那位反对庸俗的俄罗斯作家。他为翻译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下半生,奉献了一切,甚至他的健康,他配得上翻译家这个称号。”
童道明:2008年,国家图书馆请我和一个导演一起去讲课,主持人说,五十年前我们在这里请汝龙先生讲契诃夫小说,今天我们请童道明先生在这里讲契诃夫戏剧,我听了以后非常激动。为什么呢?因为头一次感觉到一个接力棒的状态。不仅是我,我们这一拨后辈,包括刘文飞,都在进行着汝龙先生的事业。汝龙先生的翻译水平,我们很难企及。假如把汝龙先生的翻译跟后来人的翻译比,先生的译文绝对是最简洁的,因为契诃夫的风格就是简洁。但是如果译者没有一定的文字功力,就做不到汝龙先生那样的简洁。
我当年翻译《万尼亚舅舅》的时候,以为就我一个人翻译过这部作品。后来听人讲,汝龙先生也翻译过。我非常惊讶,因为这是契诃夫十八九岁的时候写的一个五万字的剧本,是他的处女作。假如汝龙先生连这篇都翻译过的话,他一定就把契诃夫的作品翻译遍了,非常了不起。
鲁迅当年写《祝中俄文字之交》时,文章里反复用这句话——“绍介进来,传播开去”,我认为可以用来概括汝龙先生的贡献,他老早做了这样一个工作,所以今天我们终于知道契诃夫作品是怎么传播开来的。
濮存昕:刚才汝企和先生讲,汝龙先生对他的工作充满了热爱。一边是俄罗斯文学,一边是中国文学,作为桥梁的翻译工作是很枯燥的、很艰难的,不热爱就无法做好。演员对自己的角色,对戏剧文学、对电影文学,也要充满热爱,才能更好地实现对艺术的认识、解释和演绎。契诃夫也好,汝龙先生也好,他们的认识能力、解释能力和表现能力,也是我们在重复的。
汝龙先生以中国人的眼光翻译契诃夫,用中国文学诠释俄罗斯文学,以他的才智进入了契诃夫的世界,很了不起。我相信他们俩人的在天之灵,是要握手、要交往的。他们的作品是永恒的,多少年之后读者一定会继续谈论契诃夫,继续谈论汝龙先生的作品。
刘文飞:今天一起纪念这两位先生,我想大家还是在传递一种东西。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写过一篇文章,说真正的诗人从来不是为自己写作,也不是为自己同时代的人写作,他真正的读者活在后代中间。我们经常说一个作家、一个戏剧家不朽,其实换一种说法就是要让后代人、后后代人也喜欢你,这个是艺术和文化的力量。
我国有一幅名画《富春山居图》,差点被烧毁,抢救回来以后一半在浙江,一半在台北故宫,后来展览时起名“山水合璧”。今天这个活动让我想起这幅画和这幅画带来的一个结果。首先这是一种拼接。汝龙先生生前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所以他的译本往往是人文社出版的。这次这套《契诃夫小说全集》又拿到人文社出版,我觉得这张图是和谐的。让我想起《富春山居图》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握手。因为这套书的出版,契诃夫和汝龙完成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握手。
(本报记者吴娜整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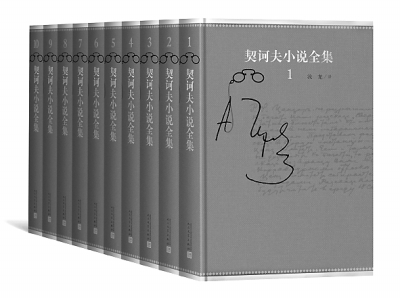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