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之苑】
目前短篇小说创作稳健、扎实,作家能够把握时代脉搏、历史流向,在对日常生活进行深度挖掘时,没有简单地从抽象概念出发,而是忠实于生活实践,借日常生活琐事及其矛盾冲突,来发掘社会内涵并展现时代风貌。对作家来说,不可能对日益物化的社会生活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异化现象熟视无睹,这势必会导致他们的创作思想、观念和方法的变化。面对现实,不少作家把笔触放在社会变化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上,力求从历史的联系中进行深入的艺术思考,探求问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变奏
随着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几次提速,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面临严峻挑战。现代所具有的高密度聚集、快节奏生活、商业化赢利等世俗特征,以及营造出的新式人际关系令人眼花缭乱。以短篇小说这种看似随意、实则精致的形式关注传统的现代境遇便成为一些作家自觉的创作选择。
邱华栋的《云柜》(《当代》2016年第1期)把云计算这一“互联网+”时代颇具代表性的事物介入生活中,艺术系教授孔东在与云计算系统服务商施雁翎的交往过程中发现:这个新型的女人把爱情、婚恋、生育等人生的云计算都计算好了。孔东作为一个传统的男人,面对这样新型的朋友关系、伙伴关系、男女关系,忽然感到了体内原始的反抗力量:好啊,你不是强势吗?你不是不再需要男人了吗?一切都云计算好了,还有什么意思?男人的脸往哪里搁?我就是不让你得逞。最终,这种没有母性、功利主义算计和强悍的女人在强大的传统男权视角中彻底溃败。施雁翎顺应市场经济成为典型的成功人士是必然结果,但她无法卸下传统意义上女性还担负着的育子责任。作者写出了当下一些人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现象。王海雪的《道具灯》(《山花》2016年第7期)对边缘人的书写抱有深沉之爱,“怪人”丑丑凭着精湛的刻灯手艺和执着的忍耐最终刻出照亮温斯堡之路的石灯,照亮了一群在平凡喧嚣的世界里执着于各自真理的畸零人。艾克拜尔·米吉提的《我的苏莱曼不见了》(《回族文学》2015年5期)里站在赛肯面前浑身惬意的苏莱曼,不再是为了妻儿、为了生活打工的苏莱曼了。生存的困境和精神的危机让人们逐渐意识到,人的存在不仅仅是物质性、经济性、社会性的存在,更是情感性、艺术性、精神性的存在。次仁罗布的《九眼石》(《民族文学》2016年第1期)考察生命之畏,既符合现实逻辑,也使对人生困境的揭示带上现代化特征。小说在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和生命质量时,尤其关注人的精神状态,这更是以“人”为核心的现代文化本质的体现。作家关注人们生活中那种最基础、最恒常、最原始的部分,其目的无非是要借此对现实做冷静的思考,以及在现实基础上探讨构建生存的空间。
作家们勇于直面现实,既对传统的道德伦理抱有依恋之情,又对现代变革热情接纳,并对之充满重铸的信心。虽说其中不乏揶揄与困惑,但更多的是沉思和期盼。在创作中,作家构建人类诗性生存理想之光的目标和使命并未消逝,由传统转入到现实,转向对当下生活的倾心观照。
孤独与希望的双向展示
在社会现实中人们热衷于追逐财富和地位,真诚和信任逐渐被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替代了,人与人之间诚挚的交流变得日益困难,孤独不可避免地成为短篇小说的一个普遍主题。小说的人物正是基于自己在现代社会孤立无援的状态感到无法忍受,而采用了非理性的方式宣泄,而作家本人试图用孤独的人物来证明社会的弊病是孤独肆意横行的本源。
马拉《阳台上的男孩》(《作品》2015年第12期)中写独居老人的孤独,城市儿童的孤独,邻居之间看似礼貌其实隔膜甚至防范的关系。老人买玩具表面看是为邻居孩子买的,其实更是独居老人对自己、孩子和天伦之乐的怀念。老人渴望和孩子相处,这种渴望却被恶意的揣测阻断,但又不能简单指责孩子父母心胸狭隘。小说最后,老人与孩子越过孩子父母的目光交流,使作品余韵不绝。晶达的《所有的灵魂最后都到河里去》(《草原》2016年第3期)中,缺少父爱、母爱的荷妮在姥爷去世后表现得既坚韧强大又孤独无助,溺于水底的她发现原来所有生命的魂都在这河底下,“死”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大家都平等地在一起。麦家的《畜生》(《十月》2016年第1期)中,木金被枪决后村里无人收尸,但牛围着尸体不肯走,直到把尸体架到牛背上,它们才肯走,不知是牛通人性,还是木金通畜性。一个小人物难以和同类进行正常交流沟通,只能在异类中寻找交流对象。小人物的这种与人为壑不仅直接造成了木金的悲剧,而且使个体对人类怀抱的美好信念也因心灵隔膜而发生动摇。作家对希望是朦胧的,但希望毕竟还是存在的。
无论过去、未来还是现在,孤独永远存在于人类的内心。作为人类基本处境之一的“孤独”,从来就不乏探讨者、追问者和玩味者。尤其是进入当下短篇小说世界里,孤独几乎成为一种主题景观,让人叹为观止。作家们孜孜不倦地描绘时代各具特色的孤独,或作为生存力量之明证,或凝聚作家对生命状态的沉思,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边哭泣一边追求,竭尽全力,为孤独探明来由,也为人类存在问路。
温情与粗粝的并置观察
考察这段时间问世的短篇小说,可以发现许多作家继续鼓起探索的勇气,着力创造新的写作范式,进入诗性的、审美的文学境界,特别是在对现实世界的感受和自身的写作中,立足当代的现实生活,寻找与现实最为贴近的表现形式。
钟求是的《星期二咖啡馆》(《人民文学》2016年第5期)线条简单、场景固定、叙述沉着,开场波澜不惊,从老人早起出发乘高铁到咖啡馆展开,结尾以一个女孩快乐的笑声收尾。然而,淡然开合之间却包含着意味深长的气象。老人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二都要到另一座城市的一间咖啡馆,与一位叫徐娟的服务生聊天,因为姑娘的眼睛里有他因车祸去世的儿子的眼角膜。现实社会充满着不确定性,儿子离世时身边留下的一本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向读者道出一个朴素的哲学道理:不管明天如何,也要以平和的态度把握日常生活的温情脉脉,感受生活中无处不在却往往被眼睛和心灵忽略掉的那些点点滴滴的幸福。扎西才让的《来自桑多镇的汉族男人》(《西藏文学》2016年第1期)自从这汉族男人来了之后,杨白玛的脸比以前嫩了,连说话时的声音也渗着蜂蜜的味道。他用拳头来说理,留下来的理由是不想离开那个漂亮的女人,他的不屈不挠让人感受到一种温暖。吕新的《烈日,亲戚》(《收获》2016年第2期)完整地概括了个人在特殊年代的生存际遇和那个寒意凛冽的年代里存在着的温暖的人性光芒。这也许是人在那个年代活下去的理由,它有效化解了“烈日”的强度,“亲戚”这个词,带有浓浓的暖意,即温情。陈毅达的《三色玫瑰》(《人民文学》2016年第5期),写出了当下中年夫妻的情感余音。时间的飓风吹了几十年,早把夫妻关系刮得没有留下什么浪漫,只剩下化石般的感情和遗址般简单的生活了。有人通过快递送来玫瑰,从7枝到20枝,送给谁,谁送的,查无结果,引发的家庭大战却让人看到了生活还是鲜艳美丽的。小说打开了底层社会世态人心的画卷,默默地传递爱的能量,这种美的体现使小说更加贴近生活。
范小青戏谑而讽刺的小说《死要面子活受罪》(《芒种》2016年第3期)则走了另外一个路子。孙子玩网游缺钱,向奶奶要钱,不想意外引出一场连锁的身份证明危机,讽刺的是所有事实都无法证明事实。这个令人尴尬的现实,被孙子写出来发到了网上,不想又引起一番追捧,孙子因此得了不少钱。整件事让人觉得既真实又荒唐。作者没有直接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抨击以及对底层人民的同情,更多的是通过思想上的讽刺来达到反思的效果。这种理性之美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对现实中那些荒蛮、丑陋、僵硬、扭曲的环境切身体验后的提炼与升华。
一个能表达时代精神的作家,不但能发现人类生活的缺陷和不完美,而且还能用审美理想观照甚至超越这缺陷和不完美,并把读者带进反思和升华的艺术氛围。这可能是当下短篇小说创作不同于以往的地方。现实是粗粝的,这既是一种物质意义上的说明和直白,也是精神上的一种暗喻。粗粝展示了现实的客观性,对人性和生命的价值形成了挤压甚至吞噬,消解着生活的诗意。在艺术中,展现和描绘现实的粗粝,可以为冲突的发生和激化创设心理逻辑、提供前进动力。如此,人本质中那些积极的因素,就能够迸发力量,显示生命的尊严和崇高。作家直面现实的艺术探求,方向是正确的。过去的苦难使人成熟起来,它必然成为今后创作的良好条件。衷心期望,作家在自己千辛万苦开拓出来的这条广阔道路上继续孜孜以求,奉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作者单位:哈尔滨学院)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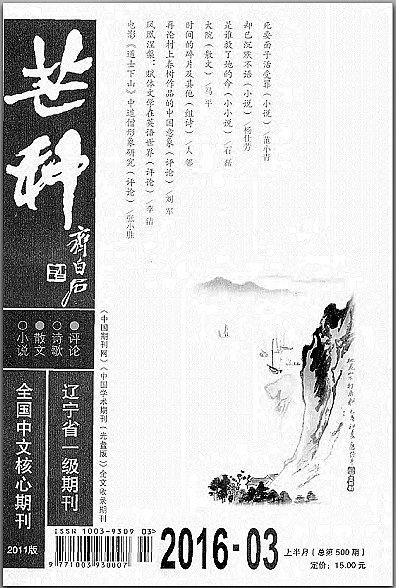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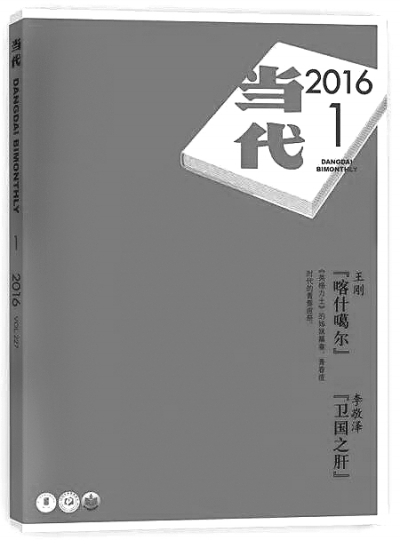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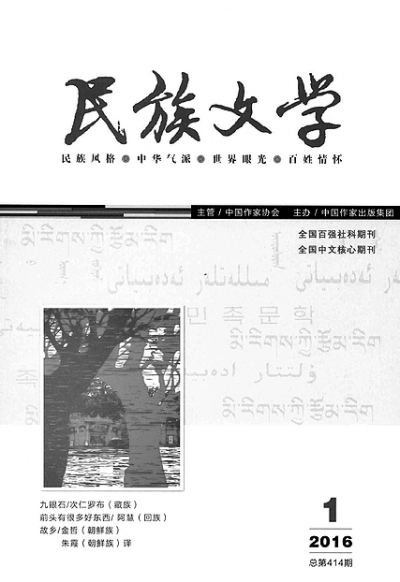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