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了夏晓虹教授的新作《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增订本),生出一些姊妹同道的感触。说起中国人的“妇女观”,近代以前两千年间,一直是以纲常礼教、男尊女卑的儒家伦理为主调,“男女平等”的新妇女观则是伴随近代女性解放运动才开始提倡流行的,而这一新旧的转换,始自晚清时期。一般史书所记“女性解放”的先声,往往标举晚清维新及新政时期一些“大男人”的倡说,如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等,而很少听到女性的声音。因而有人说,这是“男人的女性解放运动”,或是“男人代言”的女性解放运动。
20年前夏晓虹教授这本书首版时,书中列举的“晚清文人妇女观”的代表者也仅是两个“大男人”:一位是著名翻译家林纾,一位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也许是由于本书作者身为女性,对这种只讲“男性的妇女观”而没有女性声音有着本能的不满意,因此称之为“半成品”。这部“半成品”留给我们的疑问就是:在女性解放运动初兴、新妇女观形成之际,“女性解放”的主体——女性自身,真是无声的一群么?
手里这部新出的增订本给了我们新的答案,作者从历史尘埃的淹埋中,梳理挖掘出几位晚清知识女性,在女性解放运动初兴的舞台上率先发声,而且唱出不同于男声的女性心声,堪称“新妇女观”主旋律中一支独具音色的女高音!
一
“男女平等”是女性解放运动初期由男性率先提出的口号。甲午战争刺激下维新思潮兴起,一批维新志士、新潮男儿从“变法求强”目标出发,提出女性解放、男女平等、兴女学、废缠足、女性就业等观念。他们的主流言说逻辑是:占人口半数的女性一直是靠男人养活而只消耗财富的“食利之民”,要把她们转变为与男子一样创造财富的“生利之民”。这种男性视角的解放女性、男女平等的思路,固然很有从“国家富强”大局着眼的宏大目标,但若从女性角度来看,总有点被解放、被主宰、被需要、被平等的意味,而且缺少对女性本身命运、感受、利益、权力的眷顾。尽管如此,这些男性率先喊出“解放女性”的先声,毕竟为女性解放开启了一扇大门。此后女学、女报继之而起,沐浴新潮、接受新知的女子渐次成长,并很快登上社会舞台,开始行动,开始发声。
《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一书揭出的“女权”第一声,出自一位如今已少有人知的上海女子吴孟班。1901年4月,上海一位教会学校的女学生,年方十八九岁的吴孟班,写就一篇《拟上海女学会说》在《中外日报》刊出,并致信该报主编、维新人士汪康年。她认为身为女性“有改革之责,发言之权”。她指出:“中国之积弱由于女权之放失,女权之放失由于女学之式微。思之思之,痛之耻之!”她倡兴的“女学”,与当时男性“女学”论不同的是,不只是为了“强国”,还为了争取“女权”。她宣称:“女学者,全国文明之母;女权者,万权之元素。”所以她要站出来倡导这一“中国四千年以来开辟之举”!
在这篇论说中,满篇跳跃着“女权”二字,在当时可是个颇为显眼的新名词。据本书作者考证,虽然“男女平等”之说自维新时期已广为流传,但“女权”一词,却是到1900年6月《清议报》上刊出日本人所写《论女权之渐盛》一文,始为国人所知。而仅仅不到一年,吴孟班文中即已标举“女权”为关键词,且处处以“女权”自期自许,满篇洋溢着“女权”意识,故本书作者判其为“女权本土化”的先声。如本书作者所言,被历史淹没的小女子吴孟班,实为从维新时期女性被解放意味的“男女平等”,到20世纪初首倡“女权”、自主解放这一妇女观转折链条中的一个“关键人物”。
自吴孟班首倡“女权”之后,“男女平权”之说开始流行开来。1904年,天津女子吕碧城继续唱说“女权”,成为北方女界提倡“女权”的先声。这位出身书香仕宦之家但不愿受家庭压抑束缚的女子,刚过20岁便走出家庭寻求自立。她在《大公报》上发表诗文,提倡女学和女权。她倡办女学的目标,不只是使女子“助国家之公益”,还在于“激发个人之权利”。她呼吁女子要自我解放、独立自主:“须我女子痛除旧习,各自维新,人人有独立之思想,人人有自主之魄力。”她的呼声震动社会,遂在新派官绅协助下创办了北洋女子公学,她自任总教习,成为北方女界领袖和著名女教育家。
二
秋瑾的大名今人皆知。《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为我们展示了这位“女杰”是怎样由“家庭革命”走向“社会革命”的历程。她婚姻不谐,痛感旧家庭制度下女性是“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遂立志“欲以一身挽回数千年之积习,使吾国二万万女子脱此沉痛,以达其自由之目的。”为达此志向,她倡兴女学,并先行“家庭革命”,以中年之妇而离家弃夫、放下一双小儿女,单身赴日求学。面对外敌环伺、亡国灭种的危局,她鄙视软弱无能、苟且偷生的一众男子,她自号“鉴湖女侠”“汉侠女儿”“竞雄”,宣称“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起而与男子并肩革命、策动起义,直至慷慨就义,谱写了一曲傲视群雄、名彪史册的现代“女侠”之歌。
比秋瑾稍后到日本留学的女子何震,创立“女子复权会”,创办《天义报》,宣传鼓动“女界革命”。她主张“天赋之权,男女所同。”要“尽女子对于世界之天职,力挽数千载重男轻女之风。”她高张“实行男女绝对平等”的旗帜,她批判男女不平权的“妻从夫姓”习俗,并率先实行父姓加母姓的“双姓”,直至“废姓”,引时人注目。虽其言论或有偏激,其主张也引起争议,但她从制度设计和社会理想上推进“女界革命”的探索,正如本书作者所赞,具有“思想深度与理想光辉”。
《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举出的几位最先发声倡导女权的晚清知识女性,其言其行震动当时男权当道的社会,或被称为“奇女子”,或被誉为“女豪杰”,她们高亢的“女权”第一声,穿越百年,余响至今,而今日女性也莫不受其泽惠。一般所称近代“文人”,多指男性,说到女性时则往往用“女作家”“女诗人”“知识女性”等“差别性”称谓。本书则将女性也纳入“文人”名下,也算是“男女平权”的历史回声吧。
作者自述:夏晓虹
《晚清文人妇女观》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是历时最久的一部著作,此书对我也具有特别的意义。
记忆仍清晰如昨日:1994年7月下旬,其时尚任职于《北京日报》的孙郁君向我约稿,因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转年9月初将在北京召开,他有意主编一套“女性文化书系”,邀我加盟。1995年春季的研究生选修课,我报的题目就是“近代文人妇女观”。由此催生出本书的前两章——“晚清妇女生活中的新因素”与“晚清妇女思想中的新因素”。在课程的进行与孙郁的催促声中,到5月7日,书稿好歹凑出了四章,字数约莫有了十五万出头,便急忙交稿。而我的抱愧更在于,送出的书稿只是半成品,个案研究仅得两家,且均为男性,显得零落而不成阵势。
而以此书为开端,我在近代女性研究的道路上也越走越远,且兴致日高。2004年印行的《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以及近日出版的《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便都是这本半成品的嗣响。而歉疚之情与补阙之愿也一直不曾远去。利用各种约稿与会议的机会,我先后完成了关于秋瑾、何震、吴孟班、金天翮与吕碧城各文。至于其他两章又是另一种情形。限于篇幅与论题,文笔不免局促,观照点也相对单一。因此,现在这部增订本尽管比最初版本添加了五章又一节(第一章第五节“婚姻自由”为新增),却仍然留下了遗憾。
其实,“晚清文人妇女观”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个案的选择可以不断增加。本次的增补重点是在女性人物上着力。不过,初编计划内的康有为仍然未能现身,即使一直有意纳入的梁启超也失于机缘,无由在列。而种种不完满,又给予笔者新的希望与动力,一如初版《晚清文人妇女观》的缺憾,反而激发了此研究课题的日渐深入与扩大。
(李长莉,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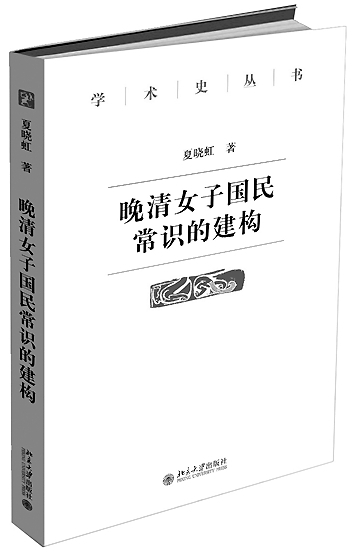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