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应镠先生(1916-1994)是20世纪“上海十大史学家”①之。掐指算来,已仙逝20多年。人到老年常念旧。这些年来,我经常想到他,不时讲到他。讲到他对我国宋史研究的特殊贡献,讲到他的为人与治学之道。想到在他引领下工作的那些日子,想到他留给我的一些不理解或不甚理解的疑问。
一
我有幸认识程应镠先生,是因为参加编审《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大辞典》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历史学界的一项重大工程,由当时资格最老、最具感召力的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担任总主编,著名历史学者多半参与其中,担任分卷主编或编委。
据介绍,这部大辞典“是迄今为止新中国编纂出版的第一部由国家组织编写的特大型历史专科辞典”,号称“当今世界上最全面、最权威的中国历史百科全书”。《大辞典》有14个分卷,《宋史卷》的主编是邓广铭、程应镠两位先生。因邓先生忙于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辽宋西夏金史分册,《大辞典·宋史卷》由程先生全权负责。
我初次见到程先生,是在上海桂林路100号——现在的上海师大徐汇校区。1982年春,应程先生之约,我与徐规先生等前辈学者以及朱瑞熙、王曾瑜等朋辈先进一同来到这里,在程先生主持下,编审《大辞典·宋史卷》。
2012年秋,程先生的高足虞云国教授邀请我到上海师大访问,我当即欣然应允。因为这个“书香惹人醉,花落梦里回”的地方,给我留下了不少美好的记忆和若干值得回味的往事。
30年后,这里旧貌换新颜,装修整饬一新,让我几乎无法辨认。经云国兄提示,我才发现早餐饭厅就是从前的食堂,徐规先生和我等当年在此处拿着饭碗,和同学们一道,依次站立,排队打饭,然后回宿舍就餐。
下榻的宾馆正是当年我们寄宿的招待所。当年,外地来的7位学人在此住宿。两人一间屋,兼做办公室。刚从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师大任教的元史研究生,后来大名鼎鼎的萧功秦教授和我同住一室。徐规、颜克述两先生与我们毗邻而居。
徐规先生是温州平阳人,每餐必饮老白干,工作时总要打开收音机听越剧。越剧声音开得很大,并不影响徐先生工作。他眼力非凡,酒后头脑反而特别清醒,总能迅速发现我们的错误,并快速一一予以纠正。
此刻,我仿佛回到30年前的时光,想得最多的、同云国兄谈得最多的无疑是我们的主编程应镠先生。
程先生给我的直觉印象有二:一是体格格外健旺。他身材高大,目光炯炯,有锻炼身体的好习惯。每天清早都看到他穿着当时很时尚的运动鞋,在学校大操场里跑步,他年轻时似乎是个体育运动爱好者。二是组织能力超群。他非常讲求效益,从不开会闲谈,主要依靠曾维华②、虞云国两位助手开展工作。行政事务一概由曾维华负责,编审事务则通过其学术助手虞云国上传下达。
任务一清二楚,工作井井有条,我们几乎没有任何事情和问题需要直接找程先生。
程先生事业心极强,为集中精力,全力以赴编撰《大辞典》,他辞去校内一切事务,一人专心致志在家里办公。我们不便打扰,只是晚饭后偶尔到他家短暂拜望。先生颇有长者之风,待人诚恳,乐于助人,有求必应。
当时,我刚调离西藏,到四川师大任教,想趁机观摩上海师大历史系的课堂教学。程先生立即安排,让我听他的大弟子李培栋老师讲课。李老师讲五代十国,讲得十分精彩,至今记忆犹新,给我启发很大。
当年从事国家特大重点科研项目,条件之艰苦,生活之简朴,在今天难以想象。参与者无任何好处,每人每天仅有生活补助费3角6分钱。或许是为了弥补一下吧,离开上海前,程先生出资40元,请我们在徐家汇衡山饭店吃了一顿淮扬菜,算是“奢侈”了一回。应邀作陪的有早年著有《宋金战争史略》一书的沈起炜老先生。其中一道鲜虾仁炒豌豆,味道异常鲜美,始终让人回味。
在程先生的精心组织和辛劳工作下,《大辞典·宋史卷》于1984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印行,在各断代分卷中是最早出版的。这本辞书缺点虽然相当明显,正如程先生所说:最大的缺点是“所收词目远远不能符合读旧史时的需要”。③然而,直至本世纪初仍是宋史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
二
程先生对宋史研究的特殊贡献远不止此,主要在于以下两大方面——
其一,创建上海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将它建设成为我国宋史研究的重镇。
《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两大部书标校本是由上海师大④组织整理的,其主持者主要是程先生。这两大部书标校本问世,在当年是宋史研究者的两大福音。程先生有远见、抱负大,他决心在此基础上迈出大步伐。他说:“宋代史料整理的工作,是大量的,没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不认真组织人力,是整理不完的。”⑤
为此,程先生网罗了不少人才,于是上海师大古籍所在20世纪80年代是宋史研究者人数最多、整体实力最强的单位,足以同当时以研究人才少而精著称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相媲美。
后来,宋史研究基地增多,但上海师大古籍所始终是我国最具实力的宋史研究重镇之一。2014年,在杭州宋史年会上,会员海选理事,上海师大当选理事者竟多达五位,成为一大“怪事”。其实怪事不怪,上海师大宋史研究实力之强为学界同行所公认。营造这方宋史研究重镇,程应镠先生厥功至伟。难怪每当提到或来到上海师大,我和同行们一样,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到程先生。
其二,主持宋史研究会秘书处,将它建设成为“会员之家”。
程先生是宋史研究会的发起人和筹备组成员之一,并负责具体筹备工作。1980年10月,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及第一届年会在上海师大召开,由程先生主办。程先生出任第一任秘书长,稍后又任副会长兼秘书长。第一本宋史年会论文集由邓广铭先生领衔主编,程先生具体操持。《宋史研究通讯》由程先生创办,并亲笔题写刊名。研究会在民政部注册、年审等相当琐细的事务,程先生都操心不少。研究会的规制最初是在程先生参与下制订、形成的。在知名学者当中,程先生是一位难得的办事能力极强的干才。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当年的宋史研究会,如果说会长邓先生是“董事长”,那么程先生便是“总经理”。他为草创时期的研究会做了许多实事。当年,我到上海或路过上海,总是选择投宿桂林路100号,连招待所工作人员也会用欢迎的口气说一声“又来了”。因为我们的研究会秘书处就设在这里,这里熟人最多,来到这里多少有些回家的感觉。如果程先生健在,秘书处只怕应当始终设在上海,不会迁往保定。
程应镠先生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爱惜人才,提携后进,并自有其特点。我在上海师大编审《大辞典》期间,程先生不仅做主引进了萧功秦等青年才俊,而且千方百计将朱瑞熙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调到上海师大,并准备让贤。
程先生与朱瑞熙既无师生情谊,从前又无交集,程先生看重的是他的学识。我后来致信程先生,将他盛赞为“韩荆州”,并非溢美之词。程先生爱才,具有兼容性,不拘一格。微观考据型、宏观探索型、微观宏观研究复合型三种人才,一概受到他的赏识和提携。经他建议留校的俞宗宪、刘昶、虞云国三位爱徒,照我看来,大体属于上述三种不同类型的人才。
俞宗宪属于第一种——微观考据型。
我在上海师大期间,程先生指导的六位我国第一批古籍整理研究专业硕士生刚毕业不久。他们的毕业论文,我有幸拜读。其中以俞宗宪的论文《宋代职官品阶制度研究》考论最为精详,受到邓广铭先生等史学名家称赞,很快被《文史》杂志采用,刊登在第21辑上。
其他五篇论文质量都很不错,如李伟国有关宋代内库的探索、朱杰人有关苏舜钦的研究等等。至今我还记得,据朱杰人考证,苏舜钦的祖籍不是梓州铜山县(今四川德阳市中江县广福镇),而是绵州盐泉县(今四川绵阳市游仙区玉河镇)。此说虽然未获广泛认同,但我个人认为,可信度最高。
程先生指导的这批硕士生水平这么高,一是由于在校内校外广聘名师授课,如千里迢迢从兰州请来我母校的郭晋稀老师讲音韵学。二是特别重视实习课,让每位研究生点校一本宋人笔记,如李伟国校欧阳修《归田录》、俞宗宪点苏辙《龙川略志·龙川别志》、朱杰人整理王铚《默记》等等,后来均由中华书局出版,收入唐宋史料笔记丛刊。足见程先生对基本功何等看重。
刘昶属于第二种——宏观探索型。来上海师大前,我就知道他的大名。刘昶读本科时所作《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一文很有见地,经程先生认可,先在《上海师大学报》1980年第4期上发表,后在《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全文重登。
文章开篇敏锐地提出:“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这样漫长?历史,特别是现实,把这个严峻的课题摆在人们的面前,迫切地要求回答。”于是,在史学界引发一场相当热烈的再讨论。我老来记忆力差,但始终记住文章里的这句话:“六道轮回,出路何在?”因我与萧功秦同住一室,我亲眼看到,刘昶与程先生门下的其他在读硕士生以及成长为中国中古史及宗教学专家的严耀中教授等不时来找萧功秦谈论学问。这或许可以称之为学术小沙龙。这些青年才俊思想如此活跃,固然是时代使然,只怕与程先生的倡导也不无关系。
虞云国属于第三种——微观宏观研究复合型。刚到上海师大,就听说虞云国虽然年纪轻轻,但很不简单。1980年秋,他是唯一列席宋史研究会第一届年会的在读本科生,提交年会的论文《从海上之盟到绍兴和议期间的兵变》占有史料相当全面,被邓广铭先生收入他主编的年会论文集。
编审《大辞典·宋史卷》期间,虞云国作为程应镠先生的学术助手,态度异常严肃认真,搜寻核查考索之功很强。起初,我仅仅认为虞云国与俞宗宪相似,是个能成大器的历史文献学好苗子。离开上海前,他以其新近发表的大作《经典作家对拿破仑的不同评价及其原因和启示》相赠。论文理论性强,表现出相当高的抽象思维能力,与刘昶在伯仲之间。我才恍然大悟,虞云国是位不可多得的复合型人才。
三
或许因为程应镠先生有1957年的遭遇,在很长时间里,我对程先生的身世与阅历知之甚少。在我心目中,仅仅将程先生定位为一位学风严谨的古籍整理专家,甚至误以为他是个象牙塔里的迂夫子,因而留下了一些疑问。最大的疑问是,与微观考据型人才相比,程先生为什么更赏识宏观探索型与复合型人才?据说他还特别欣赏擅长理论思维的赵俪生老师的高足葛金芳师弟,并曾给予其很大支持。后来,读过《程应镠自述》及虞云国所著《程应镠评传》等传记资料,才发现我从前的定位大谬不然,于是疑问迎刃而解。
程应镠先生青年时代的经历跌宕起伏,丰富多彩,颇具传奇性。与其同龄人赵俪生老师性格虽然不尽相同,但经历则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青年时代的程、赵二位先生都属于理想主义者。
20世纪30年代,程应镠先生在北平读大学时,酷好写诗著文,参加北方左联,创办文学刊物。在民族危亡关头,投身“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奔赴抗战前线,在八路军115师当过战地记者,到过宝塔山下的延安。
稍后,程先生又跟随奉命潜伏的同学、中共党员、有“红色卧底”之称的赵荣声来到洛阳,相继在第一战区长官卫立煌司令部、13军汤恩伯部任上校秘书。抗战胜利后,在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中,他壮怀激烈,加入民盟,被特务盯梢,上了黑名单。
程先生绝非读死书的书呆子,他志向高远,写下“斗争文字疾风雷”“报国谁知白首心”等诗句以言志。青年时代的他是令人崇敬的战士、斗士和勇士。
程先生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西南联大等名校,迭经沈从文、闻一多等文史名家指点,其治学主张与方法在当时相当前卫,至今仍很有价值。按照我的粗浅领会,其主要精神或可概括为“三个交融结合”。程先生反对食古不化,主张古与今交融结合: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他强调史料不等于史学,主张史与论交融结合:重视理论,推崇会通,既追求高屋建瓴,又鄙弃不根之论。他认为史无文则不行,主张文与史交融结合:文笔简练明快,生动流畅。
程先生的《南北朝史话》《范仲淹新传》和《司马光新传》等史学论著即是其治学主张与方法的具体体现。依我看来,程先生如果1957年不被错划,是不会主要从事古籍整理的,必有更多更好更加厚重的史学论著问世,像《南北朝史话》一样,令专家交口称赞,让读者齐声叫好。
1988年在南京大学召开的社会史研讨会上,我意外见到程先生的公子程念祺,倍感亲切。拜读他提交研讨会的论文,我连连赞叹:“颇有家父之风。”
程门弟子众多,其中我最熟悉的是有上山下乡经历的虞云国。当年,徐规先生和我等曾在程先生近前,夸奖过他。程先生谦逊地说:“虞云国不是我程应镠培养出来的,而是社会造就的,他进大学时水平已经很不错。”
其实,虞云国走上研究宋史之路缘于程先生引领,他发表的第一篇宋史论文《从海上之盟到绍兴和议期间的兵变》经程先生点拨并厘正。他出版的第一部宋史论著《宋代台谏制度研究》是以程先生指导的硕士论文为基础的。程先生对他有不少重要指教,如不要堆砌史料:“占有史料要全面,但用一条材料能说明的问题,不要再用第二条。”又如:“写文章要让人爱看,要干净简练,一句话能说清的,不必说第二句。”⑥
虞云国这些年来的众多史学论著,既体现汉学的功力,又具有宋学的眼光,见解不同凡响,文笔生动优雅,深得程先生真传。我拜读他所赠《水浒乱弹》《敬畏历史》等书,脑海里总闪现出程先生的影子。虞云国《细说宋朝》一书不仅博得学界好评,而且在社会上流传,在我个人看来,实可称之为《南北朝史话》升级版。程门学术后继有人,程先生当含笑九泉。
据说,文化有京派与海派之分。对两者一概贬斥者有之,如鲁迅:“在京者近官,近海者近商”“‘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一概肯定者也有之,如曹聚仁:“京派笃旧,海派骛新,各有所长。”⑦更为普遍的是扬京抑海,视京派为正宗,视海派为异类。在某些方言如四川话中,“海派”属于贬义词。其实广义的海派文化,其内涵和外延都具有不确定性,是个相当含糊的概念。
至于海派史学一说,只怕更难成立。“识大而不遗细,泛览而会其通”的吕思勉先生,“纵论古今,横说中外”的周谷城先生,较早用历史唯物论探索我国古代史的李亚农先生,力图“以史经世”的陈旭麓先生,同属当代“上海十大史学家”,但他们的学术追求和治学风格各不相同,差异性远远大于同一性。如果一定要将程应镠先生视为海派史学家,那么我坚定地认为:海派不“海”。程先生治学,标新不立异,严谨而笃实,不另类,很正宗。我怀念程先生这位对我国宋史研究有特殊贡献的长者。
2016年3月于海南琼海
①姜义华主编:《史魂:上海十大史学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
②本世纪初,我到上海师大时,曾维华兄刚从科研处处长岗位上退下,他专程前来与我会面,共同述说着当年的往事趣事。
③《编辑〈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卮言》,《程应镠史学文存·流金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22页。
④“文革”期间,华东师大曾与上海师大合并,称上海师院。
⑤《杂谈宋史研究》,《程应镠史学文存·流金集》,第517页。
⑥虞云国:《我的宋史研究》,《南方都市报》2011年4月25日。
⑦参看陈旭麓:《说‘海派’》,《陈旭麓文集》第二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第598-602页。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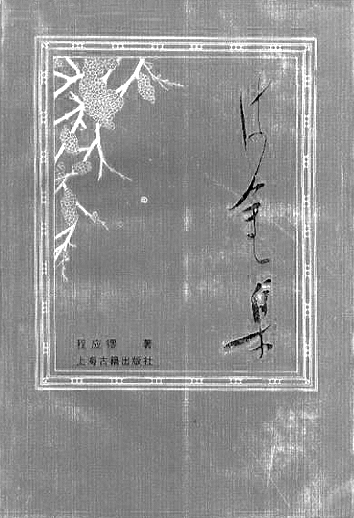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