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内的长篇小说《慈悲》写工人的生活,时间跨度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后,近五十年。国营苯酚厂是社会的缩影,时代变幻,厂里的人便有了戏剧性的腾挪翻转,构成了小说故事的主体。主人公水生二十岁进厂,就此打开了世界,生命中渐次有了朋友根生,妻子玉生,养女复生,然而岁月流转,一切又终将失去。他所经历的一切,构成了个人对历史的感应。
《慈悲》写个人沉浮时代的方式,显然不是《平凡的世界》式的,而是近乎《活着》。路内讲述故事,不是沧海横流的手法,而是“收着来”,他极尽克制,不铺叙“史诗”,而是把历史抽干了,做出标本,人物在历史中生出的爱与恨,有时候也只用一两句话点出。所以,《慈悲》是需要读者参与“完型”的作品,因为历史往往被放置在人物身后。《慈悲》所展现的工人生活史,不是大哭大笑式的,而是一种淡淡的悲凉,历史中的很多细节、场面被稀释掉了,作者用朴拙的对话,竭力挖掘人物命运的线条。
以工厂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像《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工厂生活“质地”都比较“厚”,细节充分,着力塑造英雄形象。但到了路内这儿,苯酚厂是个壳,苯酚厂里人物的命运的变迁,则是他体悟历史的道具,具有时代感的、现实的“质地”,在《慈悲》里是薄的。也许把小说背景换成民国初期,苯酚厂改成酿造厂,小说也同样成立。作者的野心,并不在敷衍现实,尽管路内本人是有工厂生活经历的,但他似乎更希望《慈悲》有一些哲学意味,他要用一个一个略显抽象的人物,表达对人生,对历史的看法。
路内写“文革”中的工厂,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写改革开放后,人与人位置的反转,个人在历史中的沉浮,不由自主,但依旧跌跌撞撞朝前走。然而对这一切,他不愿意“黑白分明”,取而代之的,是佛家的“慈悲”——这个梵语词汇自唐以来广泛影响着中国人。
中国人向来缺乏信仰,相信日常,而佛教的慈悲,却能够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过日子”思想巧妙融合,作为70后作家,路内没打算“清算历史”,《慈悲》中的水生,在苦难中朝前走,活下去,彼此温暖着走过残酷人生。这种悲观中的乐观精神,多少复归了晚明以来,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也很接近上海的市民精神:多少代都是这么过来的,做工赚钱,养家糊口,送走老的,养大小的,繁杂的生活中保留一点希望,一代一代搀扶着走下去……
《慈悲》中那些比较可爱的人物,水生、玉生、师傅、根生、复生,他们的性格没有多少演变(坏人同样没有),从出现到死亡,基本恒定,就连复生这个小女孩儿,也似乎从落地那一刻就很成熟,了然世俗规矩。小说中的老师傅得了癌症,临死前还为丧葬费去厂里讨价还价,不是为了自尊,而是为了活着的人考虑,这人物一分钟也没忘记俗世,即便面对着死。这些人有眼前的计算,但身上却保留了小市民骨子里的某种情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慈悲》也算是对平凡市民的礼赞。
梵语里的“慈悲”是从佛眼看世界,众生皆小,慈航普度,但路内的“慈悲”显然不是俯瞰式的,他讲过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自己家中经济困难,日子难过,其父靠外出打麻将赢钱贴补生计的事,恰恰说明他与每个人一样,在历史和生活的潮涌中,起起伏伏——从世俗角度看,他父亲靠打麻将赌钱赚菜钱是非理性的,可在困难中,这或许就是上天的安排,所以又是合理的。
因此,《慈悲》所讲的故事,或许可以稍微跳出历史因循,那些对与错的二元判断,它所用来说服读者的,是一些近乎宗教的意味感触——男主人公陈水生从大饥荒的农村走向城市,最后又带着复生走回老家。陈水生身上还保有乡村中国人的憨厚与机敏,他“挽救”了很多人,包括患有肝病、不能生孩子的妻子玉生,被人送出的养女复生,逞强好斗却终究一败涂地的根生,甚至厂子里的人申请补助,也总是找水生才能办成。
《慈悲》里没有传统的英雄形象,小说中貌似最狠的角色根生,也在命运的沉浮中被打折了腿,最终因倒买倒卖一败涂地。反倒是水生,柔软而有力量,他受得苦,认命,依足做人的规矩,懂得顺势而为。人生如雾天舟行水上,水生这个平凡的男人,最后反倒成了引航的人,因为平凡、坚守,终于获得几分悲壮。水生的形象从而有了普遍意义:怨恨有什么用,爱着身边人,好好活下去,或许已经是对生命的最大成全。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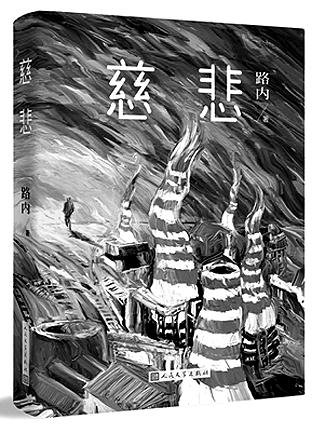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