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普雷基(Robert Pledge),1942年生于英国伦敦,曾任法国视觉艺术杂志《Zoom》的编辑,后来任伽马图片社纽约办事处主任。1976年,他与一些摄影家共同组建了联系新闻图片社。他也是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大型摄影展和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等活动的知名国际评审团成员之一。曾被《美国摄影》杂志评为世界摄影最具影响力的百人之一。
在中国第16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评选活动上,本报记者对罗伯特·普雷基进行了专访。
——编者
记者:作为中国第16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的评委,您对此次展览的评选活动有什么印象?
罗伯特·普雷基:参与这样的活动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这个比赛每两年一届,更多是遵从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一种传统,让更多摄影爱好者参与进来的一个活动。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就可能不会有许多专业的摄影师去拍摄一些严肃的主题。但这样的影展对我来说是一个获取新信息的渠道,可以看到中国摄影师在过去三五年中所关注的主题。因此,他们拍得好与坏其实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他们关注的领域是否发生变化,以及他们的兴趣点在哪里。
记者:作为一名出色的图片编辑,您怎样辨别一幅好的摄影作品?
罗伯特·普雷基:这其中并没有秘密,也不存在什么魔幻的方程式。我相信你去问不同的图片编辑,会得到不同的答案。但评判好作品有三个基本的元素:内容与主题、形式与风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诗意与情绪。尽管摄影作品都是一些信息的传达,但更重要的是它背后的那些诗意。这同音乐、文学与绘画一样,其中并没有什么神奇的东西,但是因为长期耕耘在这个领域,这些经验都会帮助我做出正确的判断。
记者:为展览选图片与为媒体选图片,您觉得有什么不同?
罗伯特·普雷基:为媒体选图首先要界定是给什么样的媒体,是资讯类的还是摄影类的专业媒体。如果是摄影类的,那么它呈现的形式就很重要;如果对于资讯类的杂志,其拍摄美学上的意义就不是那么重要,更多的是图片冲击力能否更好地支撑新闻内容。为媒体选图片,数量往往很少;但是对于一个展览,需要的图片数量就要多很多。人们在阅读杂志的时候,会看到一幅幅连续的图片,你可以向后看,也可以往回翻;而在展览上,你和图片的关系则会产生不一样的感受。在做图片编辑的时候,你的工作有点儿像一个DJ,在酒吧播放歌曲与在婚礼上或者是家庭聚会中选择音乐是不同的。所以,这样的工作区分还是很大的。
记者:据说,20世纪80年代您来中国参加摄影活动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摄影师应该把35毫米以下和70毫米以上的镜头全部锁在柜子里。”为什么这么说呢?
罗伯特·普雷基:我是说过类似的话,但当时的意思是你应该把变焦镜头锁在柜子里,无论它的焦段是30-70毫米,还是70-135毫米。这主要的原因是定焦镜头会迫使你去选择拍摄的距离,迫使你去接近周遭的环境,去接近事件正在发生的现场。但是如果使用变焦镜头,它就会代替你靠近和远离被摄者,这些都是人造的效果。
所以我说那句话基本上是抛出一个概念,具体的技术焦段其实并不重要,因为环境是会变的。有些时候你必须要使用变焦镜头,例如在拍摄短跑比赛选手接近终点时的画面。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是一个你对拍摄主题的选择,因为你可以不当体育摄影师。如果希望独立、自由地拍摄,那么你应该选择35毫米的定焦镜头,你必须要接近拍摄对象,必须要在现场。摄影是一件孤独的事情,你要长时间一个人工作,也要随时准备冲到前线去拍摄,所以要准备灵活轻便的器材。总之,如果你要拍摄一些真正有冲击力的故事,那么就必须接近拍摄对象,去了解更多,做更多功课,在知识上变得更加强大,这和用一个长焦镜头远远地去拍摄是完全不一样的。
记者:您认为中国摄影师有没有什么共同点,能让人一眼就辨识出来?
罗伯特·普雷基:有很多共同点,例如主题,中国摄影师所拍摄的主题往往会让你一眼就看出来。我比较关注常河,他供职于一家传统的新闻媒体《东方早报》,但同时也拍摄了许多有趣的独立主题摄影。他拍摄的《中国动物园》曾获得荷赛的奖项,在他的镜头下,这些动物们已经很衰老了,它们被不友好地对待,而常河使用Holga相机(Holga相机是一种胶卷相机品牌,存在漏光、眩光、色彩偏移等现象。——编者注)记录了这一切。一般情况下,一个严肃的摄影师是不会使用Holga相机的,但是他打破了规则,使用了另一种摄影语言。
记者:在过去与现在,摄影改变世界的方式是不同的,您是怎么看待这个不同的?
罗伯特·普雷基:首先,我不认为摄影能够改变世界。确实,对于某些人来说,尤其是在二战和越战之后,摄影让人们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公众的意见可以导致政府行为的变化,人们认为它改变了世界。我想,摄影的确可以在这方面起到一些小的影响,因为它们提高了公众认识,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有很多大型的公司直接拥有新闻媒体。
其次,虽然我说摄影无法改变世界,但是它可以作出自己的贡献,它可以唤起大众对问题的认识,而这完全取决于摄影视觉冲击力的大小。要知道,现今世界上主要的大型非政府组织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摄影的帮助,他们要仰仗摄影师的作品来传递信息,但同时这也让人们产生了一种幻觉,就是摄影可以改变世界。
记者:您相信在未来摄影可以改变世界吗?
罗伯特·普雷基:我不是站在玩世不恭的立场上说这件事。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会让手段服务于目的,有些成功的摄影师也的确用自己的摄影服务了特定的目的,但你并不能陷入这种幻觉,某天你一睁开眼睛,世界改变了,它不会这样瞬间发生的。只不过媒体的确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摄影了,使用声音、图像、视频所制作的多媒体让人们见证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它们帮助世界改变了许多。要知道,摄影是没有声音的,这也使它突然间失去了力量,地位并不像过去那样重要了。
我认为摄影必须要开始关注一些真正重要的议题,例如卢广和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所做的,他们只会在重要的议题上投入精力,长时间地工作,挖掘深层次的故事。他们要做大量的调查和准备工作,并把所拍到的图片整合成一个长篇故事。社交媒体做不出这样的工作,因为他们是基于当下的分享机制的。相对来说摄影所需要的技术支持和运作资金都是非常少的,你可以住在廉价的宾馆长时间拍摄一个议题,这就是它现在的优势。
所以,虽然我不相信摄影可以改变世界,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因此,我们一样也可以期待一个更好的世界在未来等着我们。
(本报记者 马列)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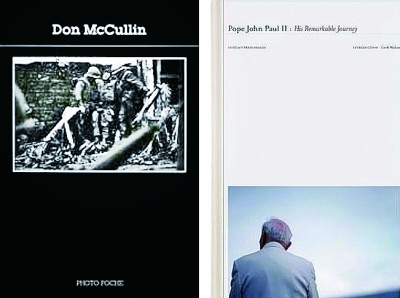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