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离老师是忘年交。我调北京工作,只要回保定,都会与李老师一起坐坐。但他回济南后,我们就无缘一面了。从金善那里常常听到他的消息,闹过一次血栓,但已经恢复。耳朵背了,有些发呆,都是身体越来越老的表现。我一直不太在意,以我对他健康的了解,坚信他会活到百岁开外的。但3月8日,突然接到金善短信,告诉我不幸的消息,李离老师辞世了。看来人过八十,无论怎样健康,也是残年,如风中之烛,随时寂灭。
李老师身体之好,是校内闻名的。山东汉子,一米八的个子,穿黑呢子中山装,从来走路笔挺。我在河大时,李老师的父亲还健在,和李老师住在一起。我有时会碰到他们父子俩到澡堂洗澡,七十岁的小老头,用自行车带着九十岁的老老头,我颇感慨二老身体之结实,叹为奇观。听说李老师八十岁还骑自行车,直到他离开学校。
有时,我会情不自禁问他养生之道。他总是笑而不答。其实,我这也是明知故问。李老师从来不养生,如果说有的话,也是以不养为养。他一生的嗜好只是三件:书,烟,茶。
李老师是有名的书痴。乍看起来,他对书的喜爱,源自他的职业。他 1946年入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毕业后到《开封日报》、《河南日报》做副刊编辑。1949年秋调天津市文联,编辑《文艺学习》《天津文艺》。1952年调人民日报社文艺组任编辑。他被定为胡风分子之前,主要从事编辑工作。与此同时从事小说、散文、诗歌等创作,发表于《天津文艺》《天津日报》《进步日报》和《新观察》等报刊。1953年调华北文联工作。1954年调天津师院、即河北大学的前身任教,直到退休。李老师一生从事的都是写书、编书和教书工作,自然是与书结缘最深的。但也并非所有与书接近的人,都喜欢书。据我所知,有相当多的教书人是不藏书的,有更多的与书打交道的人是不喜欢藏书、不爱读书的。而李老师是真正的读书人。
与书结缘,也可能是好缘分,读书、写书,给人带来幸福;也可能是坏缘分,读书、写书,给人带来坏运气。书给李老师带来的显然是厄运。可以说他是因书得祸,书毁了他一生的正常生活。五十年代,李老师被定为胡风分子,而且是在天津的四大金刚,逮捕入狱。他因何定罪,我不得而知,他老人家想来也是糊里糊涂。人不如草芥,就那么轻易地被剥夺了自由。但他因书结识了芦甸,又因芦甸结识了胡风,当是他受胡风株连的主要原因。李老师在监狱中关了一年半才被释放,但作为胡风分子,从此再也不能登讲堂,下放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其后被贬到资料室做资料员,直到八十年代被平反。这三十年间,他的命运就是“被”着,自由被人左右,生活被人颠倒,读什么书的权利被人剥夺,自然写书也是被人禁止的。书是李老师的霉头,也许是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霉头,因了书而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大有人在。听说胡适的研究生魏际昌先生去世后,北京书商要收购魏先生的书,家人犹豫不决,魏先生的夫人于月萍说了一句在我们听来无异惊世骇俗的话:“书有什么用!”乍一听,我颇愕然。但是慢慢想通了,于先生的话里潜藏着老知识分子爱书而又恨书的悲辛。魏先生如此,李老师更甚。若是换个人,也许早就远离倒霉的书了。但李老师始终与书不离不弃。可见李老师爱书,不简单是职业关系,而且是他的气质秉性使然。
这也从他的藏书之广博看得出来。他教明清文学,但他藏书却不限于这一领域。平时收集,无论古今中外,且多有奇书。每当遇到罕见之书,他很高兴能与朋友分享,我的许多书,是经李老师介绍买到,或者就是他代购的。李老师的好书,多藏于他家迎门楼道的壁橱上。有时去李离家,还没坐稳,他就会搬着椅子往外走,那一定是他搜到了好书要给你看。他站在椅子上,打开壁橱,将身子深深地探进去,取出书来,放到我的手上,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那时你会懂得,什么才叫爱书之人。
在我认识的河北大学朋友中,有两位阴阳颠倒的人,小的是宫敬才,老的是李离。李老师的作息时间,一般是下午两三点起床,吃早点,或不吃早点,但必泡一杯酽茶,然后是他处理家务和社会活动的时间。写信,接待来访的客人。大约五点左右去单位取信和报纸,顺便去菜市场,回来做一天中非早、非午、非晚但又三者皆是的一顿正经饭。大约九点前后,开始读书,直到次日的早晨。当大家起床上班时,李老师开始上床睡觉。他和常人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九十年代后几年,我常到李老师家。时有急事,尽管知道他的作息时间,也会上午或中午去拜访。敲门,一遍不会有人应声;再敲,声大些,喊上一句:“李老师,是我。”门会悄然打开。睡眼蒙眬的他,躲在门后,再匆匆回到床上。此时,我会转到东屋,等他穿衣服。东屋也躺着一位老人,那就是李老师的父亲。但老伯显然已经起床,穿戴整整齐齐地躺着,候着李老师起床。李老师中年丧偶。打成胡风分子后,夫人陪着他熬过了极艰难的岁月,待到“解放”,她却突然离世。李老师的悲痛可想而知,从此不再续弦。在李老师的宿舍,挂着夫人的遗像,文绉绉地透着漂亮。就是这样的女子,嫁给了读书人,坎坷半世,惨淡了一生。所以,每当看到两个老人隔屋相对而卧的景象,我就感到极为怪异,继之,酸楚之感,从脚跟升起。
宫敬才颠倒作息时间,既是为了读书,也是忙于写书。而李老师白天睡觉,夜里熬灯,却只有一样:读书。八十年代后期,文坛渐呈开放之势,李离老师曾尝试恢复写作,写一些回忆胡风分子的文章。九十年代初,陆续在《传记文学》、《新文学史料》等刊发表。他每发一篇,都极其高兴地送给我看。我鼓动他写一本关于胡风事件的书,告诉世人,他的朋友的真实面目。李老师也是信心十足。但是似乎只发了三四篇,就中止了。问他原因,他说,这类的文章又难发表了。不便写书,遂只有读书。所幸书渐次容易得到了。我之于读书,自信是既能坚持、又能读得很快的人,但比起李老师来就自愧不如了。有时,我有可读之书,李老师也会借去阅读,常常是头天拿去,次日返回。开始时,我怀疑他是否认真读过,但说起所读书来,他的评论都深中肯綮,而且细微到某一个细节。由此我服了他。
李老师是老烟枪。他读书,离不开手的是香烟和茶杯。一口烟,一口茶,一页书;一支烟,一杯茶,一本书,此为李老师的读书境界。进李老师家,如进神仙洞,云雾弥漫,需仔细辨认,才会发现隐居云端的仙人。我没问李老师何时开始吸烟,但揣度如此大的烟瘾,应系之于他一生的不如意。书固然可以排遣苦闷,但在监狱中,能容许他见到书的影子吗?对待一个因书获罪的人,最好的“改造”,实则是最重的精神摧残,就是不许他读书,不让他见到书。书是他的禁忌。读书固然也会填满漫长的冬夜,挤掉孤独老人的寂寥,但读书不能代替回忆,不能代替思考。而对这位曾经才华横溢却无端陷入囹圄、遭遇不幸的读书人来说,岂能不回看他走过的泥泞?岂能不思考他命运的因果?此时最佳的伴侣就是烟了。那缭绕的烟缕,何尝不是他的百转愁肠、纠结的心绪?在我的朋友中,多有烟民,亦不乏大烟枪。但若论抽烟之老辣,无过李离者。可惜,也最遗憾的是,李老师只留下了他回忆几个倒霉朋友的文字,却没有个人遭际的文章,更没有留下他对个人人生命运的思考。
但是,从他回忆胡风、芦甸、阿垅、冯大海、葛覃和高云览的文章中,我还是颇为唏嘘感慨他为人的温柔敦厚。他的朋友中,多是才华横溢的作家,但因胡风事件的牵连而命运悲惨。芦甸被关押了十年,七十年代瘫痪致死。他年轻时就守寡的老母亲,也在他关进狱中后被遣送回江西原籍。等到芦甸出狱,他的母亲早已不在人世。而另一位朋友阿垅,就更为不幸。这位参加过战争的军人,1955年,因“胡风集团”案下狱,十几年的铁窗生活,终于熬干他的生命,60岁病死狱中。在“胡风集团”中,《小城春秋》的作者高云览似乎幸运。1955年,胡风事发,他却于1956年因肠癌去世,而且《小城春秋》居然意外出版,并且一时洛阳纸贵。但是就在1980年“胡风集团”案件平反时,人们发现,在平反的名单里,竟然列有高云览的大名。所幸者,他生前没有享受到胡风分子的“特殊待遇”;不幸者,死后也要背上“分子”的恶名。每每写到此处,李老师都悲慨他们命运的悲苦,为他们鸣不平,文中充满勃郁之气。李老师于文艺理论有深厚修养,他知道何为命运,既谈命运,就不能不讲遭际,即社会对个人命运的影响。有时社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甚于上帝。所以卡夫卡无可奈何地说,目标虽有,但道路却无一条,所有的只是彷徨而已。但是,在李老师的文章中,却多反躬自省,寻找朋友悲剧命运的内在原因,写他们性格里的悲剧因素:胡风的性情耿直,诗人气质,断送了他的艺术生命。芦甸思想上想不开,解不开问题的疙瘩,精神上不堪自戕,终于疯掉。冯大海诗人气质太重,感情十分脆弱,脾气暴躁不计后果,自尊心太强宁折不弯,等等。但是,在一个非正常的环境中,决定个人命运的,恐怕很难说是个人的性格气质。读到此处,我不免感叹,中国的读书人实在是太厚道了。
在李老师那里,烟与茶的关系,如同相生相克的阴阳两极。他有在我听来极为可笑的理论:浓茶可以解烟。因此他喝茶总是与抽烟相伴,而且必是浓茶。只要看看他的茶杯有多黑,就知道他喝的茶有多酽了。对于李老师的理论,我常常姑且听之,一笑了之。但有时也会开着玩笑与他理论,那茶走的是消化道,烟走的是呼吸道,如同猫上房,狗跳墙,各走各的道,两不相干,喝茶又如何能够把烟稀释了呢?每当此时,李老师总是呵呵一笑,摆出信不信由你的面色。不过,茶为提神之物,有此不夜侯侍奉,也助李老师涤除了无数烦恼,读破了万卷诗书。
李老师本名张立信,生于1927年,故于2015年,享年88岁。这是一位因书得祸,却又因书而获解脱的读书人。
(作者为国家图书馆原馆长)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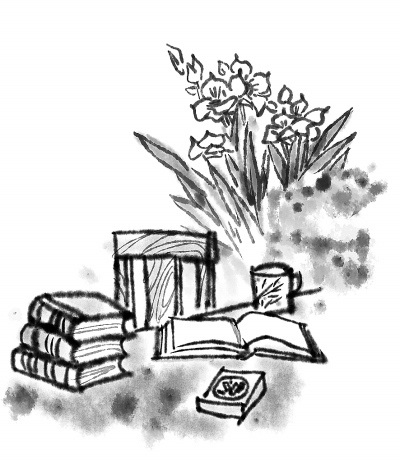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