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大众文化呈现出让我们惊讶的“青春恋物癖”趋势:除非讲述可以吸引年轻人的故事就再也没有故事可讲;除非在青春的故事中寻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值得留恋;除非一场爱情,就再没有激情。自从《亮剑》开启了新战争片的时代,不难看到,“悲壮感”的获得变得非常艰难。英雄片里王成式的死亡再也不能激活人们的崇高,就连香港古惑仔电影确立的男性主人公死亡惊颠,也无形中消解了;与之相应,诸多故事都是通过“爱情女人之死”来完成故事对观众的震撼作用。东方闻英、秀芹、杨紫云、梁楚韵……只要不是插科打诨,这些革命题材的影视剧就只能通过女人的死代替英雄的死,来产生悲凉的煽情力量。今天大众文艺处在一种“青春故事逻辑”的支配之中,其意义生产的贫乏乃是因为没有其他意义言说,就只能也恰好生产爱情神话。爱情,由此成为利己主义时代同质化生活的可靠信仰。这种“情感偏执狂”现象,不是禁止了其他意义言说的权利,而是因为另一种意义的言说丧失了现实基础,变得没有了听者,也就丧失了可能性。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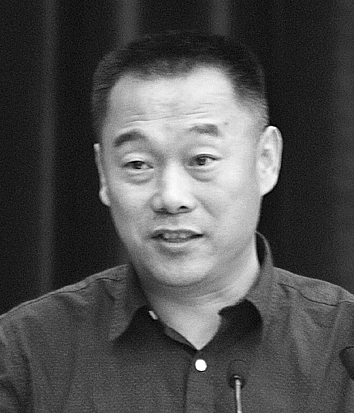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