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斗室满壁书,毕生心血自然道。
记得2010年10月,为纪念“人民科学家”钱学森逝世一周年,记者在这间简陋的书房里采访了黄顺基。如今,5年过去了,一切如故。满壁书籍,书页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地作了很多批注,既有读书时的体会,亦有对思想的疑问与点评。
眼前的先生依然平和、朴实,虽至鲐背之年,但讲话铿锵有力,谈哲学、谈人生、谈社会,兴味不减当年。
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举行了“科学技术哲学与社会系统工程研讨会暨黄顺基九十华诞庆典”。有人说:“在中国自然辩证法领域,像黄顺基这样以大尺度的时空跨越为本学科作如此系统深入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多。”
对此,黄顺基却用不能再“白”的话谦虚地表示,这九十年来,自己只是过得很“实在”——“能够勤恳工作,踏实研究,而且研究基本上都着眼于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相关的科技问题”。
为学之本
1925年,黄顺基出生于广西昭平一个贫苦家庭。彼时的昭平,地理位置偏僻,没有公路,水路只通木帆船。家里兄弟六人,他排行老五。父亲在叔父的店铺里打工,薪资少得可怜。
因此,对于黄顺基来说,能用心用功读书且读到大学,实属不易。“大学前两年,我读的是师范类,可以享受公费;1949年上海解放后,就转由党和国家供给继续读完大学。”
幸运的是,闭塞和贫穷并没有禁锢幼年黄顺基喜爱思考的天性。初中时,他写了一篇日记《人是一张白纸》,没想到竟受到老师的大加赞赏。
“接触到哲学后,才知道英国哲学家、经验主义的开创者约翰·洛克早就说过类似的话——‘人心如白纸似的,没有一切观念’,只是我那时候并不知道而已,纯属巧合。”黄顺基笑言。
由于出身贫寒,黄顺基对劳动人民始终保持一颗同情、感恩之心。“国家的命运决定了我的命运,如果能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做点什么,那是我的荣幸。”
1947年至1951年,黄顺基就读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大学的学习为我后来进入科学的殿堂打下了基础,特别是其中的两门学科,令我终身受益。”
黄顺基所说的两门学科,一门是数学。“数学的分支学科不少,比如微积分,它是学习牛顿物理学必不可少的工具,而牛顿物理学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是‘理论物理学领域中每个工作者的纲领’。再比如抽象代数,它以‘结构’为范畴,概括了群、环、体等代数系统,大大锻炼了我的抽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能力。”
另一门是哲学。“作为数理逻辑学家和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罗素与老师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奠定了数理逻辑的科学体系。他的哲学思想是‘语言结构与世界结构一致,命题与事实相对应’,由此出发建立了他的知识论。”当时,黄顺基阅读的主要是罗素的哲学著作,因此深受罗素思想的启发。
术业之功
1951年,大学毕业的黄顺基由国家统一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研究生班,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此后,他的从教生涯随着学校事业的发展和哲学学科的分合变化,有了三次大的转折,也由此涉足三个哲学研究领域。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初期的教师,除中共党史专业外,全是苏联专家,教材也是苏联专家的讲义,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以《苏联共产党(布)简明历史教程》为主要内容),大约每两个星期就发给研究生十几本参考资料。黄顺基被分配在逻辑组,除学习上述课程外,他还会专门去听苏联专家尼基金的逻辑课。
研究生期间的学习任务繁重,几乎每天都要熬到半夜1点钟才能睡觉,星期天也不休息。对于这段学习经历,黄顺基十分珍重,认为它为自己后来的教学与研究指明了方向和道路。“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了人类在19世纪创造的优秀成果,给我们以完整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价值论——没有这个理论基础,就没有我后来的学术成就。”
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成立。由于黄顺基的专业方向是数学与逻辑学,为了教学的需要,学校把他从工经系数学教研室调到哲学系逻辑学教研室。
当时,哲学是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的一门学科,也是黄顺基有兴趣研究的方向。“担任哲学系逻辑学的教学工作,把国家的需要和我的专业兴趣结合在一起,给我创造了一个发展机会,可以说是我学术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关键点。”
“文革”期间,中国人民大学被迫停办,黄顺基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直到1978年复校。由于工作需要,黄顺基又从逻辑教研室转到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并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后半生的学术研究方向,成为我国最早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的学术带头人。
这门科学之所以给自己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按照黄顺基的说法,是因为从学科体系来看,逻辑学是一门基础科学,而自然辩证法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科学观),既是关于自然界和自然科学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又是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方法论。“它涉及广阔的领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起着其他学科所不能代替的作用。”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实力当时在全国高校中处于领先地位,不仅教师队伍齐备,有全国公认的教材,还是在改革开放前唯一培养过自然辩证法研究生的高校。黄顺基带过的两届研究生,毕业后在自然辩证法界大多起着骨干与带头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新技术革命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类未来发展的思考,“后工业社会”“三次浪潮”“大趋势”等学说如潮水般冲击着我国思想界,于是,黄顺基组织自然辩证法界的部分学者编写出《大杠杆——震撼社会的新技术革命》一书。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人民日报》《大众日报》《文摘报》《国内哲学动态》等都先后发文称赞,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读后也来信致贺。
历史的车轮行进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亲历国际、国内科技发展的大变革期后,加之多年的研究心得与经验总结,黄顺基撰写出《科技革命影响论》。这部著作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为指导,全面而具体地考察了科学技术革命对哲学、历史学、经济学、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未来的影响。
哲学家黄楠森读后认为,“以如此广阔的视野,从哲学的高度,详尽论述科技革命影响的著作尚不多见”,并评价该书是“十多年来我国科技哲学研究和讨论的总结”,也是“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时代挑战的回答”,因而具有极强的理论性、时代感、现实性、创造性。
哲学之思
1957年4月的一天,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办公室通知:上午10点钟派车送逻辑学教研室的王方名和黄顺基到中南海,要整理好衣装。听闻电话打给了时任校党委书记胡锡奎,说是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
接见时的情景令黄顺基终生难忘。“到了新华门,由门警通话,然后引我们沿中南海步行到颐年堂,田家英(毛泽东主席的秘书)早已在那里等待。他和我们谈话不久,便见主席从后庭迈步走进厅堂,他后面紧跟着周谷城先生(复旦大学教授),我们两个赶紧迎上去和主席握手。”黄顺基回忆道。
“这两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关于逻辑的文章,你们的观点相同嘛!您有知音呀。今天约大家来谈谈。”毛泽东向周谷城介绍说。
落座不久,又陆续来了一些哲学与逻辑学界及学术界的前辈,其中有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郑昕、费孝通、胡绳等。刚刚三十岁出头的黄顺基万万没有想到,像自己这样一个“无名小辈”竟然能够与学术界的名流坐在一起,特别是能够受到毛主席的亲自接见,这是何等的荣幸。
后来,黄顺基才知道,这件事并非偶然。当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为了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就在这时,逻辑学界发生了一场争论:一方代表苏联学术界的意见,认为形式逻辑是哲学学科,它的同一律是形而上学,是反辩证法的,因为它说“同就是同,同不可能是异”;另一方则认为,形式逻辑是一门科学,同一律是指在思维与论述过程中应保持对象的同一性。与此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形式逻辑是否只管对错,不管真假?
王方名和黄顺基对苏联学术界的观点提出了质疑,相关文章发表在《教学与研究》上——凑巧的是,他们的意见与周谷城不谋而合。
《教学与研究》面向全国发行,毛泽东非常重视,在百忙之中经常深夜阅读上面刊载的文章,以了解国内的思想理论动态。国内这次对逻辑学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如何学习苏联问题的继续,因此毛泽东力主邀请争论中的有关人士到中南海座谈。
这次会见,毛泽东主要谈的是关于学习苏联的问题。“教条主义的亏我们吃得太多了,不能老是照抄照搬,要走自己的路。我找邓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谈了几次,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多动脑筋。看样子贯彻起来很难呀!”
接着,毛主席话锋一转,谈到了学术问题。“学术上也应该百花齐放,各抒己见。京剧有梅派、谭派、马派……各式各样的派,为什么逻辑学界就不可以有周派、王派、李派等学派呢?”然后,他转向周谷城,“你的观点与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有同音,不孤独嘛!”
座谈的气氛轻松而愉快。金岳霖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被公认为我国现代逻辑学的创始人。毛泽东希望金岳霖能够推动国内逻辑学的研究工作。费孝通不久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早春的天气》一文。毛泽东对他说:“你写的《早春的天气》,我看过了,写得不错嘛!”田家英插话道:“读了是有吸上新鲜空气之感。”
谈话间,不觉过了中午,毛泽东邀请大家一起用餐。黄顺基紧挨着主席入座,田家英坐在主席左边。主席面前摆着一碟湖南家乡菜豆豉辣椒,其他便是几盘普通的菜。当加上杂粮的米饭端上来时,主席笑着对大家说:“这是金(黄色小米)银(白色大米)八宝(各种豆)饭。”
服务员斟上葡萄酒,毛泽东举着酒杯,站起来风趣地说:“为消除紧张局势干杯!”在黄顺基看来,主席的意思应该是:在逻辑问题讨论中,各方都声称自己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争得面红耳赤,彼此毫不相让,大有拼个你死我活的态势,这是何苦来哉?!
坐下来后,毛泽东转过头来给黄顺基夹菜,并亲切地询问他的年纪、哲学系主任是谁。当听说系主任是何思敬时,毛泽东说:“哦!我们在延安认识。”
饭后,大家坐下来接着谈。黄顺基记得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有趣的话题:动物是否也有思维?在座几位学者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后来是胡绳(或者田家英)说:“行军过河时,马总是要用前蹄往水里探一下,看来动物还是有思维的。”
毛主席谈兴甚浓,从上午10点钟起一直到下午4点多钟,谈话进行了六个多小时,仍毫无倦意。黄顺基等人怕主席过于劳累,于是起身告辞。“主席亲自送我们,走到庭院时,他指着枝叶繁茂的桂树说:‘八月中秋,这里桂花开得很香,那时再邀请你们来’,说完便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
回到家里,黄顺基兴奋得彻夜难眠——“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和学术界前辈相识,如此殊荣真得感谢《教学与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理论界‘一面倒’的情况下,它竟然敢于发表与苏联老大哥不同的意见,以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为己任,谈何容易!”黄顺基不禁感慨道。
此后,借由早年同《教学与研究》结下的不解之缘,黄顺基再接再厉,思维不止则笔耕不辍,在该刊物上先后发文20多篇,时间跨度长达50多年。
书信之缘
虽然钱学森与黄顺基的专业领域不同,从事的工作性质也不同,但二人却因“英雄所见略同”而有着长达10年的书信交往,其情谊鲜为人知。
二人的相识,还要从1986年黄顺基组织编写的《大杠杆》一书出版说起。“当时社会上反响强烈,各大报刊纷纷发表述评给予高度赞扬。我没有想到,钱老也通过山东大学出版社写信来表示祝贺,他说:‘《大杠杆》比起时下流行的、中外关于新技术革命的书都更完全,所以是本好书。向各位执笔人及编者致贺!’”
当时的北京医科大学教授刘奇曾经与钱学森同住一个大院。“一次散步时碰见,钱老问我是否看过《大杠杆》,并郑重地告诉我这是一本好书,要好好阅读,可见这本书给钱老的印象很深。”刘奇说。
1996年在获悉《大杠杆》获奖后,钱学森又很快给黄顺基寄来信件:“我首先要向您表示祝贺,恭贺尊作《大杠杆》荣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1994年,黄顺基写了一篇文章《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投到《人民日报》。当时学术界很多人认为自然科学才是第一生产力,不同意这个观点,因而黄顺基的这篇文章很可能发表不出来。“《人民日报》编辑部主任卢继传读后,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有道理。他出了一个点子——把文章的题目从肯定的语气改为商榷的语气,以《关于社会科学是否是生产力的思考》为题发表。”黄顺基说。
在众多友人的帮助下,文章终于在《人民日报》刊发出来,黄顺基将其寄送给钱学森。关于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1995年内,钱学森先后给黄顺基回复了三封信。
2月26日,钱学森在回信中说:“您前次送来的大作我拜读后认为很重要,我也同意。我们要宣传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的论点。因此我已把尊作送呈宋健国务委员,我知道他关心此事。”
5月29日,钱学森又来信说:“有关国家领导人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26日讲话是完全支持您的观点的,也是支持我的观点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要同社会科学、哲学联合;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让我们庆贺吧!”
9月3日的来信内容则是:“我从《哲学动态》的专访稿中才知道您原来是学数学的。数学属自然科学,所以您是从自然科学走到社会科学、哲学的,当然比不学自然科学技术的人要胜一筹。您现在看到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比社会科学大多数人要高明,道理就在于您知道什么是自然科学技术。”
同年9月11日,钱学森在密切关注新产业革命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之余,给黄顺基寄来美刊《科学美国人》,要他注意信息技术的发展。“钱老认为,信息技术必然带来一次新的产业革命——第五次产业革命,它不仅是科学技术问题,也是社会组织的改革问题,建议我组织力量探讨‘第五次产业革命在社会主义中国’。”
对此,黄顺基回信道:“‘第五次产业革命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题目非常好,这是一个有重大社会历史意义的课题。如果说第三次产业革命把落后的欧洲推上世界舞台的中心,并且为资本主义时代奠定了物质技术与思想基础,那么,您所提到的、当前正在进行的第五次产业革命,在正确的设计、指导与协调的条件下,必将大大推动社会主义中国迅猛前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创新的篇章。”
黄顺基认为,如此重要的课题一定要请钱学森亲自挂帅,因为“以钱老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洞察力和高瞻远瞩,方能驾驭”。
然而,钱学森却在黄顺基的回信上签注:“我只能当顾问,不挂帅”,并请自己领导的课题组成员汪成为院士、戴汝为院士、王寿云秘书长、于景元所长、涂元季教授、钱学敏教授考虑此事。
1996年9月16日,“新产业革命在中国”课题组召开成立大会,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及人事部、交通部等20多个单位的30多名专家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
此前,课题已被批准为“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博士点重点研究项目”,由钱学森任顾问、黄顺基任课题组组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负责组织实施。此后的研究成果有:《信息革命在中国》(1998年)、《现代信息技术基础知识》(2001年)。
“回想起来,我在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的研究方向上取得的成果,与钱老对我的关怀、帮助与指导是分不开的。”对此,黄顺基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桑榆之志
1997年,黄顺基从科学技术哲学的教学岗位上退下来,却并未停止学术研究,而是继续在两条科学战线上进行新的探索。
一条战线是逻辑学。“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的学习、研究与交流中,特别是在知识创新中,逻辑学的作用绝对不可以忽视。对此我提出了独立的见解,先后发表了《逻辑学在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知识创新不能没有逻辑》《新世纪逻辑研究方向探索》《问题、逻辑与理论创新》等论文。”
除了在逻辑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的一系列文章外,2001年,黄顺基还与学术同仁们一道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逻辑与知识创新”,后以著作形式出版,同样受到广泛关注与好评。
另一条战线是科学技术哲学。在现代科学技术以雷霆万钧之势推动历史前进的新形势下,如何从新的视角考虑中国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战略?对此,黄顺基提出了较深层次的思考,先后发表了《中国科技发展战略问题初探》《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学研究》《钱学森论科学技术业》《新世纪科技对社会影响的新特点》等论文。
2003年,受教育部社政司委托,黄顺基主持编写的《自然辩证法概论》(国家示范教材)正式出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东北大学等知名高校均有资深教授参加编写。
根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科学技术的新进展,《自然辩证法概论》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的学科”,被学界认为“较全面地体现了自然辩证法这门科学在新时期的新进展与新特点,为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新境界作出了贡献”。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退休后本应颐养天年、含饴弄孙,但黄顺基却说,退休后自己拥有了更多时间与精力,能够沉下心来思考问题。因此,他的很多理论文章和学术著作都是在退休以后完成的。“国家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社会也处于改革开放的变动期,涌现出不少新的现象与问题。既然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科学技术的发展究竟如何影响国家的发展?我们需要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与指导。”
生活中的黄顺基豁达开朗,用他的话说,就是“研究哲学久了,对名利就淡泊一些,获得的幸福和得到的真理就多几分”。如今,他的晚年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早晨起来打一套太极拳,上午、下午都出去散步。
“重要的是保持情绪稳定,以一颗平常心看待生活中的矛盾。对于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心态一定要平和,不要自找麻烦,而是把精力集中在思考问题上,这样烦恼自然就少了。”黄顺基打趣地说,这是自己一辈子生活经验的总结。
除了每天上网看新闻、读书、思考、写文章外,精力充沛的黄顺基还会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和社会活动,比如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牵头、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组织实施的“口述钱学森”工程。眼下,他正在修改一篇杂志社的约稿《社会系统工程与协同推进四个全面》。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黄顺基非常欣赏的一句话。“名和利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因此还是要留下一些对社会和历史有价值的东西。”黄顺基希望年轻人能够尽早打下扎实的知识基础,并拥有热爱国家、关心社会、同情人民疾苦的人本情怀,因为“这是做任何事情都需要的”。
人物简介
黄顺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著名哲学家,1925年出生于广西昭平,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深造,次年留校任教。1956年起从事逻辑学教学,1978年后转入自然辩证法领域,研究自然辩证法和管理学。1992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称号。
(本报记者 张蕾)(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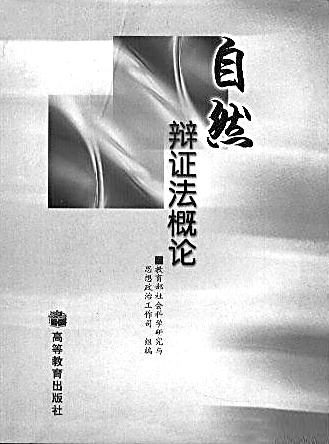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