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前夕,我终于找到了我寻找了30年的小学老师!但找到老师的结果却是我没有料到的。
那次去浙江省天台县采访,我顺便向县委宣传部时任副部长王正多打听我的小学老师,他是天台人。
“他叫什么?”宣传部办公室主任丁必佑问。
“张云洲。”
王副部长和丁主任马上都掏笔记下这个名字。
“让你寻找了30年的老师,一定对你影响很大吧?”王副部长问。
的确,在我短暂的求学生涯中,张老师对我产生的影响增加了我的自信,因而改变了命运。
1957年,我父亲因文惹祸被划为右派,被逐出杭州遣送回乡监督劳动。从此我成了右派的儿子,自信就是从那无处不在的歧视中离开了我。
我入读的是临海县(现临海市)花园区龙岭公社兰田小学,这是附近几个村唯一的小学。四年级时,班里新来了一位班主任,叫张云洲,是个“非常严厉的老师”。
果然,张老师的第一堂课就将我们全班征服。
上课铃响过,张老师走进教室,他敦实伟岸,浓眉大眼,一脸威严。这节是地理课,张老师一上来就提了个问题: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是多少时间?张老师从第一排开始让学生答题。农村孩子胆小,被老师的威严一吓,竟都答不出来。而答不出的不让坐,叫“插蜡烛”。不多一会,我前面的“蜡烛”已插成一片。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简单,成绩好的同学也能回答,但慑于新老师的威严,大家竟都失语了。
一根根的“蜡烛”在向我逼近。我本来就在人前犯怵,此时更感到自己心跳加剧。终于,我无可逃遁地站了起来,血,直往脑门上冲,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我失声了。
张老师的第一堂课就使全班同学慑服,包括那几个无所畏惧的“鼻涕英雄”。
张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二堂课是作文。作文是我的强项,我的作文常被当作范文在班上宣读。有了那次地理课之辱,我决心挽回颜面,好好表现。
那篇作文我写得神采飞扬,一气呵成。
下堂作文课应是讲评,凭经验,我的作文应能作为范文。
终于等到了那堂课,作文本在讲评前发了,没有我的。我更坦然了,肯定是老师把我的作文留作讲评。于是我轻松地期待着屈辱之后的好评。
然而,张老师没有在班上宣读我的作文,当张老师开始布置另外的作业时,我心慌了。既不讲评,又不发作文本,什么意思?经验对这位新老师失灵了。我无心听课,开始反思这篇作文,于是许多不足之处便一一显现,我越想越怕。
恐慌中,张老师已站在我面前,手里拿的正是我的作文本。他冲我点点头,嘴角微微翘起,微笑着说:“好好看看!”
我急忙打开,又迅速合上——作文后面是红红的一片。
不用说,那是批评!
此时,我蓦地感到——我自认,张老师的笑分明是一种讥讽。
我怎么会写出这么糟的作文!
下课铃一响,我冲出教室,跑到学校后面的山坡上,急切地打开作文本。
苍劲有力的行书俊美飘逸,张老师的批语如一股暖流注入我的心田,我顿感嗓子发热,鼻腔发酸——张老师在批语中热情地赞扬了我的作文,并以探讨的口气,对文中的几个段落提出修改意见:“如果这样写,是不是更好些?”“这一段如果能……可能会更生动。”
受惯歧视的我,我的老师竟平等与我探讨文章写法!我只是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啊!
那是极左时期,张老师明知我出身不好,仍不避讳,常在班里表扬我,这使我在饱受欺凌和歧视中感到了人性的温暖,自信逐渐恢复。
“知识就是力量,一个有知识的人就有力量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把他说过的这句话记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在我困守山村前途无望时仍督促自己不放弃学习。
然而好景不长,“文革”开始了。同学们用白眼、唾沫、咒骂、殴打来表明鲜明的阶级立场,甚至有同学往我头上撒尿。5年级没读完,我就被迫逃离,从此辍学。
不久,张老师也离开了我的母校,从此音讯杳然。
逆境是最好的老师,能教人怎样做人;苦难是金钱难买的经验,是一个人终生受用的财富。辍学后,我转入社会大学,放过牛,14岁参加生产队劳动,学会了所有农活,当过守林员,后来又成了云游四方的木匠。感谢张老师,是他的激励使我阅读的兴趣更浓,不管境遇如何,我都没有放弃读书。
十一届三中全召开了,父亲右派改正,高考恢复。在父亲的鼓励下,我鼓起勇气跨进考场,那份勇气中,有张老师给予我的自信。凭着这份自信,一个山村农民,一个乡村小木匠跨进了高校,并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天台有这么好的老师,是我们的光荣,我们一定帮你找到张老师!”丁主任说。
然而,要找到张老师并不容易。1983年我大学毕业即入光明日报浙江记者站工作。从此我便开始寻找张老师,我多次回老家临海采访,每次都打听张老师的下落,却一直未果。
张老师是天台人,会不会调回天台了呢?
1989年5月,我随浙江省一位副省长到天台调研教育,顺便向教育局打听。教育局很重视,马上查,还是没有。
临海,天台,一次次寻访,一次次碰壁。我还在浙江日报撰文寻找,我在文中呼唤:“张老师,你在哪里?”
“这个张老师必须找到,找张老师的是我的朋友!”王副部长对着电话加重语气。
很快,教育局回复了:查无此人。
看来,找到张老师的希望仍然渺茫!
“再找找,在离退休教师中找!”丁主任给已退休的县教育局长打电话。
当晚,我们正吃饭,王副部长手机响了:“……找到了?张老师在平桥镇!”王副部长的脸顿时神采飞扬起来。
我突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激动,眼眶顿时湿润,我别转脸去……
当晚,我见到了张云洲老师。这是我寻找了30年、离别46年后的见面!
记忆里伟岸挺拔的身躯已变得清瘦干枯,眼前的张老师,发斑白,背微躬,凌厉的目光已变得平和慈祥,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
“张老师,还记得我吗?我是温家岙的叶辉啊!”我握着他的手说。
张老师笑着,眼睛内视式地在记忆里迅速搜寻。
“温家岙?我记得有戴荣光。”
“我与戴荣光同班!”我忙示道,希望能勾起他的记忆。
“有陈三香。”
“对,陈三香高我一级。”
“还有小美,他家曾失火……”他目光开始躲闪,似乎是为自己的遗忘而愧疚。
“我爸爸是从杭州下放的老师。”我竭力帮助他寻找记忆。难道30多年来骚扰得我寝食难安的老师竟对我没有一点印象?我不甘心!
“老师?我记得叶泽楚、蒋素秋。”他说的这对小学教师夫妇与我同村。
张老师张了张嘴,终于无法记起我来。
显然,我与他的交往时间太短,在他众多的学生中,我太卑微,他的记忆一定是向那些闪光的同学敞开着。
我没想到,使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老师,我苦苦寻找了30年的老师,却对我毫无印象!
然而我很快平静了。对他来说,肯定和激励学生,这太平常了。他不会想到,自己的激励和肯定竟会使这个学生增强自信,走出自卑,彻底改变命运。这普通教师的平常之处,不正是灵魂工程师的神圣和伟大之处吗?
老师可以忘记学生,而学生却永远忘不了老师!
告别时,我嗫嚅着试图表明我的感激,但终于什么也没说出来。但此时我的心绪已恢复宁静,毕竟,我终于找到了寻找了30年的老师!
(作者为本报领衔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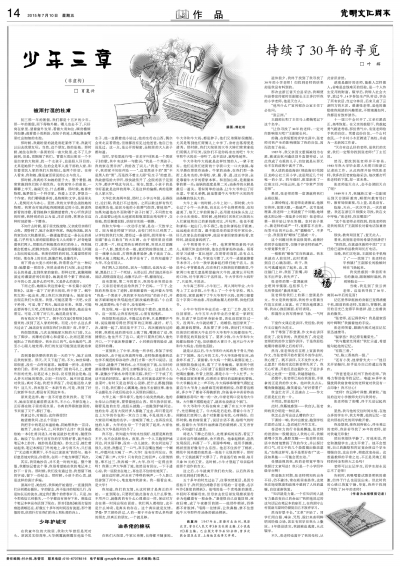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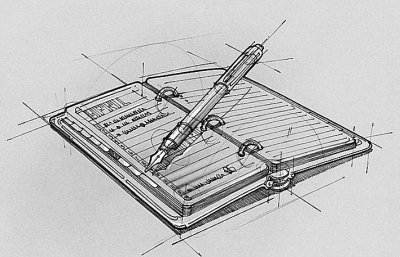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