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人类文明的“恶之花”,在政治和国家出现之前,战争就已经是人类文明的家常便饭。然而,随着政治和国家的发展,战争的规模、手段和破坏性也在不断变化升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6000万以上的死亡人数,在战争史上空前绝后。对于战争学者,首先要回答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不外两种观点:一种是理性主义战争观,即战争是国家、领袖、官僚机构或利益集团的理性的选择。另一种是非理性主义战争观,强调战争现象的感性一面:武士文化、竞技精神、荣誉与炫耀、集体心理——归根结底,文化是战争的根源之一。
英国战争学者约翰·基根是文化战争观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在文化论者内部的争论中,不同于以色列的马丁·范克勒韦尔认为战争文化是永久而普遍的,基根坚持认为,随着文化的变化,战争也会因之而变。这种观点使基根成为独树一帜的战争学者,也使他成为诸多批评的靶子。
基根历史视野中的盲点
基根因腿疾而无缘亲历战争,可是他却用一生来研究战争的历史。他在《战争史》一书中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战争文化观。开篇第一句,基根就表明了他与克劳塞维茨的势不两立:“战争不是政策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他认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创造了一种意识形态,从而改变了欧洲战争的性质:“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个异乎寻常和极其可怕的文化畸变,出自欧洲人在克劳塞维茨世纪作的一项无意的决定,那就是将欧洲转变成一个武士社会。”他认为这种文化转变是欧洲战争形态变化的根本原因。“我们将克劳塞维茨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识形态之父仍是对的,就像我们将马克思视为俄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之父是对的一样。”纵观人类战争史,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化仍是战争性质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得益于这种鲜明而“任性”的观点,他的书几乎总能成为热点,引来无数批评和赞誉。
基根的一系列战争史著作都一以贯之地坚守他的战争文化理论。其中《一战史》和《二点史》都称得上是史料翔实、视野宏大的传世之作。然而,《二战史》与《一战史》一样,暴露了基根历史视野中的盲点:他对两次大战的叙述,几乎全然忽略了中国。无论作为两次大战的参与者还是作为二战的重要战场,中国都不应被任何一部试图客观描述两场大战的著作所遗忘。在《二战史》中,中国战场只是被当作太平洋战场的局部性问题偶一提及。例如,他仅在“东条英机的战略困境”一节中简单交代了日本侵华计划,在描述缅甸战况时提了一句史迪威将军指挥的中国军队,在“日本在南方的战败”一节中用一页多的篇幅介绍了中国国共两党的行动,其中还有三分之一是关于“飞虎队”等援华美军的情况,如此等等。相比起一个中途岛海战就可以单列一节,整个中国抗战却只有寥寥几页的介绍,这不禁让人感到,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望远镜里,“远东”的景物只是可有可无的背景而已。
然而,西方中心主义不仅决定了基根世界观上的近大远小和矮化其他地区和文明的无意识心理,它还决定了基根战争理论的狭隘性,注定了他理解人类战争的努力最终不可能成功。在《二战史》的绪言中,基根再一次重复了他的战争文化理论及其对二战根源的理解。基根固然超越了那种认为1914年马恩河战役的偶然结果就决定了两次大战的幼稚观点,但依然没有跳出一种“欧洲战争”而非“世界战争”原因论的窠臼。模仿埃利亚特或韦伯式的社会史笔触,基根从欧洲的人口、兵役、财富和技术因素,也即“欧洲的军事化”开始了他对二战根源的探索。他依然强调人和文化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必不可少的人的品质,物质再丰裕也不能发挥什么效用”。由于兵役带来的平等感觉,自由而热情的士兵成为19世纪以来欧洲战争的重要因素。志愿兵的普及和人民的普遍武装,不仅使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得以成功,使1848年革命和德、意民族统一成为可能,最重要的是,也使欧洲浸泡在一种集体精神之中。在一战中失败的德国,产生了自由军团现象,有助于使国家成为一个大军营,使军队成为社会模式的理想样板。这种军事文化的极端发展,决定了二战的性质和面貌。
作为对一个侧面的强调,这种观点有其魅力,但它完全回避了现代世界战争发生的本质原因。由于基根忽视了资本和帝国主义的作用,他的理论只能部分地解释战争的“现代性”,却完全无法解释“现代”的世界战争。特别是,它只能适用于现代性发达的欧洲和北美,无法解释其他地区的问题。正是这一点,导致他在绪言中提出的理论与正文对战争过程的叙述之间存在脱节。也是由于这一点,决定了他对中国战场的忽视——在中国,是战争锻造了现代性,而非现代性决定战争。
深刻反思西方战争文化
尽管基根的战争理论存在严重缺陷,但在一个问题——对西方战争文化的批判上,他显示了杰出的洞察力。在《战争史》中,基根指出中国军事生活的“最经久特性是温和节制”,穆斯林战争文化也通过招募或雇佣专门的武士阶层从事战争而使战争方式保持着受限状态。其实这并不新鲜,长久浸淫于文明状态的多数地区,都产生了类似的战争文化,即战争之目的,止于屈人之兵。“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正如基根终生反对的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政治的目的不是摧毁,而是建构秩序。随着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产生了不同的战争文化。基根深刻地揭露了这个致命问题:“西方战争方式的胜利是虚妄的。针对其他军事文化,它已证明不可抵挡。可是转而针对它自己,它却招致了灾难,连同全盘毁灭危险。”西方的战争文化摧毁了西方文明中的最好的东西,即它的自由主义和乐观气质,“并且最终否定了一个命题,即战争是或可以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可见,能使克劳塞维茨论断不成立的,恰恰是西方自身的战争文化。
《二战史》继续了这种反思。美国为首的盟国提出了“无条件投降”。这个待遇对于法西斯战犯毫不过分,但是它也同样隐藏着危险的可能性。“无条件投降”似乎是美国人的最爱,早在美国内战中,格兰特将军就对南方军队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的屈辱要求,终结了战败者不失尊严地离开战场的传统。一战后,虽然没有无条件投降的口号,但是协约国对德国的报复性惩罚不仅摧毁了德国国内建立稳定宪政的可能,也开启了下一次战争的序幕。正是这种追求“虚妄”胜利的战争文化,间接导致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兴起。用无条件投降来威慑罪恶固然应当,但却不能指望它消除未来战争的阴影。更可悲的是,当西方国家面临冷战的新威胁时,同样的战争文化,即全面战胜苏联的要求,又使它们中止了对日本的清算。
二战后的美国到处追求“虚妄的”胜利。除了在朝鲜和越南之外,这种战争文化畅行无阻,摧毁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也使美国人在陶醉中将之推向极致。终于,美国在中东又遇到了泥潭。由于违背了“制衡”而非“全面胜利”的传统战略智慧,追求不切实际的军事目标,美国最终只得收获“敌人的敌人还是美国敌人”的尴尬局面。
《二战史》一书出版于1989年。当时的中国,对于战略家阶层之外的普通西方人来说,确实不甚重要。作为一个军事史家,基根对中国的忽略既是他自己理论的逻辑结果,也是当时西方文化氛围的产物。如果基根能在今天修订此书,也许他会自觉到这个问题。如同西方学界受中国发展的触动而对国家能力、协商制度和中国模式的“重新发现”一样,基根也许同样会“重新发现”中国的抗战对于军事史和世界格局的所具有的伟大意义。历史不会被遗忘,中国将举办的二战胜利70周年阅兵,算是这个意义的再一次郑重呈现吧。斯人已逝,经典犹存,此书中片面和深刻使其对今天的读者仍大有启发。(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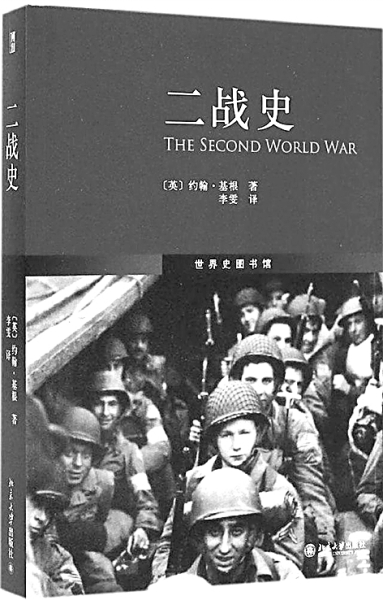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