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目睹却无视水的辉煌与苦难,当水被污染,水有撕心裂肺的痛感吗?水的死亡是土地的死亡,是人类以及万类万物的随之消亡。
● 我们天天为经济增长费尽心思,而有多少人曾为江河水忧心忡忡?没有可持续的流水,哪有可持续的未来?
一
溪涧小沟江河水,我儿时的水。
人之初也,我在崇明岛西北角一落地,便落进了蜘蛛网一般的河沟水网中,于是便终生湿漉漉,涛声水气涌动于血脉故。崇明岛三面为长江环绕,大江浩渺西来,于岛的西端分出南北两支,如母亲的双手怀抱东西狭长如卧蚕的沙洲汇合于东滩,再与东海交互相接。崇明西部的崇西水闸即为一岛之水口,引汹涌江水滋润农田家园。然何能流进千家万户、仟佰田亩,使人和地、青苗芦苇螃蟹均能得而享之?崇明岛的水集江海关系、水沙关系、水陆关系而极为复杂,要而言之,拒东海咸潮于大堤之外,引长江淡水于岛上田畴,修堤筑坝,开沟凿河,对崇明农人而言,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称崇明岛的水利网络如蜘蛛网实在相宜:把崇西水闸引进的长江水分流至运河、横河、竖河就是浩大工程了。但江水既到竖河而农田、农家,还仍只能望水止渴。横河、运河等较大的河为“官河”,由政府组织人力开掘,为使江水能灌溉饮用,农人一村一社自凿者为沟亦称民沟,到1984年岛上仅横河623条,民沟15080条(参见拙著《崇明岛传》,作家出版社2009年出版)。崇明河沟中最具特色的是宅沟,一姓一宅,沟以绕之。民沟连接农田村落,宅沟与民沟通,民沟与竖河通,竖河与运河通,运河与江海通,西引东排,如是流转,无地可荒,无水不活。那是岛上数以几十万计的大河小沟的地表水面,春秋夏日,水汽蒙蒙,水波不惊,清气荡漾,芦苇守望河沟,游鱼追逐涟漪,在回想的风景中,我竟茫然于不知如何言说。
二
冬季是枯水时节,河沟不再丰盈,枯水成冰,雪阵漫漫,芦苇枯黄。儿时面对此种景象,似曾有过淡淡的忧伤。于今想来,冬日却是大河小沟敞开的季节,敞开着河沟的期待,期待一年一度的疏浚,也敞开着河沟的秘密,河沟的秘密就是河泥——水与土交互渗透后的一种物质。水不仅“善下之”“利万物而不争”(老子语),水还无声无息地制造河泥,黑色的柔软的极富营养的河泥,洁净的水制造的河泥也洁净。没有比崇明岛的农人更珍惜疼爱河泥的了。他们赤脚或者穿着草鞋劳作于河沟底部,深入河泥之后再挖掘搬运至地表,层峦叠加,经过一个冬季的冰雪严寒之后便冻结,泛出一层乳白色,河泥于是成为充溢生长力的肥料。开春后便置于小麦地的陇趟间,以农具拍成细小碎末,簇拥麦苗,再静候春雨,河泥释放肥力,小麦开始拔节。东宅上的才元好公说,他能听见小麦拔节的声音,村里的孩子们为此惊讶羡慕,便去麦田屏息以听,惜乎只闻见风吹麦叶声。
挖掘河泥时也是孩子们的节日,因为河泥中有芦根,芦根雪白、有节、甜脆,等不及回家洗干净用手一擦便大嚼,芦根的甜味与河泥芳香交织,并且黏滑,美味也。吃不完的便抱回家,洗净后慢慢吃或者晾干,到镇上卖给中药铺,可得1毛钱几分钱。河泥的黝黑、芦根的雪白,便成了我记忆中故乡河沟的别一种写照:水不再盈,鱼不再游,唯黑白而已。黑者泥也,白者根也。有泥有根,何愁不生?有根有泥,即为大地。
何谓大地?“生而不有”,无极之地也。
三
河泥使我想入非非,制造河泥的河沟,那水波游鱼不妨当作表象来品读。水,渗入土中与土结合便有了无穷的创造力,但丰水时节,我们看见水流进了田畴,听见了庄稼地吸水时的“滋滋”有声,却看不见水在河沟中与土结合制造河泥的过程,不知道是土吸引水?还是水寻找土?结合之初想必愉悦,是深藏不露的愉悦,是温柔细腻地铺陈于河沟底部成为基础的愉悦。如此等等,只能是猜想,或许可以这样说:河沟类似上帝的作坊。
上帝的作坊里我看见了农人的手,农人的劳作,挖掘河泥的冬日,使水成为活水的沟通之物出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了:那是一根根打通了的粗大毛竹的竹简,挖掘河泥的同时,农人还要清理或更换竹筒,竹筒中也有河泥,甚至还有黑鱼。
竹筒蛰伏于河沟相连处。
竹筒静悄悄,沟通与连接不必喧哗。
竹筒是美妙的,活水之道也。
水从竹筒里流进流出,流进流出的水是活水;鱼也从竹筒里流进流出,流进流出的有鱼类中最华丽的鳗鱼。鳗鱼学名鳗鲡,曼妙美丽之谓也。猜想起来,那些花鲢、鲫鱼或各种杂鱼青虾之类,它们进出竹筒,不过是好玩,想体验一下沟河有别,竹筒幽深,是短暂的出游,即兴为之。对鳗鱼而言,这千根万根连接大小水体的竹筒,却是生命通道了。鳗鱼在水生生物中对水质的要求之高近乎苛刻,它绝对拒绝水体污染,甚至以死相争。在20世纪70年代初叶之前,崇明地表水掬之可饮,民沟竖河、横河,乃至宅沟中均有鳗鱼生息,鳗鱼好在河泥中挖洞穴居或者以竹筒为养生地,鳗鱼通体光滑较鳝鱼粗壮长大,以其身段柔顺能自然弯曲故,亦称“弯鱼”,然鳗鱼之弯曲却是有捕鳗者得手后的爆发,先弯曲后伸张,力大无比,溜之乎也。我又怎能责怪儿时的无知呢?看见捉鳗鲡人捉鳗鲡,看见鳗鲡弯弓发力而重获自由,却不知去向何方?原来,鳗鲡在洁净的淡水中生活三年,然后性成熟,体色苍黑,下腹部两侧生出金色光泽,胸部呈浅红色,此华丽之由来也,人称“婚姻色”。
这时的鳗鱼焦虑而急切,它们将远行。霜降前后便在夜色中寻找入海通道,以每夜30至60海里的速度,不眠不食不息,奔向北纬20度以北、28度以南的琉球群岛海域,在水温约10℃—17℃,盐分35%以上,500米左右深的海水中产卵。鳗鱼,一条鳗鱼,集群的鳗鱼因何能从崇明的河沟水面远游至琉球?端赖竹简也,可以沟通,可以连接至琉球群岛。人之爱竹,人知之,鳗之爱竹,人不知。鳗鲡为一次性产卵,一尾雌鳗产卵700万至1300万粒,产卵毕,成鳗死。鳗鱼卵在海水中漂流孵化,又回到近海崇明岛东滩,时为15毫米左右的鳗苗,再溯河而下于夜间寻找岛上竹筒连接的沟河,淡水家园之一宝也。
这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了,这是水泥尚未全面登岛,水泥坝尚未重重阻挡,沟河淡水洁净时。而今崇明地表水大多污染,尤其是民沟、宅沟无水不污,水体之间沟通断绝,岁修不再,使游鱼相望于道,鳗鲡直奔远海的毛竹筒,不复见矣!
四
水与泥还有梦。
加斯东·巴什拉的《水与梦》使我惊叹,他说:“一滴有威力的水足以创造一个世界并驱散黑夜。要梦想巨大的威力,只需一滴在深层中想象出的液体,如此有朝气的水是一种萌芽,它赋予生命以取之不尽的飞跃。”在形而上的意义上,老子《道德经》说水,可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我们总是会把形而上的一切弃之如敝屣,而只是以“水利”“水害”言之,并付之修筑累累高坝大库,让江河水不再自由流动。
流动的水流动着水之梦、梦之水。
凭我回想中获得的儿时经验,水之梦或者梦之水的烂漫多姿,还必须要与土结合,也就是说把水在土中搅拌、揉捏,手指深入泥团之中,再揉捏,揉捏成各种物体的形象,那是雕塑的开始?玩水,玩泥团,水和泥团是我少小时最可爱的玩伴,母亲及乡邻在地里劳作,我便坐在田角玩泥。前文所说的联想那是后来的事情,但是留存于心中的是水的清凉以及双手进入泥团并揉捏的快感,这样的快感从何而来?孩提时代虽然未解却已经感觉到的是:水与泥团具有母性,水召唤着已来和未至的生命,而泥团因为汲取水分之后而饱满、嫩滑细腻,触摸揉捏这嫩滑饱满时,我的手已经伸向至生命的原初和母亲。
在地头玩泥时,正值春耕时节秧田灌水,春水所至,地里冒出无数的蝼蛄,水淹之下落荒而逃。我问昌囝阿哥:“它们原先在地里干吗?”“自己钻洞埋着睡觉。”“水会淹死蝼蛄吗?”“喝足了水,它就会跑。”“跑到哪里?”“高田,要不就钻到你裤裆里。”崇明农田有低田高田之分,低田种水稻、油菜,高田种小麦、棉花,其间相隔一条田埂,田埂路上有马斑草、花被单草、车前子和马兰头。我赶紧伸手摸索裤裆并无蝼蛄,便放心捏泥团,手捧起湿漉的土块时,能闻到田野湿润以后的泥土味、香味。已为水濡湿的土块变得柔软的土块,却仍是土块,然后手指伸入其中开始揉捏,反复揉捏,此一过程使水和土愈加紧密结合,手参与其中,制作并改造水和泥的形状,激发一个顽童的想象力,揉成各种泥团,制作成碗、小房子,以及我记忆中的在母亲怀里吮奶时的两个泥团乳房,“乳房”顶部又加一小粒泥团,“乳头”是也。我的泥团,我的作品,手深入泥团被泥团淹没,揉捏泥团揉捏出各种物事的快感,直至写大地湾彩陶、良渚黑陶时又被唤醒:使水与土结合成泥团,然后深入揉捏,创器之始。人的手成了抚爱之手,人之为人,创制并使用工具,由此而始也。
五
我离开故土浪迹天涯,跋涉山川大漠,除了追名逐利之外,大约就是崇明岛上水和沙的引领了。崇明的泥土均为长江几千里挟裹而来,经过几番大浪淘沙以后的一路尘沙,崇明确切的称谓应是:世界第一河口冲积沙岛。沙从何来?大江一路携来淘泥成沙,层层堆垒,农人垦之肥之成田成土,长江西来之水成就了崇明沙岛,聚沙成岛,妙哉。更奇妙的是水和泥成为一体的过程,包容不足以言之,还有渗透黏合。水有黏性吗?水可黏合万物吗?农人平整后的秧田、稻田,水面光滑,田土如玉,农人播撒谷种,水若肤层,泥似肌肉,水何言哉!泥何言哉!万物生矣!众生得而享之矣!
可是水从何来,都说“河出昆仑”,昆仑在哪里?昆仑之河因何而出?因何奔腾不息却让泥沙沉积,造出一个崇明岛来?
行行复行行,道路阻且长。我到了青海,出塔尔寺过日月山,游青海湖,再行,渐入大野,有水沟中的玛尼石,有煨桑台,有经幡塔,有风马旗;又行,荒草稀疏,海拔渐高,这是可可西里,三江源区了,可以远望雪山冰川,茫然连绵起伏腾挪,冰川在阳光下与雪山交相夺目。我在心里揣着一张冰渍湖沙化的图片,从高倍望远镜所见冰渍湖已是砾石湖,冰川后退,雪线上升,无可置疑。我在三江源还遇见了一个牧人,名叫次保,一边放牧一边画水彩,开始是为上世纪70年代的风景吸引,他以水彩作速写,没有一点学院派的技法,只是雪山皑皑,芳草无际,一抹又一抹的绿色,浓得化不开,其间有红蓝白交错,红蓝是野花,白得娴静而又成群结队的是次保的羊,或者闻香吃草,或者饮水溪畔。80年代后草地斑秃,90年代后地表裸露,小溪将枯……“我不能再画了,心碎了。”次保悲叹。
那是江河源区的生态危机,我们天天为经济增长费尽心思,而有多少人曾为江河水忧心忡忡?你要去三江源,你要登高,你登高一望便明白:没有可持续的流水,哪有可持续的未来?
六
我从江之源,重回江之尾。先到石鼓,访金沙江,石鼓金沙江两岸砾石满山坡,十里无一树,但闻机声震响,原来是金沙江的梯级开发——在中国西南众所周知的地震带上——随江水巨大落差阶梯状筑大坝高库,其总容量远远超过三峡大坝,对地质、环境、水生物种有何影响?论证的专家们说“没有影响”!你懂的。
长江频发枯水,万船搁浅之外,下游海水倒灌吾土首当其冲。层层报批后要等待命令开闸放水。由此可知:一条天然的中国第一巨川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由人为控制,所谓人为控制,包括大坝、高库、闸门、发电机组、人的权力。水需要乘势利导,都江堰之不二法门。此种利导,是人和地势及水的协商和谐,高坝大库则霸道之谓也。回乡,正遇上海水倒灌,茶水中有苦咸味,苦咸的水,我儿时的沟河清水,后来污染的水,死水,长满绿藻发臭的水。加斯东·巴什拉有言:“水也是生与死亡间一种柔顺的中介。”忽然想起儿时邻村的一个小伙伴落水而亡;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三峡江轮上见过一个裸体的女性沉浮在波浪间;我在北大做工农兵大学生时接到噩耗,我疼爱的长得清秀高挑的侄女云美因为爱情喝“敌敌畏”而死……
我痛恨“敌敌畏”。因为农药及化肥的过量使用日积月累的后果是,到80年代崇明地表水除去大运河一律污染,污染的水渗入土地,地下水亦污染。我在暑假时还乡,宅院里多了一口井,何故?母亲说民沟的水不能吃了,打出来的井水也不能吃。河沟岁修不再,水体从此无往来,又何故?分田到户后只管自己的田,农田基本建设再也无人问津,农村的衰落是由此开始的吗?
水啊水!2013年3月26日,国家发布水利普查公告称,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为22909条,相比50年代以1∶30万地形图的计算少了2700多条,几千条河流的消失啊,浩浩荡荡的死亡。中国70%的江河水系已被污染,淮河居首,海河、辽河、黄河次之。所有流经城市的河段90%为重度污染,3亿农民喝不到洁净水。农村水染从点源而面源,由此引发耕地污染。2015年《参考消息》转引香港《南华早报》说:2014年政府部门发布的公告称“全国19.4%的耕地污染物超标”,除去农药化肥,“铅和镉是最主要的污染物”。污染物是怎样进入耕地的?被污染的水排放流淌故也。污染之地稻麦无以立足,稻麦无以立足,农人无以立足,农人无以立足,吾中华民族何以立足?有一个数据不能不三复斯言:地球表面含有洁净水的十厘米厚的地表土层,两千年方可形成。清水之美也,成土之难也,水与泥之秀于万物者尽在此也。
七
西哲认为世界有四种基本本原:火、土、水与空气,大体上与中国古代的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合。本原、五行云云,简言之物质也,是最普通的物质,最普通的物质是最基本的物质,最基本的物质是最宝贵的物质。而水的特殊性在于:它渗透、参与并黏合其他事物。起火的木柴中有水,石块中也有水。水之为物也,有母性,融万物,不惜牺牲自己。加斯东·巴什拉之言能不让人伤感?“许给水的存在是一种眩晕的存在……它每分钟都在死去,水的苦难是无止境的。”
我们目睹却无视水的辉煌与苦难,林木葱郁,瀑布飞泻,稻麦秀穗,野花怒放,蜜蜂成群,大野流香,水之美也,其非辉煌烂漫乎?而询问,体察水之苦难的更是鲜有人在了:淮河是从一滴水进而一片水再进而一河水开始污染的吗?当水被污染,水有撕心裂肺的痛感吗?清水成为黑水,活水成死水时,没有安魂曲,只有癌症村。水的死亡是土地的死亡,是人类以及万类万物的随之消亡。
水啊!泥啊!少小时揉捏过的乳房状的泥团啊,谁不曾吮吸过母亲的乳汁啊!泉源啊!
“你的泉源不是泉源,是本原本身。
是原初物质!是母亲,是我生命的母亲”(克洛代尔《五大颂歌》句)。
(作者为诗人、散文家,曾获中国图书奖、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首届中国环境文学奖、冰心文学奖、郭沫若散文奖,其代表作《伐木者,醒来》为中国自然文学的开创性作品)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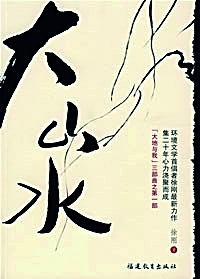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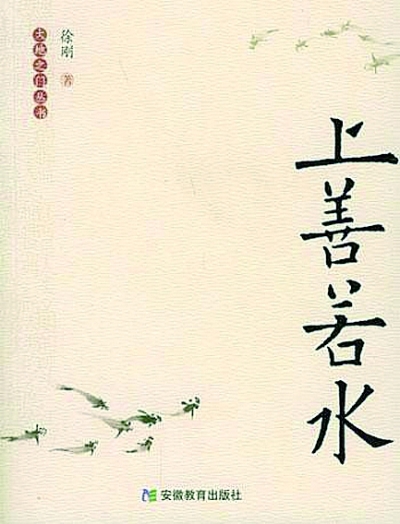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