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信出版社出版了安伯托·艾柯的三部重要作品:《误读》《带着鲑鱼去旅行》和《开放的作品》。与艾柯在全球热销1600万册的小说《玫瑰的名字》相比,《误读》《带着鲑鱼去旅行》堪称他的奇思妙想文章大集结;两本小书以杂文的形式,将艾柯天马行空的性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开放的作品》是艾柯探讨西方现代艺术、文学的最重要著作,也是文艺界划时代的一部先锋作品。
艾柯是谁?
安伯托·艾柯,享誉世界的符号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美学家和小说家。艾柯的学术研究纵横古今,小说随笔睿智幽默,著作横跨多个领域,并在各领域都有经典建树,是跨越雅俗的知名人物。
1932年,艾柯诞生于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蒂州的亚历山大,这个小山城有着不同于意大利其他地区的文化氛围,更接近于法国式的冷静平淡而非意大利式的热情洋溢。艾柯不止一次指出,正是这种环境塑造了他的气质:“怀疑主义、对花言巧语的厌恶、从不过激、从不做夸大其词的断言。”艾柯是后现代文学批评的奠基人之一,更是符号学领域的开拓者。1971年,艾柯在欧洲最古老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创立了国际上第一个符号学讲席;4年后因发表符号学权威论著《符号学原理》,艾柯成为博洛尼亚大学符号学讲座的终身教授,以符号学家的身份声名远扬。有评论家说,阅读安贝托·艾柯,对我们的精神痼疾而言是一种解毒。艾柯的写作范围无所不包,诸如足球、咖啡壶之类看似“无脑”的话题,在他笔下变得既有趣又深刻。他是一位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全才,至今出版的各类著作已达140余种。
艾柯的“创作故事”
艾柯的创作生涯也许源自家族的馈赠。艾柯的父亲买不起书,一家人努力工作才能勉强维持温饱。于是,艾柯的父亲就到街边的书报摊去,站在那儿看书。当报摊老板表露出不耐烦的神色时,他就换一家报摊,继续读那本书的第二部分……艾柯的母亲谈吐优雅,有高贵的意大利范儿。她很早就不上学了,但写作很有文采,朋友们都请她代笔写信。艾柯回忆是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纯正的写作品位以及最初的文风。但对艾柯影响最深的是他的祖父。祖父在退休后帮人装订图书,那些带有精美插图的戈蒂耶和大仲马创作的十九世纪流行小说——便是艾柯最早接触到的书籍。在祖父离世后,那些未装订完的书都放进了一个大箱子,有一次,小艾柯在地窖里偶然打开了这个箱子,这如同打开了一座珍贵的宝藏。
艾柯在少年时代开始画漫画、写小说。他自称是“完美主义者”,希望自己的“书”看起来像已经印出来的一样,因此费尽心思编写扉页、摘要,还配了插图。这些工作对一个孩子来说非常累人,但艾柯认为这段回忆非常值得留恋。与今天大众所熟知的小说家身份不同,艾柯在48岁之前一直是世界知名学者,之后才开始写小说。但在他看来,自己前半生的学术工作也在“创作故事”。1978年,一个朋友建议艾柯写一个短篇侦探小说,艾柯婉拒了,而一个关于19世纪修道士的长篇小说却在他脑海里展开。两年后,艾柯最负盛名的小说《玫瑰的名字》面世。
艾柯的“阅读经验”
艾柯认为一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本,但它在对多种解读开放时,告诉了我们某种无法改变的东西。假设你正在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你极其希望娜塔莎不要接受可怜的无赖安德烈的求婚;你希望那个了不起的王子一般的安德烈不要死去,让他和娜塔莎能白头偕老。如果你有一部超文本的或交互式的《战争与和平》,便可依你所愿重写自己的故事;你可以创造无数的《战争与和平》,让彼埃尔·别素霍夫杀死拿破仑,或是按照你的意愿,让拿破仑最后击败库图佐夫将军。多么自由,多么激动人心啊!但一本已经写出的书,其命运已经被作者的决定所确定,我们无法改变宿命。一本超文本的和交互式的小说允许我们去实践自由和创造,艾柯希望这种富于创意的写作活动能在未来的学校中实现。
同样地,在《悲惨世界》中,维克多·雨果给我们提供了滑铁卢之战的美丽描述。雨果的滑铁卢与司汤达的截然不同,司汤达在《巴马修道院》中,透过他的英雄的眼睛看这场战役,而这位英雄的角度是在事件内部,这就不能理解其复杂性。相反,雨果从上帝的视点来描写这场战役,跟从每一处细节,让他透视整个场景的叙述居于统治地位。雨果不仅已知道发生了的事,而且知道可能会发生的,以及实际不会发生的事。的确,某人可以重写滑铁卢,但是雨果的滑铁卢的悲剧之美,正是让读者感到事情并不以他们的意愿为转移。悲剧文学作品的魅力,是让我们感到书中的英雄有逃脱其命运的可能,但却未能遂愿,原因在于他们的脆弱,他们的骄傲,或是他们的盲目。这就是每一部伟大的书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可重写的书是存在的,因为其功能是教给我们必然性,只有在它们得到足够敬意的情况下,才会给我们以智慧。
艾柯的图书馆
艾柯的寓所内布满了迷宫似的回廊,回廊上排放着高及屋顶的书架。这里共有三万卷书,而在他的庄园里还有另外两万卷。是摆设吗?不是的!许多书因经常翻阅已经陈旧磨损。估计艾柯对访客们惊呼的“你真的都读过了吗?”不胜其扰,在《带着鲑鱼去旅行》中,他以戏言应对:“哦,这些只是我本月底前要读完的书,其他都放我办公室里了。”
爱以深奥典故及冷知识折磨读者的艾柯,不但不为大众所恶,反而受到追捧,在现代社会简直是独有的现象。有人甚至认为这是读者有受虐倾向,“缘于门外汉读者对自己无知所感知的羞耻,进而转化为对作者博学轰炸的天真崇拜”。对此艾柯回应道,每位学者和作家的日常工作都带有剧场性质,他并不是为了把知识堆在读者面前,而是希望引发读者自己的思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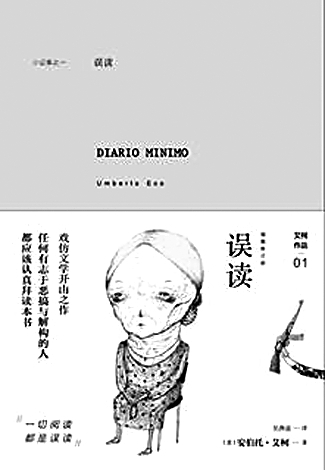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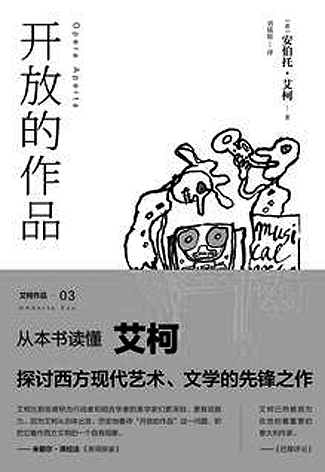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