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秋,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撰写的《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一书问世。该书的长条稿样先经维希当局审查,后由纳粹宣传局授权,最后才被送往印刷厂正式刊印。按照当时的规定,公开发行的书籍要盖上“希特勒小国旗”形状的印戳。在法国沦陷时期,费弗尔还出版了其他著作,它们也经历了类似的程序。相比之下,这一时期年鉴学派的另一位创始人马克·布洛赫未有任何著作“正式”出版。他把笔当枪使,走上公开反抗纳粹的道路,最终因之而失去了生命。对于布洛赫的“激进”言行,费弗尔似乎不太认可。他曾写道,付出生命的代价,并非是通向精神伟大的唯一道路。那么,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费弗尔选择走的是何种“精神伟大”之路呢?
一战爆发时,时年36岁的费弗尔被征召入伍,成为一个步兵团的中士。除了几个月因病养伤之外,他一直奋战在抗敌前线上,因此获得多枚荣誉奖章(如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19年,他以一名机枪连队长的身份复员。与费弗尔的经历相似,布洛赫先是一个步兵团的中士,后来成为一名情报官员,到1919年亦以队长的身份复员。1920年,他们均前往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由此开始了20多年过从甚密的友谊生涯。尽管二人性格差异较大,但都支持共和民主政体,思想上接近当时左翼的社会党。由此可见,费弗尔在人生格调上是与布洛赫相通的,其爱国情怀毋庸置疑。
既然如此,如何解释他们在法国沦陷时期的道路“歧异”呢?要对这一问题做出合适的回答,我们需将个人置于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1940年6月22日,法德双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标志着法国本土全面沦陷。根据停战协定,法国军队宣布解散,并交出所有军事装备;法国只能拥有一支10万人的维持治安的部队。值得注意的是,停战协定并未向法属海外殖民地提出要求,也就是说,法军若坚持抵抗的话,并不缺乏根据地。然而,由于殖民当局纷纷倒向维希政府,法国境内任何有组织的军事抗争活动也就化为泡影。法兰西要获得民族解放,相当程度上需依赖于外部形势的好转,即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军事进展。
对此,费弗尔和布洛赫心里都十分清楚,只是不知道国土沦丧究竟会持续多长时间。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和民族的悲惨命运,他们一度迷惘过,布洛赫甚至想过逃亡美国,只是手续出了问题而未能成行。他们都在思索,还有什么事业有益于法兰西民族及其未来。此时,他们找到了目标上的契合点,那就是年鉴史学(费弗尔称之为“年鉴使命”)。早在1939年10月,《年鉴》杂志的社论中就提到:如果法国万一陷入不幸,杂志也不能放弃其客观性;要以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为榜样,将德国人抛在脑后,致力于杂志的伟大事业。皮朗是一位深受费弗尔和布洛赫敬重的年长学者,在一战期间被德军囚禁在战俘营里,恰是在这种环境里,他写下了举世名篇《穆罕默德与查理曼》。
《年鉴》杂志为何如此重要?因为它的创办,既是学科发展内在逻辑的结果,更是法、德民族在学术竞争上的产物。众所周知,历史学的科学化是在德国率先完成的,然后逐渐向世界其他国家扩散。20世纪初,主导法国史学界的,正是由德国兰克学派所倡导的客观主义史学。这种史学注重国家、政治和司法等话题,强调史家对档案材料的依赖,固守于一己学科之内,缺乏与其他学科的沟通。对于这种狭隘的历史学,费弗尔和布洛赫均表示不满。他们认为,社会、经济和文化是历史的重要方面;一切可以服务于史学研究的资料,都是有价值的;应大力开展跨学科研究,以更好地理解过去与当下。正是基于这一史学理念,他们二人于1929年创办了一份带有“反叛”色彩的史学杂志,即《经济社会史年鉴》,简称《年鉴》。自创刊起,该杂志的宗旨就不是办成一份普普通通的学术刊物,而是企图占据经济社会史领域的话语权。当时,一份名为《社会经济史季刊》的同类刊物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它由德国和奥地利学者于1903年创办,虽然该杂志声称是一份跨越民族界线的国际性刊物,却带有明显的排法色彩。对此,1933年费弗尔致信荷兰著名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年鉴》必须取代《季刊》,因为后者几乎变成了一种完全由德国人掌控的民族性刊物。
然而,1940年6月法国沦陷后,这份苦心经营的杂志却面临停办之虞。根据纳粹宣传局的规定,凡是出自反德分子、反纳粹分子、犹太人、共济会人士和共产主义分子等手笔的,均不得出版。学术杂志也要接受严格审查:编委会成员的身份务必“干净”;不得刊登列入“黑名单”之人的文章;不得提及这类人的著述等。由于这类规定,犹太学者亨利·贝尔创办的《历史综合评论》被直接勒令停办,而另一权威杂志《法国新教史协会会刊》也遭遇同样的命运。《年鉴》杂志亦受到冲击:在它的编委会成员和供稿人当中,有不少属于身份“不干净”之人。
首当其冲的是布洛赫。由于他是犹太人,不仅早些时候被逐出了索邦大学(1936年获得该校经济史教授席位),此时还得面对与这份杂志的关系问题。根据当局的规定,《年鉴》杂志要么停办,要么“讨人嫌”之人退出。针对这一情况,布洛赫认为,如果《年鉴》不能以其真正的面貌问世,还不如断然停办。他在致费弗尔的信中写道,“我不想看到的唯一事情是,人们说,‘马克·布洛赫被赶走了,而《年鉴》杂志则照办不误’。我不想看到这种局面,想必你也如此。”他想提醒费弗尔,如果自己选择退出,仅是杂志日益失去自由的第一步。
费弗尔的立场是,“《年鉴》杂志必须存在,必须。”他向布洛赫陈述了两点理由:第一,这一杂志是“一份法兰西民族的杂志”,它的停办意味着“法兰西民族一种新的死亡”。第二,在纳粹德国的铁蹄之下,许多法国民众需要精神上的支撑,而《年鉴》杂志作为一种公共平台,可以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他也提醒布洛赫,当年伏尔泰就是在不自由的环境中写下伟大著作的。因此,他向布洛赫提议:为了避免厄运,他自己必须成为《年鉴》杂志的唯一所有人和唯一主编,不过保证决不会在杂志的内容上做出任何妥协,后者还可以化名为该杂志撰稿。最终,布洛赫选择了妥协。
为了维持这份杂志,费弗尔除面临资金短缺和人手不足等问题之外,还得经受当局审查制度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正是在这种处境下,1942年改名为《社会史文集》的《年鉴》杂志(为不定期出版物,可以减轻当局对其的审查力度),仍基本坚持学术的独立性和客观性。除了学术的尊严得到捍卫之外,费弗尔的一些举措可谓大胆:继续起用遭当局明令禁止的年鉴成员,如布洛赫化名为“富热尔”,继续为杂志撰写论文和书评;着力提携一些学术新人,如杂志在1942年的“个人信息”栏目中,特意报道了身处德国战俘营的布罗代尔正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一事,当时他尚处于学术的成长期。由于这些不寻常的举措,费弗尔不仅为当时的知识界提供了一道不一样的文化风景,而且为二战后《年鉴》杂志的顺利过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战结束后,年鉴史学迎来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1946年,杂志刊名又由二战时的《社会史文集》改为《年鉴:经济、社会与文明》,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气息。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史学的推动工作开始有了一个强大而稳固的组织基地——新成立的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部,费弗尔担任该部的首任主任,1956年布罗代尔接替其职。在二人强有力的领导之下,年鉴史学逐渐走向世界,最终在20世纪的国际史坛中形成一枝独秀的局面。因此,学界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如果说19世纪是“兰克史学的世纪”,那么20世纪是“年鉴史学的世纪”。而在这一过程中,年鉴史学的创始人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布洛赫的为国捐躯,彰显了年鉴学派的人格魅力;正是费弗尔的“忍辱负重”,成全了年鉴史学的伟大事业。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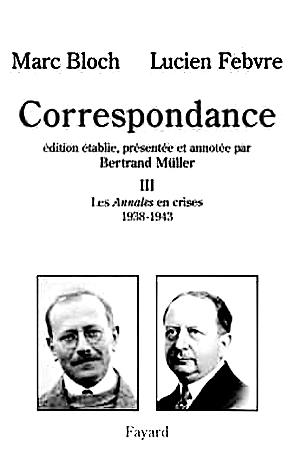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