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梦牵魂绕的家园,在美丽富饶的华北大平原上。那是一个让我深深眷恋的小村庄,听老辈人说:在明朝燕王扫北时,从山西洪洞县老槐树下,咱村,是被官兵用绳拴着先人的脖子,还拿刀逼赶着,在凄风苦雨中,拖家带口,强行搬迁过来的。老祖宗,在这上无片瓦下有立足之地的滹沱河边上,寻找了一处长满野草的河湾儿,落下脚扎了根。在这片荒凉、贫瘠、又多灾多难的黄土沙滩上,一代又一代村里人,娶妻生子,繁衍生息,好不容易才把祖先的血脉流传到了今天。
我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出生的村里人,从大跃进那个特殊的年代走来,现在已是人到中年,感觉时光流逝的速度,比贼星在天上飞还要快,回首眺望着那条我从乡村走进城里来的路,心里感慨万千。虽然,我离开儿时的家园已经30多年,但是,记忆深处清晰的画面,仿佛又在眼前回闪:早春的窗外,抬头望去,令人心爽神清,暖脸儿的南风静悄悄吹来,唤醒了沉睡的土地,忙了耕牛绿了杨柳,催春的布谷放开歌喉,筑巢的紫燕翩翩飞来。在微风细雨中,伴随着生产队里集合的钟声,从村街里走出了一群又一群赶春抢墒的庄稼人,他们满含着深情和祈盼,双手把希望丰收的种子撒进了新耕耘过的土地。
在大人们忙春播的黄金季节,自然,村里的孩子们就少了些管束和斥责,都像放开了笼头的马驹,在村里村外四处跑着撒欢生事。我们那群学龄前半不大的男孩儿,在村里捣乱淘气是出了名的招人烦,整天疯玩,不是爬树拧柳笛儿、翻墙捉猫猫,就是到老河沟里开坷垃仗,有时也围着石碾台,摔泥巴捏小人儿,还有什么猪八戒背娶媳妇、过家家的戏码也经常上演,连村里顶老实听话的光腚娃儿,也会跟在串村走街的小商贩屁股后头乱起哄,闹傻样儿,看热闹玩。刚傍黑时,隔三差五的,邻村来买鸡的二大娘,肩挑着两只竹篓,一双大脚板迈着四方步,边走边喊:钱买——鸡来哟。她这一声洪亮悠长的吆喝声,立马就喊出来了一街的小孩儿。二大娘的话音未落,紧接着,村口又响起推独轮车的白胡子破烂王那苍老的声调:乱头发——换洋针,猪骨头、旧套子——换瓦罐的——来了。随后,细长脖子里挂着柳条筐的是乔眯糊,他眼神不济,也不甘示弱,可着沙哑的嗓子猛劲喊了起来:香喷喷的哟,刚出炉的热烧饼儿。夕阳西下,村里的淡淡炊烟,开始袅袅升起,三五个沿街行走的小贩,一声接一声音调各异的吆喝声,混杂着孩子们的应答和戏闹声,给村里人的生活增添了几分热闹情趣。
在很早以前,从老辈人那里传下来一条不成文的习俗:村里谁家不管是生了胖小子还是俊闺女,据说,先得起个小名把阎王爷弄迷糊了,半路上就夭折不了,这孩子才能长大成人。因此,男孩叫大牛、二狗、三蛋、蛤蟆、老鼠、酱巴枣的满街跑;女孩叫黑丫、臭妮、春草、杏枝、枣花、鸭梨的随处可见。这些个小名叫起来好玩顺嘴又内含着亲昵,因为都是一条街上跑着玩泥巴的光腚娃,在称呼上谁也不知道个讲究,少小无猜,心里单纯又透明,互相之间,不掖不藏,那真是好起来不分你我,两人能伙穿一条裤子,红了脸也是针尖对麦芒,寸土不让,但是,吵过打过骂过哭过了之后,该玩还玩该闹还闹该笑还是笑,谁都不往心里去。
那年夏天,有几个伙伴正在河边玩耍,眼尖的二卯,看见鸭梨刚过门的新嫂子,穿得光光鲜鲜,顺着乡间小路向村里走来。他灵机一动,冲身旁的鸭梨一挤咕眼,就跳起脚拉开了唱腔儿:小哥哥,娶嫂嫂,娶得嫂嫂手儿巧,拿上剪刀把布绞,三天缝个裤裙腰。鸭梨拿给哥哥看,看得哥哥脸红了,跑进屋里打嫂嫂,枕头打得咚咚响。嫂子笑得格格格,鸭梨笑得说不成,哥哥哥哥不知羞,舍不得嫂子打枕头。鸭梨见二卯当众耍戏她,小脸羞红瞪圆了眼,从地上拾起根树枝,就追打着二卯四处疯跑,她一边追一边也揭开了二卯家的老短儿:咱村有个刘二尖儿,在街上摆个杂货摊儿,睁眼瞎不识字儿,记账净闹稀罕事儿,有人买了他五个鸡蛋,就在账上画五个圈儿,到时候人家还了账儿,就在圈儿上画一条线,到年底他又去要账儿,硬说人家欠他一串糖葫芦钱。鸭梨从小长得高大壮实,手脚麻利嘴不饶人,刘二卯瘦小蔫坏,手无缚鸡之力。在鸭梨的追打之下,刘二卯最后还得乖乖地向鸭梨服软求饶,他一连串叫了三声亲姐姐,鸭梨才觉着占了上风又得了便宜,这才算把事扯平了。后来,全村人都没想到:这两小冤家竟做了长久的夫妻。
儿时的记忆,像家里珍藏的一杯陈年老酒,年头越长越感觉回味无穷。在每一个生命开始的地方,乡音、乡情、乡俗、乡亲和村路、村街、村井、村屋,还有村里村外那曾经熟悉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个又一个无法再拷贝的童年故事。对于外出谋生的游子来说,童年的回忆里都会有一个宁静、宽厚、温暖、明亮、充满着浓浓亲情的心里家园。
我是改革开放初期,从基层调到城里来工作的,离开家乡30多年来,亲眼目睹了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村与村之间那一条条坎坷曲折的黄沙路,已经变成了平坦宽阔的柏油大道,使用了上千年的耕牛换成了拖拉机,赶马车的老把式,变成了农用汽车新司机,割麦的镰刀和轧场碌碌,已经变成了联合收割机,挑水的扁担与水桶变成了水龙头,烧饭的柴草变成了气和电,低矮潮湿的土坯砖瓦房,翻盖成了漂亮的二层楼……如今,村里人各家的吃喝穿戴都不用发愁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就把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从千百年延续下来的肩扛、牛拉、手刨的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让农民从土地上真正站立了起来。乡村里多少辈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现在一件件都摆在了眼前,你说农民兄弟们能不从心里感激吗?
今年十一黄金周,我和家人一起外出旅游了。村里的老伙伴们因为没见着我回老家,刘二卯打来电话问我:喂,你小子咋啦,为啥过节也不回家?俺和鸭梨都挺想你的,咱村里这帮老伙计们的日子都好过了。你说现在种地的多滋润啊。国家不仅不让咱上税纳粮了,还倒着找给咱钱,这都是国家给咱谋的福。再过几年,俺两口也就领上政府给发的养老金了。老伙计,找点时间,回来聊聊天叙叙旧,喝壶家乡的老白干儿,让鸭梨给咱哥俩,多整几个硬菜行不?
老哥们的一声亲切呼唤,就把我在外漂泊着的心又领回了家园。
(作者为媒体人,现居石家庄)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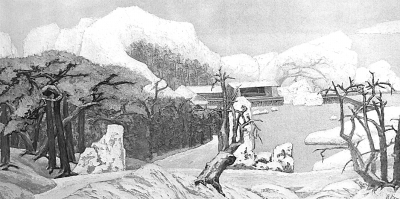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