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乐世界或天堂不管被描绘得如何美,人,还是愿意留在人世。
●死,只是个体生命的终结,但你参与创造的世界会因为你的参与而美好。
●如果寻求解脱,从对死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勇敢地面对死亡,快乐地生存,过有意义的生活。
生与死,是人的生命的始与终。人的生命内容是生死之间的全部活动。这段时间或长或短,有的人英年早逝,有的人寿高期颐。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发过感叹:“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但不能因为人人“终期于尽”,而抹平生死之间存在各式各样的人生。
人,落地时的哭声像最美妙悦耳的乐章,走时昏迷无言像断弦的破琴。任何人,都是哭着来,哭着走的。生时,自己哭;走时,亲人哭。如果只从哭声中探索人生,永远无法理解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人的生,不由自主,是父母结合的产物;人的死,不由自主,物壮则老,这是普遍的自然规律。我们不可能只欢迎生的规律,拒绝死亡的规律。可是要正确理解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重在人的一生的活动内容,这个内容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自己用行动书写的。
人世间最令人伤心的事莫过于“死别”。没有死亡,就不会产生宗教。宗教就是创造一个死亡人生中的“不死”世界,让灵魂继续在另一世界存活,所谓前世今生和今生来世之说都是缘于此。没有死亡,哲学也会失去最有智慧的部分。关于如何对待死亡,是哲学智慧的重要部分。如果没有死亡,庄子哲学的智慧就会大打折扣。全部中西哲学如果其中不包含生死智慧,就会失去它的精彩篇章。使人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是古今中外许多哲学家全力以赴的事。但对死的恐惧是人生存本能的一部分,很难坦然相对。哲学家以最大的智慧谈论生死,宗教从产生起就教导人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但极乐世界或天堂不管被描绘得如何美,人,还是愿意留在人世。
对死的分析可以有两个角度:科学的角度和价值的角度。科学的角度容易讲清楚。像庄子说的,生死如日夜之常,是自然规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生与死》中说过,“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本质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本质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局,即总是以萌芽状态存在于生命之中的死亡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如此”。恩格斯还补充了一句,“生就意味着死”。生死相依,再蠢的人,再怕死的人都无法否认这个事实。这是铁的规律。虽然有过秦始皇求长生不老药,有过汉武帝受李少君之骗,也有过无数炼丹合气、企求羽化登仙的道士,但一个个都是历史的过客。
对死的科学分析是容易的,最难的是价值判断。既然人终究必有一死,生还有什么意义呢?贤愚,肖与不肖,英雄懦夫,好人坏人,富人穷人,达官贵人与贩夫走卒,最终都是坟头一个,有什么区别呢?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生死观。其实,死只是生命的终结,而不是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终结。如果人生的价值最后都淹没在死亡中,人的生命活动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最终必有一死。
在现实中,有的人活着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仍然活着。人们之所以赞赏“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一诗句,表明人们并不认同一死百了的生死观。这种区别就是人生的不同意义和价值。近年来,学术界、文化艺术界成就卓著但英年早逝的消息时有所闻,令人倍感惋惜。人们惋惜的不仅是早逝,而且是英年早逝,即他们短暂的人生对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本还可以继续做出贡献,可过早逝世。人老寿终是必然的,但英年早逝并不正常。
话又说回来,如果人人不死,都与天地同老,万物同春,何必讨论人生意义与价值问题呢?人生意义与价值问题的产生,正在于人生短促,人人有死。在有限的人生中,如何尽一个做人的责任?对于永不消逝的东西是不存在价值问题的。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主要表现为对生与死不同意义的认识。所谓“人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讲的就是短暂人生中的人生意义问题。“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一种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好死不如赖活,又是一种理解。由于人皆有死而否定人生的意义,否定对生的价值判断,两眼一闭,管它怎么说呢!如果抱着这种生死观,为善为恶、好人坏人都是一样,反正人人归于一,最终都是死。这种生死观是最无道德、最无责任、最无担当的生死观。
死,是无可逃避的。由于有死亡而看破红尘,或人未死而心先死,都解决不了生死问题。我们应该直面死亡。人人都是向死而生,生死之间或长或短,终有了时。从个人来看,是个悲剧,是宿命;从人类的角度看,是史剧,是人类的发展。死,只是个体生命的终结,但你参与创造的世界会因为你的参与而美好。动物的死亡留下的躯体最终化为尘灰,而人的个体的死亡留下的是充满意义和价值的世界。人类,因个体的死亡而延续,因一代代个体的创造而使世界越来越美好。这就是超越个体死亡之苦的生死观。囿于个体,死亡是痛苦;着眼人类,个体死亡是社会进步和延续的必然。
如果寻求解脱,从对死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勇敢地面对死亡,快乐地生存,过有意义的生活。如果逃避死亡,寻求解脱,实际并未解脱,因为心存解脱之念,证明仍生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中。真正的解脱应该是认识死的必然性,又懂得生的价值。既热爱生命,又保持死亡时的尊严。这才是真正懂得生与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是充满智慧的回答。生死相依,只有生的伟大,才有死的光荣;而生时的卑鄙,必是死后的遗臭。
出生与死亡的性质并不相同。出生是生命的获得,这是自然的恩赐,即父母结合的产物。这是任何个人都不能自主的。死是生命的终结,它同样也是自然的规律。但有一点不同,生是不能自我做主的,是“被生”的;而死,则存在多种可能和不同方式。有寿终正寝,有冤屈而死,有为国牺牲、为理想和信仰而死,因此死亡中会存在“应当”与“不应当”的问题,即存在不同的价值负载。
我想起《论语》中孔子对管仲不死君难的评价。子路问孔子,“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算得上有仁吗?”子贡也有同样的疑问,他说“管仲非仁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路和子贡都同样问孔子,齐桓公杀了自己的亲哥哥公子纠,公子纠的老师召忽自杀,可同为公子纠老师的管仲却活着,而且帮助齐桓公。孔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远远超出了单纯道德的判断,区分仁人之仁与妇人之仁,对死的“应当”与“不应当”赋予更高的价值意义。孔子说,管子虽然没有像召忽那样死去,可他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还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样,孔子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即一匡天下、保卫中华文明来判断管仲的生与死的问题。叶落归根的死亡是必然规律,可当死亡存在可选择性时,就存在“应当”和“不应当”问题。
在生与死的问题上,我们应该贵生知死。贵生,即要重视生命的价值,尽量避免英年早逝,尤其是各种非正常死亡;也要知死,即死得其时,享天年;死得其所,即死得有价值。没有辩证唯物的生死观,不可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孔子就反对那种“自经於沟渎而莫之知也”的匹夫匹妇对生命的态度。当我读到报载有些年轻人或因感情纠葛,或因考试失利,或因就业受挫,甚至某些小不如意的事,就轻生跳楼、漠视生命,十分痛心,深感他们太缺乏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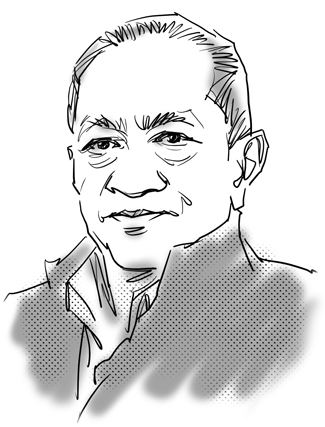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