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岁的车锡伦自称“杂家”。的确,作为扬州大学中国俗文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在俗文学的各个领域,如古代小说、戏曲、民俗、民间故事,他都有所涉猎。但在同行学者看来,车锡伦是不折不扣的“专家”:钻研“宝卷”——一种有近800年历史的民间说唱文本——30多年不辍。车锡伦总结:宝卷也好,民俗也罢,他研究的大多是文学史教材上很少讲或者根本不讲的文学现象。
游荡在少人问津的“边缘”,车锡伦的学术成果很少为外行人所知晓。直到近几年,他撰写的《中国宝卷研究》接连获得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中国俗文学郑振铎学术奖、高校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这位早已退休多年的老人才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日前,随着车锡伦主编的《中国民间宝卷文献集成》第一个分卷——15册的江苏无锡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有更多人开始理解车锡伦的学术追求。
师承“俗文学学派”
在有些学者的眼里,与正统文学相比,包括宝卷在内的俗文学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但车锡伦坚信,他的宝卷研究,始终沿着郑振铎、赵景深两位前辈学者开辟的道路前行,自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
“许多的正统文学的文体原都是由‘俗文学’升格而来的。像《诗经》,其中的大部分原来就是民歌。像五言诗原来就是从民间发生的。像汉代的乐府,六朝的新乐府,唐五代的词,元、明的曲,宋、金的诸宫调,哪一个新文体不是从民间发生出来的?”这是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的经典论述。郑振铎认为,“俗文学”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主要的成分,而且也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20世纪30年代,车锡伦的导师赵景深正是在郑振铎的影响下,投入了俗文学的研究。这部《中国俗文学史》,车锡伦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一部翻破了,就再找来一部。
“1955年,我从山东泰安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入校之初,便对赵景深教的‘中国人民口头创作’课特感兴趣。它引起我童年时代许多愉快的记忆:从干娘那里听来的歌谣,逃学到庙会上去听的山东快书‘武老二’……”车锡伦记得,他第一次看到宝卷,就是在赵景深的家里,“本科毕业后,我进入复旦大学中国文学史专业研究生班,继续追随赵景深学习民间文学。那时,我每周到他淮海路的家中听课,常在二楼书房环绕四壁的书架上找书,东壁书架最下层角落里放的是宝卷,但没有展开深入的研究。”
从复旦大学毕业后,车锡伦远赴内蒙古大学任教,历经“文革”,又调到山东大学,直至1981年进入扬州师范学院(今扬州大学)后,才真正开始了宝卷研究。
这时,虽已年过不惑,妻弱子幼,但车锡伦还是走到乡间地头,进行田野调查。实证,是以郑振铎、赵景深为代表的“俗文学学派”倡导的基本治学方法。
老而弥坚
“现在,在江浙吴方言区和甘肃河西走廊的一些农村中,仍然有演唱宝卷的活动。进行田野调查,不仅可以亲身体验、感知,而且能与历史文献研究相结合,起到以今证史的作用。”车锡伦说,退休前,他进行田野调查,都是利用学校正常教学之外的业余时间。没有经费,只能断断续续地进行,调查的地区也基本限制在扬州附近的江浙一带。
“我从事宝卷研究30多年,其间遇到的困难,外人可能难以想象。在农村田野调查中,步行十里、二十里是经常的事。有一次,搭乘农民的三轮摩托,还出过车祸。”最让车锡伦难忘的,是1997年,那时他获得了不多的科研经费,只身到山西介休调查,调查临近尾声,身上只剩下了返程的路费,接下来两天的住宿费没了着落。无奈之下,时年整整60岁的车锡伦,只好在介休火车站候车室里将就了两夜。
对现存宝卷演唱活动的田野调查,让车锡伦对宝卷的地域性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南方与北方的民间宝卷有何联系,又有何区别?内容和形式上具有什么地域特征?这些问题前人都未曾触及。
近几年,两次罹患重疾的车锡伦,无法再继续田野调查工作了,但对宝卷文献的研究一天也没有中断。他希望,能有志同道合的年轻学人与他一道,继续编纂《中国民间宝卷文献集成》。这部书他筹划了20年,除了刚刚出版的江苏无锡卷,还有江苏苏州卷、江苏靖江卷、浙江绍兴卷、山西卷、甘肃河西卷等分卷的整理工作亟待展开。
“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复旦大学教授、著名文学史家朱东润曾手书这首宋人晁冲之的诗赠予车锡伦这位昔日的弟子。车锡伦说,每当静夜读书,面对老师的法书,他便精神一振。如今,虽已年近八旬,车锡伦这匹独骑瘦马,仍然驰骋在学术的道路上。(本报记者 杜羽)
延伸阅读 宝卷
中国宝卷是在宗教(佛教和明清各民间教派)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仪轨演唱的一种说唱文本,演唱宝卷称作“宣卷”(或作“讲经”“念卷”)。
宝卷渊源于佛教的俗讲,产生于宋元时期。它是佛教僧侣用忏法的形式讲经说法、悟俗化众的宗教宣传形式,在民间佛教信徒的宗教信仰活动中演唱。
由于宝卷历史发展和内容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宝卷成为研究宋元以来的宗教(特别是各种民间教派)的重要文献;同时宣卷和宝卷又被视为一种民间演唱文艺和说唱文学体裁,纳入中国俗文学史(民间文学史)和说唱艺术史的研究范围。
——摘自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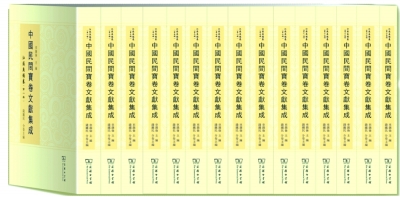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