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主编《文选》时有哪些考虑?他的这一举动究竟受到何种理念的驱动与支撑?这些深层次问题,攸关《文选》编纂认知,影响到“文选学”研究的全局,是“文选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需要予以认真审视与思考。
一
萧统主编《文选》的时间,主要是在受梁武帝重托、以太子身份实际主持朝政期间。他在《文选·序》中自陈:“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紧接着又说:“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历观”“泛览”云云,是说其主编《文选》,以广大“文囿”、浩瀚“辞林”为观览对象,以最深切的生命关怀,全身心地投入,以致因“心游目想”、专注忘我工作,而对时间流逝与身体疲倦浑然无觉。应该说,视忙若闲,以苦为乐,以高度的专业精神和对文化的热爱来对待这项事情,正是萧统得以主持编好《文选》的重要条件与动力因素。
萧统主编《文选》,还抱有更高的文化理念与理想追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萧统以太子身份实际主持朝政,绝不可能自外于“世情”与“时序”;其主编《文选》,也必然承载国家意志,有彰显国家意识形态的特定需要。魏晋迄于梁代文化审美观念的臻于高度发达与成熟、南北朝后期华夏民族文化大融合所达到的新高度,使得建构大一统文化王朝的期冀,成为南北朝后期愈加凸显的时代精神。这三种时代因素交互为用,更使萧统对历史文化发展抱持高度的使命感与责任担当,而将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审美高度有机结合作为崇高文化理念,也使其将主编《文选》并使之成为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大典,作为实现自己文化理念与政治理想的重要方式。
二
萧统界定其编选作品的上、下时限为:“远自周室,迄于圣代”,并宣称:“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文选·序》中的“姬、汉”用词显示:萧统确实把主编《文选》作为践履梁朝之国家意志,呼应建构大一统文化王朝的时代必然要求。
显然,其以周代为起点,称述自周至梁的所谓“七代”与“千祀”,有着明确的思想关切。因为就中国王朝的起点而言,并非以周代为最早,文学创作也非始于周代。若仅限于谈论文化王朝起点,举一周代即可,不必连缀“姬、汉”。尤其是谈论以周代起始的所谓“七代”时,直接跳过秦代,而明确并列“姬、汉”、也不列出汉代以后的其他王朝,仅笼统宣称“自姬、汉以来”。可知身为梁代实际主持朝政的太子,萧统目光高远,显然是专就典范意义上的文化王朝立言,故不屑论及秦代、三国、两晋、刘宋与南齐。如果认同萧统确是以周代为典范文化王朝的起点,推许大汉文化王朝可与周代比肩,再联系其界定《文选》选文的上、下时限为“远自周室,迄于圣代”,则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其必有表达梁代将可成为绍继、甚且超迈“姬、汉”的文化王朝的特定思想内涵;也可断言:其主编《文选》,必有为梁朝大一统文化事业服务的政治雄心。
萧统并称“姬、汉”,实际是沿用了在南北朝时期流行的关于“姬、汉”的固定用词。而在很大程度上,“姬、汉”用词的流行,正是建构大一统文化王朝这一时代必然要求的外显。
早在南齐时代,“周、汉”用词已成固定搭配,将周、汉视为文化王朝两大典范的认识,已经较为自觉而普遍了。如《南齐书·礼志上》记载,萧琛就曾在奏议中建言“宜远纂周、汉之盛范”;祖冲之关于更造新历的上书中,也强调“令却合周、汉,则将来永用,无复差动。”南齐王朝以周、汉为宗,不仅是对文化王朝典范的推崇,也折射了其以华夏文化正统自居,而与北朝竞逐建构大一统文化王朝的心理趋向与追求。至梁代,这种接续、超迈周汉的雄心壮志尤为彰显。梁武帝诏书中多处使用“可依周、汉旧典”“在昔周、汉”等言辞。丘迟《与陈伯之书》宣称“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实际也是基于梁朝为接续周、汉之正统,必当实现国家统一这样的情理判断。
北朝君臣普遍以接续周、汉自任。《魏书》记载赞美魏“方隆周汉”“道迈周汉”的言论,俯拾皆是。赞美孝文帝言辞体现尤多,如北海王元详、张彝、高闾等均把他比作周、汉圣王。《北史·儒林列传》评价孝文帝时代“斯文郁然,比隆周汉”。北周以周代为宗,但其建构大一统文化王朝的雄心,比以接续周、汉自任的北魏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北史·儒林列传》记载:“周文受命,雅重经典”,“于是求阙文于三古,得至理于千载,黜魏、晋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典。”北齐王朝注重周、汉并称。如高洋天保七年《并省州郡县诏》,就参照周汉楷模:“傍观旧史,逖听前言,周曰成、康,汉称文、景,编户之多,古今为最。”高洋在褒扬病逝之臣陈元康时,也举周汉功臣为例,称其如“申、甫之在隆周,子房之处盛汉,旷世同规,殊年共美”。
隋代实现了国家统一,也延续了这种“周汉”固定用词,意指明确。如隋初于宣敏针对封建之事上疏,就宣称“臣闻开磐石之宗,汉室于是惟永;建维城之固,周祚所以灵长”,期许隋代能够“继周、汉之宏图,改秦、魏之覆轨”。薛道衡在炀帝时所上《高祖文皇帝颂》,推崇隋文帝的统一、化育之功是:“张四维而临万宇,侔三皇而并五帝,岂直锱铢周、汉,么麽魏、晋而已。”
综上可见,萧统所谓“姬、汉”用词,不仅渊源有自,而且带有特殊用意:在历代王朝中,特别表彰周、汉两代大一统文化王朝,显然意在彰显梁朝欲绍继、甚且超迈周汉两代大一统文化王朝的政治雄心。因此他要把自己主编的《文选》当成“比隆周、汉”的文化大典的内在追求,就能够清晰感知了。
再具体考察萧统主编《文选》时,所处的南北朝后期特定的政治文化发展现实:其时南、北对峙,以华夏文化正统自居的梁朝,正处于繁荣发展期,也有统一天下的宏志,甚至一度还取得南北对峙的战略优势。而根据《梁书》本传记载:“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万机。”他还有“明于庶事”“天下皆称仁”的美誉,也曾以“菲衣减膳”的实际行动支持北伐事业。故其被梁武帝委以主持朝政重任,顺应时代要求,主编《文选》以为一代王朝文化大典,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三
如上所言,萧统主编《文选》的理想乃是:欲成就“比隆周、汉”的一代王朝文化大典,由此出发,也带给我们反思当代“文选学”研究系统、展望未来研究新景的重要启发。
第一,《文选》之“文”的真正含义究竟为何?长期以来,学界较少关注《文选·序》开篇即将“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作为“文”之起点,并引述《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阐述“文”之“时义”的远大深广;忽视《文选》实际是对“文”之发展的一种全面择取与系统总结,忽视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审美的关系,而是以当代更近于西方“文学”的概念与《文选》之“文”对接,从而仅将《文选》理解为一部当代意义上的“文学”总集,片面窄化理解《文选·序》所表达的“文”之进化特征与审美意义关系的思想内涵,而单纯着眼于“沉思”与“翰藻”立说;讨论《文选》的诸多精义,也只局限于当代狭义形态的“文学”层面,刻意区分《文选》之所谓“实用文体”与“非实用文体”。唐以前的“文学”概念指涉远比今日宽广,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谓“四科八体”:“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文赋》所谓“十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到萧统《文选》的三十九体分类,则这种“文”绝非仅仅是“沉思翰藻”,而应该是遵从儒家诗教说“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文”,只不过这种“文”更注重“文”的进化发展,更强调将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审美予以有机契合,从而使“文”在更高层次更好地为国家意识形态服务;《文选》也绝非今日意义上的所谓文学总集,而是一部包容更为广大的国家文化总集、文化大典。这样,研究《文选》就不仅要研究其属于当代所谓的“文学”之意义指涉,更要与古代之“文学”概念对接,全面拓展、系统研究《文选》所蕴涵的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价值观念、思维模式、思想意义、审美精神与其他属于基础性、多样性的文化价值内涵,研究《文选》在后世被确认为一部国家文化大典及其被经典化的历程和优劣得失。
第二,当代“文选学”研究的繁荣兴旺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不容置疑,但为了更好地发展,还必须追问当代“文选学”研究系统的建构是否合理?在“文选学”研究系统中,居于核心主导的方面究竟是哪些?可以肯定地说:“文选学”的核心研究对象应该在编选问题。因为其所选录的多数作品在当时皆为习见,仅分析作品显非“文选学”之要义。为何、如何选择这些作品,并以何种方式呈现出来,使这些作品构成一个自足的文化大典系统,这才是《文选》之所以是《文选》的关键。故研究萧统主编《文选》的立意,就显得特别重要。可惜学界过分专注于编者、编纂时间、编纂过程等方面的具体研究,致使《文选》的核心价值,几乎湮没不彰。因此我们也借本文郑重向学界提出呼吁:超越今日之较为狭隘的“文学”观念,回归到古代“文学”观念的对接,不仅以深入研究《文选》这部意欲“比隆周、汉”的一代文化大典为契机,积极思考重构“文选学”研究系统,推动“文选学”研究事业迈向新的高峰,也为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伟业的“文学”概念重构,以及核心精神价值与思想系统的重构,提供重要智力支持。
(作者系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文选学研究会副会长)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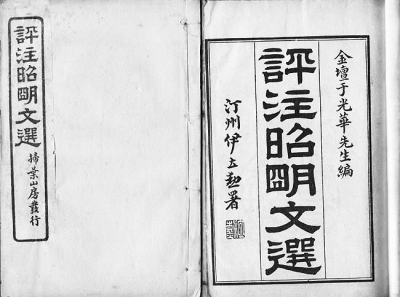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