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付彩云老太太自己讲,她是在伪满洲国康德八年(1941年)嫁到高步屯来的,当时还不满十七岁。丈夫要比她大得多,已经五十多岁了。成亲的第一天晚上,丈夫的肚子一直在“咕噜噜咕噜噜”地响,吵得她一夜都没睡好。开始她以为他是在闹肚子,后来才发现他天天这样。这准是因为他老了,她暗自猜想,人一老就啥啥都不中用了。不过她明白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在这之前,她爸已经从丈夫家里驮去了两麻袋高粱,还揣走了一沓绵羊票子(伪满洲国纸币)。
不管咋样,往后我再也不会挨饿啦!她这样安慰自己。
付彩云说:“那年月,女人就这样啊!”
丈夫名叫高步青,剃光头,出门时戴一顶瓜皮礼帽,窄脸,下巴上长着一些稀稀拉拉的花白胡子,两边脸上一边一块高高的颧骨,小眼睛,看上去似乎只有一道缝儿,然而眼神儿却特别的锐利,嘴唇薄薄的,总是紧紧地抿着,而且总是很少说话(当然不是不说话,他又不是哑巴)。
那时候,付彩云总是有些怕他。后来她发现,其实不光她一个人,家里头别的人也是怕他的。在付彩云之前,他已经有了两个老婆,除此之外,他还有儿子和儿媳妇,还有孙子和孙女,加到一起,少说也有十几口子了。大家住在一个大院里,他们之中无论谁,见了他都“溜溜”的,就像耗子见到了猫,哪怕他无意间咳嗽一声,他们也会吓得一哆嗦,那些年纪小的小孩子,甚至会“哇”的一声哭起来,他却理也不理。
照付彩云老太太的说法,她丈夫高步青是个性格很怪的人,别看他整日整日地不说话,实际脾气暴躁得很,发起火来地动山摇的,而且特别犟,就像有人说的,是属于叼着屎橛儿给他麻花都不换的那种人,就是说,认死理儿。付彩云说她亲耳听到过,他的前两个老婆背地里都叫他犟驴,简单些便说成“那驴”,那驴长那驴短,付彩云每次听到都会会心地一笑,她说她们说得对。
付彩云说,当时老高家是这一带有名的大户人家儿,好地就有上百垧,自家还开了一处油坊和一处烧锅(酒坊),除此之外,还在县里开了一处粮行,一处杂货店,专卖自家出产的东西,年年进的钱都“海海”的。屯子里更不用说了,房子都是青砖的,除了正房还有厢房,少说也有几十间,四周都有高墙围着,墙外建有炮台,里头住着炮勇,炮勇人人有枪。整个高步屯,他家就占了一大半。
高步青家财大势也大,看来这是没有问题的。
尽管他家有钱还有势,可是高步青却没有多少大财主的样子。除了付彩云,另外几个当年见过他的人也是这么说的。比方他的穿戴,除去那顶瓜皮礼帽(还有一件冬天穿的羊皮大氅),不过就是衣裳干净一点,没有补丁,他的穿戴和屯里的许多人几乎没什么两样。而且,夏天的时候也喜欢挽起裤脚,这当然是为了干活方便。据说他每天都要干活的,逮住什么就干什么。即便没什么活干,他也这么一副样子:肩上扛着一把锄头,有时候在屯子里,有时候在田里,四处转悠。
那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四处转悠。他走一会儿站一会儿,一边还东张西望,总是一脸的心事儿,谁也说不上他在想什么。“多半在想怎样扩大他的家业。”付彩云和那几个当年见过他的人都做如此猜测。
还有吃饭。吃饭他讲究吃半饱,就是说,吃到半饿不饿为止。对他来说,则只吃一碗小米捞饭,再喝一碗小米饭汤。菜也简单得很,一碟儿萝卜条咸菜是必备的,不过要用辣椒油拌一下,此外再加一个炖菜,炖土豆炖白菜炖茄子炖豆角等等,里面偶尔会放几块肉。因为是大家一起吃饭,要把菜分别盛在几只大海碗里,可是不论几只碗,菜却只有那么一个。这些事都是付彩云亲眼看见的。
问题是不光他自己这样做,他要求别人也这样做,有一次(当时付彩云嫁过来没几天),全家人正在吃饭,吃着吃着,他突然大声说:“吃饭别吃得太饱,吃到八分饱就行了……少吃一口谁也饿不死!”当时谁也没吱声,只有付彩云吃了一惊,她抬起头四处一看,发现每个人都在看她,才明白这是说给她的,她后来知道,这话他早就对别人说过了。
那些年,这儿还是日本人的天下,县里住着日本人的军队,日本人当着本县的副县长(虽然不叫副县长,而叫参事官,实际却是一回事),还当着警务局的指导官、警察署的警政,反正什么事儿都是他们说了算。
当年不是有个满洲国嘛,满洲国的皇上叫康德。早先年有个大清国,大清国有个乾隆爷还有个慈禧皇太后,他们就是他的祖上。听说二十年前康德就当过一回皇上,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最多四五岁,好像叫宣统,住在北京的大殿里,后来叫什么人给撵跑了。往后就来了一帮日本人,他又第二回当了皇上。不过不在北京住了,换了一个地方叫新京,新京离这儿不太远,那儿现在叫长春。他们说他这个皇上可不好当,说他处处得听日本人的。
“这些事儿都是我从老辈人那儿听说的,不知道真假。”付彩云补充道。
付彩云还说了一件事儿,说就在她嫁到高步屯的那年秋天,庄稼刚刚上场(就是刚从地里收回来),有一天,从山河镇来了两个人,一个是镇公所的办事员,一个是警察署的“白帽箍”。“白帽箍”挎着匣枪。他们说镇上有事,把高步青叫走了。那时候常有这种情况,一旦有什么事,就派人过来叫他,他又是高步屯的甲长,动不动就会被叫去一次。
不过这次好像有些不同。他们走的时候是贴晌时分,直到天黑他才回来。而且,和以前相比,这次的状态也大不一样。一进家门,他就破口大骂:“这些狗操的王八羔子,欺负我头上来啦!我苦巴苦业挣下这份儿家产,他们说拿去就得拿去!说拿多少就拿多少!天底下还有没有王法……”
他脸色青紫,脑袋和双手,还有嘴唇和胡子,都不停地哆嗦,没等骂完,就一头栽倒在院子里。当时家里人都在院子里,还有几个炮勇和长工,大家本来正在等他回来吃饭,这时马上乱作一团,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随即有人喊道:“别愣着!救人要紧!”
还有人喊:“掐人中!快!掐人中!”
于是有人掐他的人中,还有人进屋含了一口凉水,“噗”地往他脸上一喷,过了一会儿,他总算哼哼着睁开了眼睛。人们七手八脚,立刻把他抬进了屋。
缓过劲儿来以后,他才说出了事情的原委,日本人要建开拓团(就是要在这儿种地建屯子),要征他四十垧熟地。
他瞪着眼睛说:“娘的四十垧啊!还一个大钱不给……要不咋叫征呢!”
付彩云说,从此高步青就病了,一病十几天,天天在炕上躺着,人也一天天往下瘦,几天就瘦得不成样子了,看着让人可怜。家里给他请了大夫,说是急火攻心,抓了很多药,药都是付彩云给熬的(那会儿没有药片儿,都是草药),一天熬一帖,药汤子又黑又苦,盛在一只二大碗(碗的一种,比大碗小,比小碗大)里,眼瞅着他“咕嘟咕嘟”灌下去。
那一阵儿不论哪儿都是他的药味,药味就像小虫子一样,墙角旮旯都能钻进去。光药味不要紧,家里还处处笼罩着一种说不上来的恐怖的气氛,让人老是提心吊胆的,说话走路都得小心又小心,怎么说呢,就像家里死了人。这也是一种味。两种味道混在一起,把人压得气都喘不上来。
这期间日本人已经把地占上了,而且沿着划定的地界儿钉了好多的木牌。这消息是高步青的儿子带回来的。高步青有两个儿子,他们都亲眼看见了那些木牌,上面还写着日本字。不过这件事他们没有马上告诉高步青,怕他受不了。在付彩云的感觉里,这两个儿子都不像高步青。
高步青的病总算一天天见好了。一天晚上,他让付彩云去叫两个儿子。儿子们一前一后来到高步青的屋子,其中一个说:“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家有枪又有炮的,我看咱就别吃这眼前亏了……”
儿子还没说完,就被高步青打断了,他大声吼道:“孬种!”
因为病还没有全好,吼过之后他喘息了一会儿,半晌才平静下来,说:“这件事儿我想好了,我要上新京找皇上去。我要去告御状。不管咋说,这满洲国还是他皇上的吧。我就不信讨不回这个公道……这件事宜早不宜迟,明天我就走。”
第二天他真的走了。他是上午走的,走的时候戴着那顶瓜皮礼帽,儿子们给他套了一挂马车,车上铺了一条棉被,还带了一名炮勇。
付彩云说:“想不到,这一去他就送了命……”
关于高步青,县志上是这么说的:
“高步青,旧时本县山河镇西郊有名的乡绅地主,社会影响颇大,人送外号‘高老步’,所住自然屯被称为‘高步屯’。此人性格倔强……伪满康德八年,日本侵略者指名收其良田四十垧,为日本人专用。高执意不从,公开与日伪势力对抗,被捕入狱。释放后又去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告‘御状’,伪新京高等检察院见其是地方乡绅,不便加罪,于是采取两面手法,明则好言相劝,暗则捣鬼下毒,致使其中枢神经损伤,1942年(伪康德九年)归里后不久即死去,时年五十六岁。”
后来付彩云嫁给了屯里的一个农民,当时东北已经光复了。她和现在的丈夫生了两儿一女,如今儿女们早已各自成家。付彩云今年七十七岁,满头的白发挽在脑后。
这时已是傍晚时分,红彤彤的晚霞映照着天空。老太太坐在她家大门口一个木墩儿上,正在慢条斯理地纳鞋底儿。这会儿她抬起头,朝西天看了一眼,抱歉地笑笑说:“不能再跟你唠了……该给老东西整饭去了……”
说着话儿站起来,离开我,慢慢向院子里走去。
鲍十 原籍黑龙江省,现居广州。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拜庄》《葵花开放的声音——鲍十小说自选集》,长篇小说《痴迷》《好运之年》等。中篇小说《纪念》被改编为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作品被多种选刊选载或收入年度选本。其近作小说集《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以各自独立成章的小说,写了20多个屯的命运,被看作“一部东北平原的地理词典”。鲍十自称:“我想通过这些作品,让人们对中国东北的乡村社会有个大体的了解,包括历史的、政治的,以及人的命运、民风民俗,等等。我同时想做到一点:要使这些作品看上去不那么离谱,要基本真实,既不涂脂抹粉,也不夸大其词,尽力留下时代的真相。”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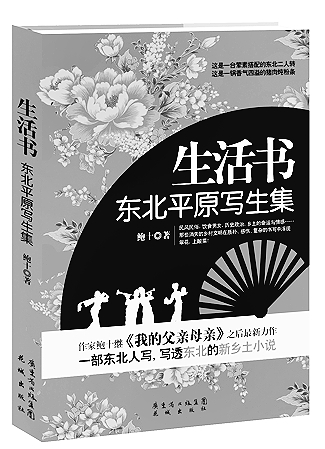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