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幢孤零零的小屋。
屋门洞开着。
她面朝外坐在门内地中央的一个蒲垫上。满头白发,乱蓬蓬的,如秋风中干枯的茅草;一脸皱纹,像煞清晨地面蚯蚓爬行后留下的印迹;一动不动,坐成一座泥塑,浑身散发着干涩、呛人的尘土味;连眼皮也难得一眨。
她的面前脚下,放着一只碗,盛满清水;紧挨着的一只碗,空的;还有一只破碗,也是空的。身子右边有一只簸箕,内盛一叠黄纸,即人们为逝者烧的那种上好黄纸。左边放了一只小板凳。
她坐在这里,从早到晚。
有脚步声自门外传来,渐行渐近。到门口处,停住了。听得有清脆悦耳的“叮当”声——那是硬币丢在破碗里;接着是衣裙摩擦的窸窣声,又听得耳边有粗粗的或细细的鼻息声——来人或站或坐,等在一边了。
老妪开口问道:“尊客人家中何人有事?”
来人便将事由述说一遍。老妪听完,并不多言,便动作起来。拈一张黄纸,盖在那只空碗上;右手手指伸进盛水的碗里,蘸了水,抬起来,悬于盖着黄纸的空碗上方,让它滴在纸上;然后又蘸水,又滴下。动作非常缓慢。
说来也真神,竟没有一滴水滴在地下,都准确无误地落在纸上;积得多了,就渗透下去,聚在碗里。
老妪仍不紧不慢地蘸水,又让它落于另一碗;口里念念有词,似乎在念着什么咒文,也许在祷告。
一只碗里的水渐渐浅下去了,另一只碗里的水渐渐多起来。蒙在碗口的黄纸,因浸水的缘故,中间也慢慢陷下去。水漫过黄纸了。
终于完了。老妪甩甩手上的水珠,又在衣服上擦了擦。于是又两手交叉置于膝上,一动不动,两眼望着门外。
来人便开口道:
“在××方向有一个水泡。”
老妪听完,嘴唇又翕动起来,似乎在念着什么。待一会儿,开口对来人说道:
“你家××的魂儿丢在××地方了。”
便伸过手去。来人也不吭声,自衣袋里掏出一方手帕,递给她。老妪把手帕摊在膝上,小心地拣起浸湿了的黄纸,折叠起来,置于手帕上;又将手帕叠起来,把黄纸裹于其中。嘴里念道:
“魂儿魂儿回来吧,魂儿魂儿回来吧。”然后递给来人:
“回去把它放在你家××贴胸的口袋里,再烧三炷香。”
来人便道一声“谢谢”。听得一阵衣裙摩擦的窸窣声,接着是脚步声,渐行渐远,听不见了。
原来这老妪是专为人家“招魂”的。
她是个盲人。
这天,她仍如平日一样,眼前仍放着那套器具;一动不动,如石雕一样。
有脚步声自门外传来,她不禁竖起了耳朵,眼皮也眨了两眨。这脚步声有点熟悉,很沉重,很有力,也许是……但似乎有点迟疑,没有她所熟悉的那种自信和冷傲,而且是她很少听过的皮鞋的笃笃声。但还是有点熟悉。她听得出某种东西。她不禁又眨了眨眼睛。
脚步声越来越近,最后在门口停住,不响了。粗粗的呼吸。重重的叹息。
不过没有听到硬币落碗的叮当声。
她也不开口。便熟练地动作起来。拿张黄纸,覆于空碗上。蘸水,滴下;蘸水,滴下。动作仍是那么娴熟,手却在微微发抖,有水滴洒在地下。
但毕竟还是完成了。
她甩甩手上的水珠,又在衣服上擦了擦。于是又两手交叉,置于膝上,一动不动,两眼“望”着门外。
却没听到那人发声。只听见粗粗的呼吸,重重的叹息,接着,是压抑的啜泣。
她仍望着门外,身子一动不动;不过,嘴角却在抽搐。眼睛又眨了两眨。
突然,她全身一震,因为她听到了带着哭音的一句话,太熟悉了,又那样陌生。
“太远了,找不到了。”
两行浑浊的老泪从她的盲眼中流出。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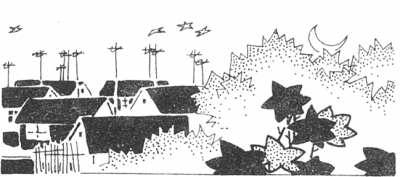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