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装帧、书名或体量来看,这本八百多页的厚书都像是三家村老学究为猎取功名而炮制的一块敲门砖。但这丝毫未妨碍它居然登上了“中国高校出版社书榜”,可见中国读者挑食的门槛之“精”,也可见当今天下已无人读书的慨叹其实是有些过虑了。收入书里的专论,近半数以发生在日军侵华时期的南京大屠杀为主题。这一灭绝人性的罪行,成为战后东京审判中最令人瞩目的呈堂例证之一。
从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国内在究竟是否存在过南京大屠杀的问题上,逐渐发展出一场持久的越来越激烈的争论。把争论各家归入“承认”和“否认”两大阵营固然不错,但现在看来又难免有点过于简单化。“承认”派中的绝大部分人,实际上都不接受罹害国对南京大屠杀受难人数的估计。“拒绝”派更是拿捏住上述数字难以被确凿地加以证实来大做文章,以数字的不易确证为理由,从根本上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把它说成是一场“虚构”。在从前陆陆续续地读过书中大部分文章的基础上重新翻阅这个集子时,我禁不住一再想起《水经注》校勘史上的一桩公案。
《水经》本是大体成书于三国时期的一部水道提纲。经北魏郦道元详加注释,它从原先仅述及130多条河流的一个近万字文本,被扩充为包含30余万字、记录1200多条河流、征引群书多达二百四五十种的有关中古中国区域地理信息的大型著作。《水经注》在宋代即有残缺,并已发生讹舛错简和经、注文字相混淆等问题。迨至明时,字句之夺讹臆改更趋增多。入清后,对《水经注》的文本从事“更正错简”“厘定经注”“捃补逸文”“校定文字”等工作而卓有成绩者,有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大学问家。使人颇感诡异的是,“戴东原氏成书最后,……而其书又最先出”。因有担任四库馆臣、得见宫中秘本的便利,他号称自己以《永乐大典》所录《水经注》作底本,并除含糊其辞地说及“与近代本钩稽校勘”之外,绝口不提全、赵二家书,示人以从未参考过这两部早先写成的校订本之意。所以当赵一清《水经注释》在戴书(殿本《水经注》)刊印20年之后刻版行世时,就有人因惊讶其书与戴本同,而指责校刻赵书者“以戴改赵”。而全祖望的《水经注》七校本遗稿则更要后此95年,方经门人整理出版。当日也有人因其与戴书雷同而摘斥遗稿整理者以戴改全。所以王先谦著《合校水经注》时,即声称对全氏七校文本“一字不敢阑入”。
但是,戴震竭力想回护的在《水经注》校勘方面超迈同时代所有学者的权威性,其实早在王先谦弃用全氏七校本的半个多世纪前,就开始无可奈何地动摇了。随着《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被抄出并流布开来,人们逐渐发现,戴震校勘《水经注》并非全以“大典”本为据。他实际上看到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全、赵二人的校本;惟赖当时人们无由查核“大典”所录《水经注》,他把自己抄自赵、全校本的字句伪托成是来源于“大典”文本。兹后,全祖望《水经注》五校稿本的发现,进一步坐实确然是戴震抄袭了全、赵二家之书,而不是相反。胡适看到全氏这个稿本后,也默默放弃了替他徽州老乡的“窃书”之过翻案的念头。
平心而论,即使不为掠美之举,作为集诸家校本优胜之大成的一项文献考据学上的总结性成果,戴震主持校勘的“殿本”仍有它自身的极高价值在。所以王国维会说,“郦书之有善本,自戴氏始可也”。他本着理解的同情揭示出,戴震亦尝独自发现厘定经、注之诸原则,“遂以郦书为己一家之学。后见全、赵书与己同,不以为助,而反以为雠”,“则皆由气矜之一念误之。至于以他人之书以为己有,则实非其本意,而其迹则与之相等”。“气矜之一念”有时真能害死人。出于“气矜之一念”,用虚词求胜或其他不够诚实的方式,把理应受真凭实据严格制约的有限论证推向极端,结果率多欲益反损,乃至于引发对冷静的有限论证之价值和信用本身的怀疑和颠覆性伤害。话未必是说得越过头就越好。这样的教训实在不可以一二数之。
本书作者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起步于“没有‘不同’意义上的争论”的年头。十多年来,该研究领域内的局面大概已经不能再以上述特征予以概括了。在推动此种变化方面,说本书作者居功甚多,应当不算是溢美之词吧。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由本书作者主持编著的一部最近出版的新书《东京审判研究手册》。这本书的前八十多页,是对有关东京审判的日文和西文已有研究文献的逐篇解说。看上去好像只是一编“经眼录”式的书目题解,但其中非但包含着极大的工作量,而且也使我借此看到,作者意欲将下一步的前沿性探索放置在何等厚实的既有成果基础之上去展开。这也正是处处体现于《歧羊斋史论集》一书内的学术风格。最后还有两句多余的话。书里提到十多年前日本出版的《检证南京事件“证据照片”》,那是“歧羊斋”主人和我一起在东京逛书店时发现的。自那以后,我一直建议他把此书翻译出来,而现在我还要再这样向他建议一次。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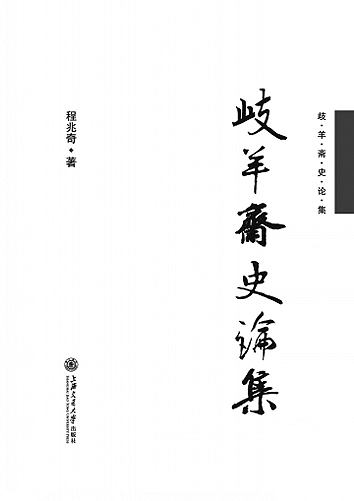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