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著名学者、理论批评家、翻译家、散文家。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学术专著有:三卷本《法国文学史》等三种;评论文集有:《理史集》等十种;散文集有:《巴黎散记》《翰林院内外》等六种;翻译与编选有:《雨果文学论文选》《莫泊桑短篇小说集》《磨坊文札》《局外人》《萨特研究》等二十余种;主编项目有:《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七十种)《雨果文集》(二十卷)《加缪全集》(四卷)等。2000年被法国巴黎大学正式选定为博士论文专题对象。200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终身荣誉学部委员”称号。
人物版:您的名字有什么特殊的来历吗?请您谈谈自己的童年往事,以及青少年时期的求学经历?是什么原因,让您走上了研究外国文学及文学理论的道路?您在北京大学时,与老一辈学者的交往中,有什么让您终生难忘的事情吗?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谁对您影响最大?
柳鸣九:古人云:“鹤鸣于九皋,闻声于天”,这就是我名字的出处,很抱歉,个性张扬的味道太浓。我的父母都没多少文化,对儿子也没有光宗耀祖的期望,起不出这么一个名字来。当时,邻居中有一位很有文化的老夫子,听说我生出来有九斤之重,父母给取的小名是“九斤子”,就给我取了这样一个“大名”,这就是来历。
我的儿童时代,基本上是在逃难的生涯中度过的。随着日本侵略军的不断进攻,我们家从湖南长沙逃到耒阳,在耒阳相对安定了几年,又从耒阳逃到广西桂林,再逃到重庆。难民生活的危险与艰辛我都经历过,毕生难忘。
后来,在中学学近代史,每当听到老师讲述中国受欺负、被侵略的历史时,我在课堂上总是心潮澎湃,哪些国家割占过我们的什么领土,什么国家没有割占过,我记得很清楚,这也构成了我近代史观的基础。我对美国之所以不无若干好印象,仅仅是因为它没有割占过中国的一寸领土。庚子赔款后,美国毕竟还在中国办了一所清华学堂。这是我少年时代思想脉络的一个主要部分。
我青少年时期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我所受到的良好的中学教育,我的父母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是他们敬畏文化、仰慕文化,深知文化对一个人生存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尽了最大努力,保证我接受系统的、完整的、良好的中学教育。
尽管我的家庭因为父亲就业地点的变换而辗转各地,但我进的都是当地最好的中学,如南京的原中大附中(即今南师附中)、重庆著名的教会学校求精中学、长沙的重点名校湖南省立一中。经过这些名校的教育与培养,我在1953年考进了北京大学。
我之所以能够走上外国文学研究这条道路,其实并没有任何早慧的根由、任何早熟的理想、任何早有的特定兴趣,只不过是顺理成章,一步步走来。
从中学起,我的文科成绩就比理科成绩好,这注定我要投考北京大学的文科,而选定西语系,则是因为想多学一门外语、多一种工作技能、多一种职业手段、多一个“饭碗”。恰好北大西语系是以培养西方语言文学研究人才与教学人才为己任的,为了这个目的,该系设置了最完备、最优质、几乎是最理想的课程,我就是从这样一个“炉窑”里烧制出来的。
当然,这个系的毕业生里有各种去处,有留校做助教的,有分配到各种文化机构与外事机构的,我运气甚好,分配到当时属于北京大学的文学研究所,具体是到《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担任翻译与编辑工作。能够如此对口,也许跟我四年学业中表现出来文字能力与思维能力还算比较可取有关。
根据工作岗位的需要,我必须做一些文艺理论翻译与西方文艺批评史的研究,这成为我专业工作的起点,然后就是一步步走下去,一步一个脚印,一步步把事情做好做大。
北大的求学生活对我一生影响很大。那时,正当全国院系调整,北大集中了全国人文学科几乎所有最具声望的宗师与精英,仅以与外国历史文化有关的学科而言,就有朱光潜、钱钟书、季羡林、冯至、李健吾、卞之琳、金克木、杨绛、潘家洵、闻家驷、李赋宁、杨周翰、盛澄华、陈占元、郭麟阁、吴大元、吴兴华、田德望等。
这些大师名家,他们的学术业绩、传道授业、讲课演说给青年学子们以直接教益,他们的气场、风度、轶事、传闻、细节给人以示范与启迪。在北大未名湖畔这样一个强大的文化学术气场中,如果善于学习的话,每时每刻、每处每地都可以受到启迪,得到营养,学到东西,兼容并蓄,取各家所长。
所幸,我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对文化的敬畏和崇拜,自己又如同一张白纸,并无自以为是、固步自封的定性,因此,还不失为一个善于吸收、善于接受启迪,也肯勤奋致学、兼容并蓄的青年。
只要是有“营养”的,我逮着就“吃”。朱光潜丰厚的学术业绩是我毕生的榜样,他每天坚持打太极拳与慢跑成为我效仿并坚持了数十年的习惯。当时的北大校长马寅初一开口就是“兄弟我”,这样一种不在乎语言时尚、不在乎礼仪规范与不流俗附和的风度,也成为我后来在学术观点上坚持自我、我行我素的最早启迪。
经济学家陈贷孙那种泰然自若、仙风道骨的神态,是我心目中名士风度的样板。而物理学家周培源在校园里蹬着自行车,风风火火地穿梭于行政大楼与教学大楼之间的景象以及上车下车的麻利动作,成为我后来办起事来颇为雷厉风行、讲究效率的最早启发。
总之,北大的四年,我没白白度过,我像一块海绵,做到了全面吸收,兼容并蓄。
人物版:您翻译的第一本书叫什么名字?它对于您今后的研究道路有何重要意义?
柳鸣九:我最早翻译的有两本书,一本是都德的《磨坊文札》,一本是雨果的《雨果文学论文选》。
都德的《磨坊文札》我从大学三年级就开始翻译了,但当时并没集中力量来做这件事情,而是断断续续,经常一搁置就是一年半载,甚至三五年十来年。我并没把它作为一件业务成果而集中力量去做,而是把它当作一种精神和情绪的调剂品,甚至当作一个解除高压的镇静剂,偶尔为之,慢吞吞地进行,所以成书出版倒比较迟。
都德是我最喜爱的作家,我很欣赏他纯净柔和的风格与幽默的语调。《磨坊文札》本身有一种隐逸恬静的情趣,颇有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韵味,读起来使人的心情归于平和宁静,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说实话,在我长期的学术道路上,经常碰到崎岖与坎坷,经常感到精神压力、烦恼与焦躁,我需要解压剂,我需要镇静剂。碰到这种时候,我就把《磨坊文札》拿来读一读,有时也译上那么一两段、一两篇。因此,我曾经把《磨坊文札》称之为我的精神绿洲、绿色家园。
我出版的第一部翻译作品是《雨果文学论文选》,翻译成书比较早。因为早在大学四年级,我做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论雨果的浪漫剧》。
雨果20多岁时便充当了法国浪漫派反古典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他发表了讨伐古典主义的《〈克伦威尔〉序》,这一篇长达五万字的大文,洋洋洒洒,文辞华美,成为西方文艺批评史上的经典文论。同时,他又按其美丑对照的原则写出了一批风格全新的浪漫剧。雨果的浪漫剧与文艺理论相辅相成,写毕业论文,我认真研读了他这两方面的文本典籍,这也为我后来翻译文艺理论做了前期准备。
到了《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后,我的本职工作是文艺理论翻译。这样,我较早地就完成了《雨果文学论文选》一书的翻译。本来,书在“文革”前就可以出版,但由于一些原因,这部作品竟被无理地压了两年。随后,就是十年浩劫,直到1980年,《雨果文学论文选》才获出版。
这项工作为我后来研究雨果,主编二十卷的《雨果文集》打下了学术基础。更重要的是,在翻译雨果气贯长虹、文辞华美的大序时,我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其影响。我喜欢写长序、写大序,实与此有关,我的理论文字被谬赞为具有“理论气势与斐然文采”“字里行间洋溢着一股浩然之气”,多少也与此有关。
人物版:您在写就《法国文学史》等专著时,有什么人和事值得纪念和铭记吗?
柳鸣九:数十年来,我的学术文化工作基本上是以法国文学史研究为主的,而写作多卷本的《法国文学史》又是其中的核心,我的其他一些编选工作、主编工作、翻译工作以及随笔散文写作等等,基本上都是从这个核心延伸出去的派生物。
《法国文学史》作为中国第一部大规模多卷本的国别文学史,断断续续用了我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其中,有诸多甘苦,学者的书斋生活一般都是没有什么生动的故事和有趣的细节可言,请看歌德的《浮士德》,其中只有很少篇幅是写浮士德博士在书斋生活中的灵魂探索。
如果一定要讲点值得纪念的人和事的话,可讲的只有两点:一是《法国文学史》是在“四人帮”仍猖狂一时的“文革”后期开始写作的。当时,我和两个伙伴都非常明确、非常自觉地以反“四人帮”的条条框框为指导思想,坚持以实事求是、科学公正的原则写史,这样才没有走上“极左”的邪道,没有把《法国文学史》写成一个废品。“四人帮”垮台后,《法国文学史》很快顺利地公开出版,并且于1993年获得了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全国图书评奖,积累了多年,参评图书共有五十余万种之多,故此奖得之不易。
第二点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法国文学史》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前辈的鼓励与支持,钱钟书先生帮助我审阅了其中的一些篇章,并给予了肯定与鼓励。李健吾先生则在《法国文学史》上册出版的时候,发表了评论文章,表达了热情赞赏,这也是我一生中得伯乐赏识、遇贵人相助的两个最特出的事例。
说实话,这在那个学术等级森严、学术阶梯漫长的时代,是非常珍贵的。
人物版:您最推崇哪位作家(国内或者国外)?您在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有何人生和治学感悟?
柳鸣九:有成就的作家是各式各样的。有的作家以精致的艺术使人叹服,得到世人的欣赏;有的作家为社会历史留下了宽阔、真实、有深度的画面,给世人开阔了视野;有的作家以深刻隽永、机智的思想而使人在智慧上受益,这些作家都有这种或那种被推崇的理由,但我最为推崇的是:外国作家中的加缪和中国作家中的沈从文。
加缪和沈从文在艺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这是不在话下,特别值得推崇的是,他们都自有一种精神力量,在为人处世上都表现出了不凡的人格。
加缪是一个平民草根出身的作家,但他作品至少发出了两道对人的存在、对人类社会有重大启迪意义与聚合力量的智慧灵光:一是人生如西西弗推石上山的哲理,二是人类社会团结抗恶的思想与道路。这两种哲理与思想都基于对人生、对社会的彻悟意识,表现出了一种坚苦卓绝、刚毅非凡的精神力量。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正能量”,这是我特别推崇他的原因。还有一点,加缪不是一个书斋学者、书房作家,他是一个投入了社会实践的行为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抵抗战士。
至于沈从文,他不仅是一位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作家,而且在他身上表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难得的坚毅精神。他曾经长期被打入冷宫,去搞一些管理服饰之类的事务性工作,这如同把一颗种子扔在一个石头缝里。然而,沈从文却偏偏不声不响地在这个石头缝里长成了一棵大树——《中国古代服饰史》。这种“石头缝里的精神”正是20世纪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可贵品格,至少对我个人很有精神感召力。
人物版:学者、翻译家、理论批评家、作家等等,在您的这些诸多身份中,你觉得自己更钟爱哪个,自己最不愿接受哪个?
柳鸣九:我的文化学术活动,内容并不单一,在不同的方面多少积累了一些实绩,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劳动部类中,从事过不同的劳动方式,有点不同的劳动产品。因此,有时被称为这个,有时被称为那个,得到了不同的名誉与身份,如此而已。
对于名誉与身份称号这类问题,我的态度是:“君子好名,取之有道”,只要名誉、名分、身份之下有实质内容、有劳动成果、有“干货”、有“硬币”,那就行了。
且不说,什么身份是我钟爱的,什么是我不喜欢的,我只想说:一、我最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真正学有专长、有所建树、有所创见的学者。二、我最想避免的、最忌讳的,是沦为一个空头的理论家、批评家,沦为一个不学无术,只靠引证圣贤经典、玩弄教条,只靠扣帽子、打棍子的理论家、批评家,我竭尽自己的力量不要成为这种人。
另外,我也曾经对翻译家这样一个头衔进行过自我调侃,不为别的,只是因为我在翻译方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我的研究工作与写作要少得很多很多。在翻译界,我只不过是偶尔客串一下的“票友”,和那些以毕生精力从事翻译的朋友不可同日而语,如今客串的“票友”也登堂入室,使我觉得有些对不起翻译家朋友们,用方鸿渐的话来说,就是“不好意思呀”。但毕竟你有过上百万字的译品,毕竟有几个译本广行于世,人家有时为了方便,简称你一声“翻译家”,那你大可安之若素,自己不必矫情了。
人物版:近期,光明日报社与中国外文局联合主办了“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十部法国书籍”和“在法国最有影响的十部中国书籍”评选活动,二十本图书已全部揭晓。您作为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荣誉会长及此次活动的中方评委会主席最喜欢其中的哪一本?
柳鸣九:在这些当选的图书当中,我相对更喜欢《红与黑》。正如我曾经所指出的,《红与黑》表现了时代巨变之际,两种价值观在一个特定青年身上的激烈矛盾与冲突,而且表现得那样真实、生动、自然,具有极大的心理深度,作家司汤达在写就这部小说、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把自己也摆进去了,使作品与人物具有社会典型性。
两种价值标准在一个人灵魂深处的矛盾冲突,其实我自己也感受过。前两年有一部电视剧,就写了《红与黑》在一批知识青年中大受欢迎的事实,可见此书的高票当选并非偶然。这部作品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那就是中国的翻译家都竞相翻译这部作品,有的甚至为了翻译这部作品,还竭力抢占译机。
这里我不妨透露一个从未向人道及的“秘密”,我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想翻译这部作品,并做了相应的准备工作,仅仅是因为听说我的同窗老友罗新璋已动手译《红与黑》,我才放弃了自己的打算,因为这位老同学在译界以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而著称,我自知不可能像他那样下大功夫,于是,心服口服,退出竞译场,乐观其成。
人物版:您能简单谈谈自己对于萨特的理解吗?对于萨特的研究,给您自己带来了什么?萨特的理论研究成果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还会有影响吗?
柳鸣九:如果撩开萨特哲学体系的术语与概念所组成的厚厚帷幕,用简明、通俗的话来说,萨特存在主义哲理的核心不外是“存在决定本质”与“自我选择”两大要义,即人的存在在先,本质在后,在现实中,人进行自由选择,进行自由创造而后获得自己的本质,英雄的存在决定英雄的本质,懦夫的存在决定懦夫的本质,人在选择、创造自我本质的过程中享有充分的自由,也承当着自我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难看出,萨特的哲理有助于个人主体积极性的启动与发挥,用今天的话来说,有助于自我启动“正能量”,在意识形态上具有积极意义。至于政治上,萨特一直是一位“老左”,一直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和平阵营中的大积极分子。但是在中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他仍被视为意识形态上的“帝国主义的代言人”,而经常受到敲打、批判,我深感对其不公正、不实事求是。
于是,我发文章(《给萨特以历史地位》)、出专著(《萨特研究》),对萨特进行重新评价,也算是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讲些公道话吧,这就是我在萨特问题上的作为。正好萨特的哲理与我的作为投合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即释放个体自主能动性的社会需要,因而,一时思想影响很大,《萨特研究》成为一本畅销书。
然而,早春的天气乍暖还寒,气候难免波动,一时间,《萨特研究》又被视为“精神污染”,被禁再版。不过,两年之后,气候转暖,有关方面对萨特问题也缓过神来,发现他的哲理并没有那么可怕。于是,雨过天晴,《萨特研究》又得以再版,这就是我研究萨特,在萨特问题上挺身而出的经过。
如果要讲我个人因此有什么收获的话,从媒体舆论那里获得了“萨特研究第一人”的称号倒是微不足道,重要的是这段经历在我生命中留下值得纪念的一页,那就是,对自己在学术良知与学术观点上诚实性、坚守性有了一次检验,而这种诚实性、坚守性对于学者来说就是灵魂,就是生命线。检验与磨炼成为我人生中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下中国,社会浮噪,来自于物质功利主义的张扬,来自于急功近利的利益驱动,来自于人文精神的日渐衰落,来自于纯正的价值取向的边缘化。要治愈社会顽疾,扶正祛邪,扶正祛燥,应该从根本的社会机理上着手,加以综合治理。光靠某种哲理无济于事。任何哲理都不是灵丹妙药,萨特哲理也不例外,它可以起到若干良性作用,但是不足以担此济世匡正之大任。
人物版:对于当前中国的翻译界现状,您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对于年轻一代的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您有什么评价和期望?
柳鸣九:“长江后浪推前浪”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也是学术文化界的既定法则,我所在的这个学界、翻译界自不能例外。不过,后浪的浪头究竟有多高,波浪有多壮阔,内在力量有多深厚,那还得稍待时日(对学术文化发展问题,每作一小结,总得要看够二三十年甚至半个世纪、一个世纪),待看后浪的努力与作为,我乐观其成,乐观其效。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文字整理:王长江)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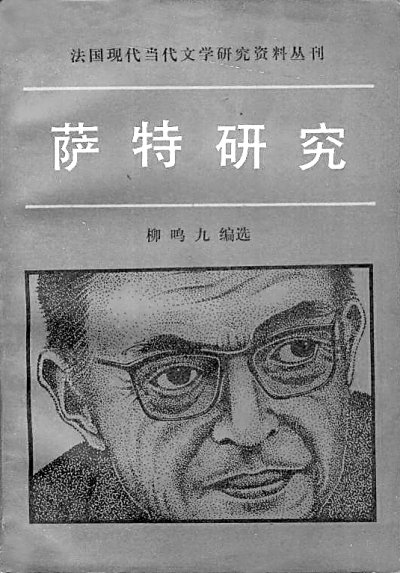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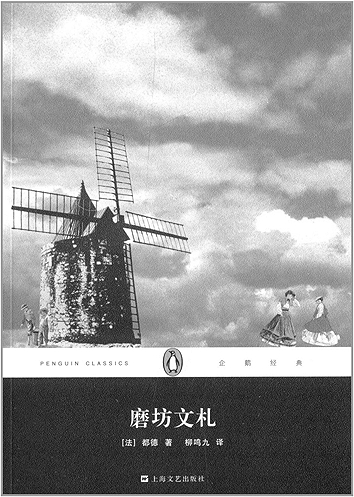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