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在近代中国实现了天翻地覆的变革,传统的研究者在解释这一变革时往往与农村的阶级关系联系在一起。然而,中国各地的乡村千差万别,单一的视角可能会掩盖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罗衍军的《革命与秩序:以山东省郓城县乡村社会为中心(1939—195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9月版)一书,以1939—1956年间的郓城县为考察中心,将乡村社会的嬗变看成一个乡村民众人身、经济、思想等的演变场域,揭示了革命运行与乡村社会秩序的独特关联,再现了一幅各种力量作用下的乡村社会变迁的立体图景。
1939年前的郓城,灾荒与匪乱频仍,社会动荡,“官仁”“绅贤”“民良”的传统诉求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乡村社会民众的心态和行为。日军入侵以前,中共主要是运用血缘、学缘、地缘等传统人际资源进行革命动员,其效果并不明显,多数乡村民众的心态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传统的思想、经济和社会分层在乡村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日军侵入以后,社会舆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共领导下的革命力量,成为民众心目中“咱们的人”,革命力量与社会打成一片。
在1946—1949年的土改历程中,革命政权通过“敌与我”的划分和革命程序的仪式化运作,实现了革命的话语逻辑对乡村“客观现实”的改造与重构。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客观现实”亦通过民众的思想与行为表现着它的存在及对革命话语逻辑、行动逻辑的回应。其中,不同村庄、村庄内不同人物对革命运作的因应是不同的,显示了隐藏在迥然不同的乡村革命运行结果下的内在缘由。通过革命的话语建构和仪式运行,中共大大增强了对乡村秩序的整合与重塑,民众对革命政权的依附性和向心力大大强化,从而为共产党获得与国民党政权作战的人力、物力创造了条件。
1949年后,革命政权通过集体化改造,基本消除了乡村贫富分化,并在经济、思想、人身等各方面实现了对农民的改造。由此,不断的革命动员最终彻底改变了乡村社会的结构和秩序。值得注意的是,在土地改革和集体化进程中,某些新的村庄领导者已无需村庄内部传统伦理、人脉等资源的支持,其政治权威与经济物资的获得,主要来源于不断掀起的革命运动。由于革命的话语逻辑是建立在对富裕者的批判斗争之上,革命积极分子对“生产新贵”的个体富裕,具有天然的警惕。在农民的平均化和求富的双重倾向中,革命政权采取的是遏制农民个体的求富趋向,倡导“集体化共富”,但因无相应的激励机制,“干与不干一个样”,有时易形成人人不愿冒头、集体“均贫”的局面以及“越穷越革命”“富裕即是罪恶,贫穷即是光荣”的行为逻辑。
以往学界的乡村革命运动研究,多为革命政权对民众动员与整合的宏观描述,读者所看到的多是中共革命话语系统中的各级政权领导者的活动,普通民众在这一过程中的心态和行为变动则隐而不明。该书通过分析普通民众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的思想和行为嬗变,将革命运行视为革命政权对民众进行动员整合及民众对政权的因应等多重互动过程。如此视角之下,所呈现的乡村土改不再是简单的“左”“右”之争和各阶层的“善”“恶”归类,而是多重的利益纠葛、复杂的人际网络与合力推进的新旧嬗递。
该书还试图对郓城县与以往研究者所考察的邻近区域——濮阳、滑县、南乐三县,中共革命中枢所在地——陕北骥村,以及长江下游区域进行比较分析,以揭示革命影响下的不同区域乡村社会变迁图景。然而,其中所表现出的差异性,究竟是地域性特点所致,抑或缘于党的政策的灵活性,还需进一步探讨。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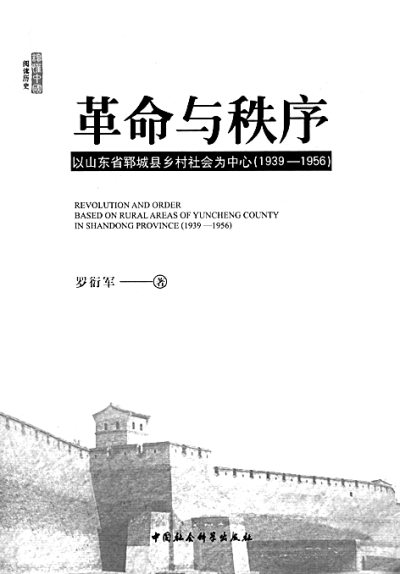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