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令哈是遥远的。从济南遥墙机场到西宁,经停银川要飞行3个半小时,再从西宁乘坐7小时46分钟的火车,中间要停靠17个站点。
去德令哈的火车逢站必停,也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欣赏窗外的景色。那些高高低低的草,或干枯或葱绿,零乱地簇出去,与弯弯曲曲、低矮稀疏的油菜花连接起来,诉说着无法言说的干枯和坚韧,让那些蜿蜒起伏的山峦有了灵性。偶尔出现的牦牛,在广袤的草原上如此孤单,呼啸而过的列车在它身旁掠过,却无法惊动它悠然自得的神情。车外的沙漠红柳,以最自我的本相簇拥成林,然后与油菜花的黄形成鲜明对照,如上帝作画时无意间洒落的色块,大而妖艳,却毫无规则,一切都是舒展的、悠扬的、随性的,缓缓流淌。
窗外下起了雨。三三两两飘落的雨滴,落在那些倔强而坚强的芨芨草身上。都说春雨贵如油,然而对于西部的草原和荒漠,任何时候的一场雨,都比黄金更有价值。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窗外倏忽而过的原野上,竟然有了成汪成片的水,像草原的眼睛,散发出淡淡的光,忧郁而深沉。
一路上有那么多充满奇异色彩的地名,比如湟源,比如海晏,比如天棚,比如关角,这些干净纯粹的名字让我充满好奇,想象着千年或者万年之前,究竟是哪个充满诗性的头颅,如同为乳儿起名般,为它们留下这些名字。
上苍总是公平的,在她给予德令哈无限苍凉的同时,也将世间大美给了她。我感叹雅丹地貌透出的时光沧桑和历史雄浑,似乎看见远古的湖礁从时间的缝隙中被托举而出,那是土地的成长,长成漫漫山峦,长成皮肤的颜色,长成骨骼的坚韧,任凭无边的风雨冲刷独自岿然不动,只留下冥思苦想的头颅和对这片神奇土地的倾情守望。绵延数千公里的祁连山、昆仑山,更像父辈温厚的脊梁,以无言铁骨抵御着凛冽北风的无情嘶鸣,也给世间生灵孕育了莽莽草原、温润的气候。我看见氤氲的水气自柏树山底升起,笼罩着山巅。它们白得像棉朵,并不急于升腾,而是旋转着、张扬着、蓄积着能量,然后将霓裳羽衣般的深情缱绻,化成无数条天使的长袖,舞出一片来自天堂的水。
西域作家梅卓曾有诗句:“我走进红马靴,红马靴埋进了雪,雪雾升上天空,化作佛的迷惘。”德令哈也恰如诗人的述写,一切都似乎充满了神与禅的玄迷。比如托素湖和柯里克湖,两个毗邻的湖,只由一条银色的小河连通,为何上游的湖是淡水,可以是水草丰腴,鱼鸟相嬉,到了下游竟成了咸水,近于一条死河,没有半点生机。当地人称之为“姊妹湖”“褡裢湖”。
因季节原因,我没能去看哈拉湖,那儿至今仍是人迹罕至的地方,还是尚未开发的原始形貌。在朋友告诉我不能成行的原因之后,我的心底生发出巨大的遗憾,改天再来的渴望也愈加强烈。我想象着在那片富庶或者贫瘠的哈拉湖畔,成群结队的野牛如何悠闲地踱着快乐的步伐,三五成群的野驴追逐着打闹嬉戏,棕熊不经意的吼鸣撕破天空的寂静,而以冰川融水滋养的大湟鱼想着谁也弄不明白的心事。有人用“地球上的一滴泪”形容这个海拔4077米的天湖,但我更觉得她是上帝后花园里的心灵浴场,以最澄澈、最动情的方式,诠释着人间仙境的贴切含义。
哲人说,“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来到德令哈,即使不到哈拉湖,也能体会到天堂的美。这种美,融汇了世间所有的神奇,以及诗句中各种各样奇幻无穷的想象。
我向来是一个方向感极强的人,但在德令哈,我竟然弄不清东西南北,如同弄不清自己到底是在人间,还是在天堂。
(作者为山东宁阳县广电局工作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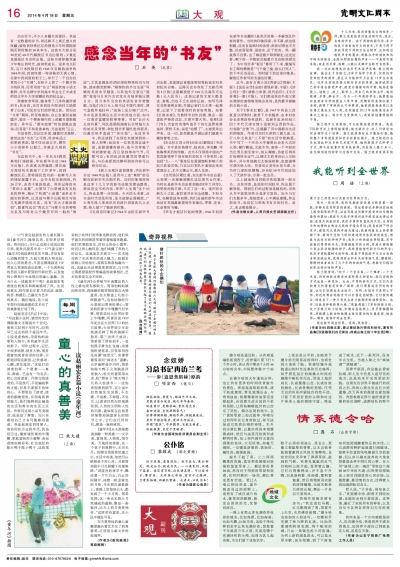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